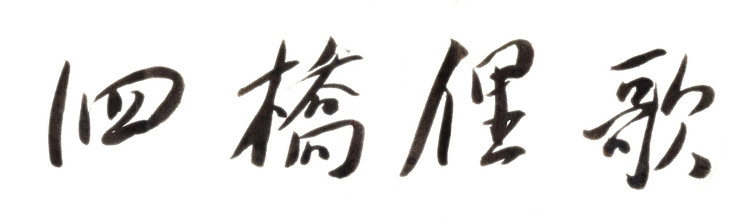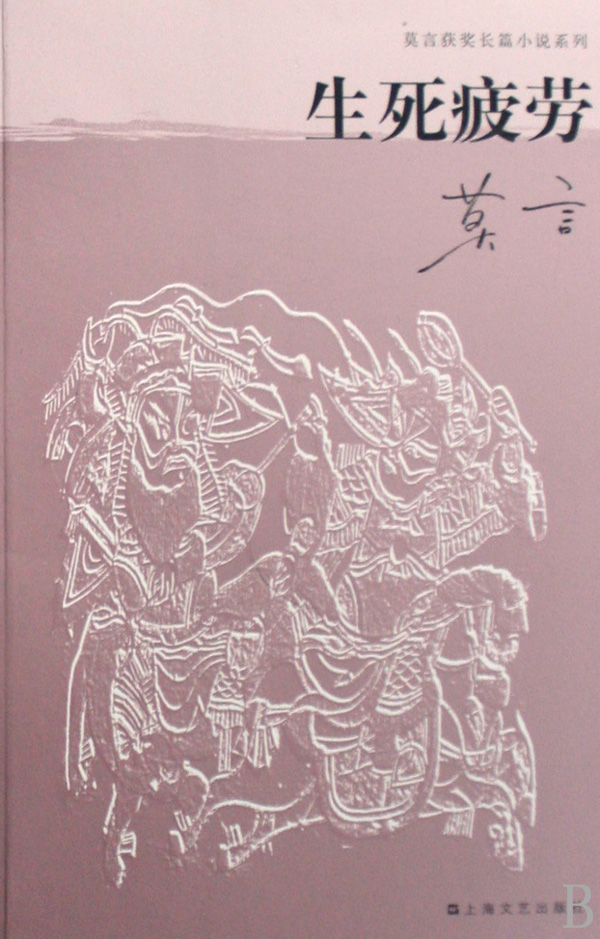生死桥-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丹丹——”
“什么?”
“没什么了。”志高回心一想,急急地说了,怕一迟疑,又不敢了,“丹丹,我还是告诉你吧,瞒下去是不成的,反正你迟早都会知道,我非卷起帘儿来唱个明白——”
“你说吧,里嗦的,说呀。”
“好,我说。”志高坚强地豁出去了,“刚才的,就是我娘。”
“哦?怪道呢,这么地老。”
“她是我娘,因为——她干的是‘不好’的买卖,让我喊她姐……我此后也是喊她姐的。你就当给我面子,装作不知道,怀玉也是这样的。”
“好呀。”
“答应了?”
“好呀,我不告诉人家,我也不会瞧不起你们,你放心好了。”
“丹丹你真好。”
“我还有更好的呢!”
志高放宽了心,人也轻了,疼也忘了。自以为保了秘密,其实北平这么一带的人,谁会不知道?不过不拆穿罢了。亏志高还像怀里揣了个小兔子,一早晚怦怦直跳——也因为她是丹丹吧?
如今说了,以后就不怕了。
“你怎么不跟黄叔叔呢?你黄哥哥呢?现今下处在哪儿?来这儿呆多久?”
“哎,”丹丹跺足,“又要我说!我呀,才刚把一切告诉怀玉哥了,现在又要再说一遍,多累!”末了又使小性子,像她小时候,“我不告诉你。”
“说吧。”志高哀求似的,逗她,“我把我的都告诉你了。”
原来丹丹随黄叔叔回天津老家去后,黄叔叔眼看儿子不中用了,也就不思跑江湖,只干些小买卖。虽是爱护丹丹,但小姑娘到底不是亲骨血,也难以照拂她一辈子,刚好有行内的,也到处矗竿子卖艺,就是苗师父一伙人,也是挂门的,见丹丹有门有户地出来,一拍胸口,答应照顾她。便随了苗家一伙,自天津起,也到过什么武清、香河、通县、大兴等大小的地方,现在来到了北平,先找个下处落脚,住杨家大院,然后开始上天桥撂地摊去。
丹丹又一口气地给志高说了她身世。
“你本是黄丹丹,现在又成了苗丹丹。怎么搅的,越活越回去了?还是苗呢?过不了多久,倒变成籽了,然后就死了。”志高道。
丹丹嘟着嘴,站住不肯走了。
也不知是怎么的前因后果呀。丹丹,她原来叫牡丹。“牡丹本是洛阳花,邙山岭上是我家,若问我的名和姓,姓洛名阳字之花。”——丹丹是没家的,没姓的,也配不上她的名的。花中之王,现今漂泊了,还没有长好,已经根摇叶动。真的,在什么地方扎根呢?是生是死呢?这么小,才十七岁,谁都猜不透命运的诡秘。志高被她的刁蛮慑住了——就像只憋了一肚子气的猫。明知是装的。
“你别生气,我老是说‘死’,是要圆个吉利,常常说,说破了,就不容易死了。”志高慌忙地解说。
“要死你自己死!”
丹丹说着,辫子一甩,故意往另一头走,出了虎坊桥,走向大街东面。
“丹丹,丹丹。”志高追上去,“是我找死,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好没有作孽多,我是灰耗子,我是猪八戒……”
“哦,你绕着弯儿骂你娘是老母猪?”丹丹道。
“不不不。”志高急了,想起该怎么把丹丹给摆平?他把她招过来,她不肯,他走过去,因只穿件小背心,一招手,给她看胳肢窝,志高强调,“我给你看一个秘密,我这里有个痣,看到了吗?在这儿。嗳,谁都没见过的,看,是不是比你那个大?”
“嗳,真像个臭虫,躲在窝里。”
志高笑起来。
他很快活,恨不得把心里的话都给掏出来,一一告诉了丹丹,从来没那么地渴望过。
真好,有一个人,听几句,抬杠几句,不遮不瞒,不把连小狗儿呲牙的过节儿记在心里,利落的,真心的,要哭要笑,都在一块……
咦,那么怀玉呢?
——忽地想起还有怀玉呀。
“丹丹,你先回家,我找怀玉去。”
志高别了丹丹,路上,竟遇上了大刘。他是个打硬鼓儿的,手持小鼓,肋下夹布包,专门收买细软,走街串巷找买卖。许多家道中落的大宅门,他都经常出入。
这个人个头高高,脸长而瘦,在盛暑,也穿灰布大褂,一派斯文。一边敲打小鼓儿,一边吆喝:“旧衣服、木器,我买。洋瓶子、宝石,我也买……”
见到志高,大刘问:
“你姐在吗?她叫我这两天去看她的一只镯子。”
“不在。”志高回大刘,“她不卖了。”
“‘不卖’的是什么?”大刘乜斜着眼问,一种斯文人偶尔泄漏出来的猥琐。
“镯子。”
“哦——”
志高只想着,娘仅有一只镯子,猜是下落不明的爹所送。卖了,反悔了,难免日思夜惦,总想要回东西。志高估摸娘实是舍不得,马上代推掉了,然后心里七上八落——钱呀,想个法子挣钱才是上路。
来到了怀玉的那个大杂院,远远便听得哭喊声,见一个呼天抢地的母亲,把孩子抱出来,闹瘟疹,死掉了。在她身后,还有四个,由三岁到十一二岁的。穷人就有这点划算,死掉了一个,不要紧,还有呢,拉拉扯扯的,总会成长了几个,继承祖先的“穷”,生命香火顽强地蔓延下去。
那伤心的母亲领了他兄弟姐妹,拿席子卷了尸首去——死了一个,也省了一个的吃食呀。志高心头温热,他竟是活着呢,真不容易。
敲了唐家的门,一进去,不待唐老大作声,也不跟怀玉招呼,志高扑一下跪下来:“唐叔叔,我给您赔罪!”
唐老大气还没消,这下不知如何收拾他。
志高又道:“对不起您,以后我也不敢搭场子了。”
说完了,起来逃一般地走了。
唐老大也不好再责怪什么了,看着他背后身影:“这孩子就是命不好。”
怀玉跟他爹说:
“命好不好,也不是没法可想的。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也得去‘谋’呀。爹,我也不打算永远泡在天桥的,我明天跟李师父说去,让他给我正正式式踏踏台毯。”
“你去练功,我不数算就是,可你去当跑龙套的,什么时候可以出头?连挣口饭吃的机会都没有!”
“我要去,不去我是不死心的。”
“你不想想我的地步?”
“爹,撂地摊吃艺饭又是什么地步?圣明极了也不过是天桥货。”
“没有天桥,你能长这么大?”唐老大气了——他也不愿意怀玉跟随他,永不翻身,永永远远是“天桥货”。但,怀玉的心志,原来竟也是卖艺。卖艺,不管卖气力卖唱做,都是卖。不管在天桥,抑或在戏园子,有什么不同?有人看才有口饭吃,倚仗捧场的爷们,俯仰由人,不保险的,怀玉。
唐老大要怎样劝说那倔强的儿?
“谁有那么好运道,一挑帘,就是碰头彩?要是苦苦挣扎,扯不着龙尾巴往上爬,半生就白过了。”
他说了又说,怀玉只是坚持,戗戗老半天:“千学不如一唱,上一次台就好!”
唐老大明知这是无以回头的,当初他跟了李盛天,就早已注定了,怎么当初他没拦住他?如今箭在弦上,唐老大一早上的气,才刚被志高消了一点,又冒了:
“你非要去,你去!你给我滚!”
一把推走这个长大了的儿子。
怀玉踉跄一下,被推出门去了。
唐老大意犹未足:
“你坍了台就别回来!”
然后重重地坐下来。孩子,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以为自己行,可马上就坍台了,残局还不是由连苍蝇也不敢得罪的大人来收拾么?早上是志高,晚上是怀玉,虎背熊腰的粗汉,胡子就这样地花白起来了,像一匹老马,载重的,他只识一途,只得往前走,缓缓地走着。是的,还载重呀,终于走过去了。他多么希望他背负的是玉,不是石头。怀玉,自己不识字,恳请识字的老师给他起个好名儿呢,怀的是玉。没娘的孩子,就算是玉,也有最大的欠缺。唐老大想了一想,便把门儿敞开,正预备把怀玉给吆喝进来了。
谁知探首左右一瞧,哪里还有他的影儿?做爹的萎靡而怆惶。
——孩子大了,长翅了。
从前叫他站着死,他不敢坐着死。
赶出门了,就瑟缩在墙角,多么拧,末了都回到家里来。
啊,一直不发觉他长翅了。
他要飞,心焦如焚急不及待地要飞。孩子大了,就跟从前不一样了。
怀玉鼓起最大的勇气,恭恭敬敬地等李盛天演完了一折,回到后台,方提起小茶壶饮场。觑着有空档,企图用三言两语,把自己的心愿就倾吐了——要多话也不敢。他一个劲地只盯着师父一双厚底靴:
“——这样地练,天天练,不停练……不是‘真’的呀。反正也跟真的差不多了,好歹让我站在台上,就一次……”
李盛天瞅着他,长得那么登样,心愿也是着迹的:要上场!
“哦,你以为上台一站容易呀?大伙都是从龙套做起。”
“您让我踏踏台毯吧,我行。”
“行吗?”师父追问一句。
“行呀行呀,一定行的,师父,我不会叫您没脸,龙套可以,不过重一点的戏我也有能耐,台上见就好。”
李盛天见这孩子,简直是秣马厉兵五脏欢腾,颜面上不敢泄漏出来,可一颗心,早已飞上九霄云外。
师父忍不住要教训他:
“你知道我头一回上场是什么个景况?告诉你,我十岁坐科,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手脸都裂成一道道血口了。头一回上场,不过是个喽罗……”
李盛天的苦日子回忆给勾起来了,千丝万缕:母亲给写了关书,画上十字,卖身学习梨园生计;十年内,禁止回家,不得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他的严师,只消从过道传来他咳嗽声,师兄弟脸上的肌肉就会收紧,连呼吸都变细了——全是“打”大的。一个不好,就搬板凳,打通堂。
那一回夏天,头上长了疥疮,上场才演一个龙套,头上的疮,正好全闷在盔头里,刚结的薄痂被汗水洗的脱掉了,黄水又流出来。就这样,疼得浑身打颤,也咬着牙挺住,在角儿亮相之前,跑一个又一个的圆场……
怀玉虽是苦练,但到底是半路出家的,没有投身献心地坐过科。
比起来,倒真比自己近便了,抄小道儿似的。
李盛天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不肯稍为宠他一点,以免骄了——机会是给他,可别叫他得了蜜,不识艰险。
怀玉只听得他可跟师父上场了,乐孜孜的,待要笑也按捺住。一双眼睛,闪了亮光,把野心暗自写得无穷无尽。这骗不了谁,师父也是过来人。好,就看这小子有没有戏缘,祖师爷赏不赏饭吃,自己的眼光准不准。功夫不亏人,功夫也不饶人。怀玉的一番苦功,要在人前夺魁,还不是时候;龙套呢,却又太委屈了,李盛天琢磨着。
“这样吧,哪天我上《华容道》,你就试试关平吧,我给班主说去。不过话得说回来,几大枚的点心钱是有,赏的。份子钱不算。”
——钱?不,怀玉一听,不是龙套呀,还是有个名儿的角色呢,当下呼啸一声……
生死桥 '贰'(5)
“怀玉哥,有什么好高兴的事儿?”
在丹丹面前,却是一字不提。
对了,告诉她好,还是瞒着呢?
头一回上场,心里不免慌张,要是得了彩声,那还罢了;要是像志高那样,丢人现眼的,怎么下台?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心高气傲,更是输不起的人。
不告诉她,不要她来看——要她看,来日方长呀,她准有一天见到他的风光,这怀玉倒是笃定的。在关口,别叫一个娘们给影响怵阵了,卡算着,就更不言语了。
丹丹跟怀玉走着路,走着走着,前面胡同口处青灰色的院墙里,斜伸出枝叶繁茂的枣树枝来。盛夏时节,枣儿还是青的,四合院里有个老奶奶,坐在绿阴下,放上两个小板凳,剥豆角。
蝉在叫。怀玉伸手想摘几个枣儿来解渴。手攀不上呢,那么的高。只因太乐了,怀玉凭着腰腿,一二三蹦上墙头,挑着些个头大的,摘一个扔一个,让丹丹接住。半兜了,才被奶奶发现:“哎呀,怎么偷枣儿呢!”她忙赶着。
怀玉道:“哈,值枣班来了,可早班晚班都不管用了!”丹丹睨着这得意非凡地笑的怀玉,他正预备跳下来。
还没有跳,因身在墙头,好似台上,跟观众隔了一道鸿沟。丹丹要仰着头看怀玉,仰着头。真的,怀玉马上就进入了高人一等的境界了。心头涌上难以形容的神秘的得意劲,摆好姿势,来了个“云里翻”。
往常他练云里翻,是搭上两三张桌子的高台,翻时双足一蹬,腾空向后一蜷身……好,翻给丹丹看,谁知到了一半,身子腾了个空,那老奶奶恨他偷枣儿,自屋内取来一把竹帚子,扔将出来,一掷中了。怀玉不提防,摔落地上。猛一摔,疼得摧心,都不知是哪个部位疼,一阵痉挛。丹丹一见,半兜的枣儿都不要,四散在地,赶忙上来要扶起他。
怀玉醒觉了,忍着——这是个什么局面?要丹丹来扶?去你的,马上来个蜈蚣弹,立起来,虽然这一弹,不啻火上加了油,浑身更疼,谁叫为了面子呀?用手拍掉了土,顺便按捏一下筋肉,看上去,像是挥泥尘,没露出破绽来。忍忍忍!
“怎么啦?”
“没事。”怀玉好强,“这有什么?”
“疼吗?”
“没事。走吧。”怀玉见老奶奶尚未出来拾竹帚,便故意喊丹丹,“枣儿呢?快捡起来,偷了老半天,空着手回去呀?快!”
二人快快地捡枣儿。看它朝生暮死的,在堕落地面上时,还给踩上一脚。直至老奶奶小脚丁冬地要来教训,二人已逃之夭夭。丹丹挑了个没破的枣放进嘴里:
“瞎,不甜的。”
怀玉痛楚稍减,也在吃枣。吃了不甜的,一嚼一吐,也不多话。
丹丹又道:
“青楞楞的,什么味也没有。”
见怀玉没话,丹丹忙开腔:“我不是说你挑的不甜呀,嗄,你别闷声不吭。”
“现在枣儿还不红。到了八月中秋,就红透了,那个时候才甜脆呢。”
“中秋你再偷给我吃?”
“好吧。”
“说话算数,哦?别骗我,要是半尖半腥的,我跟你过不去!”
“才几个枣儿,谁有工夫骗你?”
“哦,如果不是枣儿,那就骗上了,是吗?”
怀玉说不过她,这张刁钻的嘴。只往前走,不觉一身的汗。丹丹在身边不停地讲话,不停地逗他:“你跟我说话呀。”
清凉的永定河水湛湛缓缓地流着,怀玉跑过去在河边洗洗脸,又把脚插进去,好不舒服,而且,又可以避开跟丹丹无话可说的僵局。她说他会骗她,怎么有这种误会?
丹丹一飞脚,河水撩他一头脸,怀玉看她一眼,也不甘示弱不甘人后,便还击了。
玩了一阵,忽地丹丹道:
“怀玉哥,中秋你再偷枣儿给我吃?”
他都忘了,她还记得。怀玉没好气:
“好吧好吧好吧!”
“勾指头儿!”
丹丹手指头伸出来,浓黑但又澄明的眼睛直视着怀玉,毫无心机的,不沾凡尘的,她只不过要他践约,几个枣儿的约,煞有介事。怀玉为安她的心,便跟她勾指头儿。丹丹顽皮地一勾一扯,用力的,怀玉肩膀也就一阵疼,未曾复元,丹丹像看透了:“哈哈,叫你别死撑!”又道,“你们男的都一个样,不老实,疼死也不喊,撑不了多久嘛,切糕哥也是!咦?我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