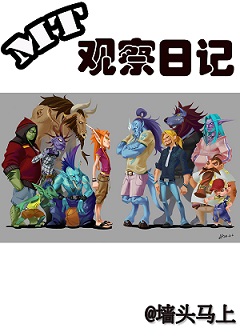绝望日记-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既然睡不着,索性就不睡了,白子惜安静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顺手带上了门。她打开电灯,昏暗的小房间霎时间变得通明起来。床边摆放着木质的衣橱和巨大的穿衣镜,在灯光照射下镀金的边框熠熠生辉。
白子惜划开手机的锁屏,没有新消息。她顺手把手机丢在床上,叹了一口气,百无聊赖地走到了穿衣镜前。她看到镜中那人一身松垮的睡衣,及肩的长发柔软地披散着,如同羊脂玉一般的肌肤尽极白皙紧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就如同她母亲年轻的时候,眼波流转间每一次颦笑都独具风韵。
想到这里,她非但不欢喜,反而黯自神伤起来。只可惜良辰美景都不能长久,红颜终会有一天风华逝去,人老珠黄。她定定地看着自己镜中的脸,像是在端详一件绝世的艺术品,但也像是在对着虚幻的镜花水月徒劳地留连。
人终归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老去……
容颜就像是指缝间的沙子,永远在昼夜不停地缓缓消逝……
白子惜的目光慢慢地游走在镜中人那完美而易碎的躯壳上。
突然,就在那一瞬间她的目光猛的定住了,双眼骇然地瞪大,黑色的瞳孔急速骤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女人的尖叫声划破深夜的寂静,白子惜惊恐万状地跌倒在地,双手颤抖着触碰着自己脖子……
那上面……
赫然是五个红色的手指印……
那是用力掐过的痕迹……她能看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她回想起自己刚才那个诡异的梦境,顿时惊恐得汗毛倒竖。
房门被嘭的一声推开,门口站着她同样骇然的母亲。
“怎么了?!”
“我我……”她惊惧地在地上颤抖着,不知道要怎样解释。
这到底是……
“又做噩梦了吗?”
“是……”她用手遮盖着脖子上的红印,一步一步地挪过去躺到了床上蒙上被子,“我是做噩梦了……”
母亲白了她一眼,你就这点出息?多大的人了,别没事就大呼小叫。
听到母亲摔门而去的声音,白子惜暗地里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在这件事情被搞清楚之前她绝不能让母亲知道,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解释为一种处事的本能或是直觉吧?
她缓缓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再次站到了穿衣镜前,白皙的脖颈上几枚鲜红的指印怵目惊心,她伸手比了比,的确是人的手指印,是右手,那个手印比她自己的手大了一圈,确实像是个男人留下的。
但是她脑海中却一直有一个声音叫嚣着否定这种想法,这不可能是别人留下的,在她睡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过,唯一解释这个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睡着的时候一不小心压出来的……
可是……
睡觉怎么可能压出这样的痕迹啊?!
说不定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
无厘头的猜测互不相让,就像是两块碰撞在一起的大陆板块,互相拼命地挤压着试图粉碎对方,直压得白子惜肝肠寸断。
说真的,白子惜现在宁愿相信这是某种奇怪的病症也不愿意承认这手印一样的东西和那个恐怖的梦境有所关联。
不会是那样的,这顶多只是个巧合而已……
毕竟如果是那个梦境变成了现实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啊……
白子惜在心里默默地安慰着自己。
所以为了彻底打消自己可笑的疑虑,她打算做一个更加荒唐的实验来证明自己此刻的安然无恙。
是不是还活的好好的,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
她偷偷地溜出房间,从餐厅橱柜里的家庭药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听诊器,这简直是太荒谬了,太可笑了……简直就是脑子有病啊……白子惜一边取笑着自己一面颤抖着戴上听诊器耳管,把胸件狠狠的按压在自己的左胸上。
我真Tm是个精神病……
真是的,这件事要是被母亲知道了,准够她笑话几个月的了……哈哈哈……
算咯,反正我大半夜的睡不着,就当是打发时间好了……
哈哈,哪有这样打发时间的,分明就是神经了么……
各种乱七八糟的思绪在她的大脑里绞作一团,白子惜越发觉得自己可笑起来。
钟表的指针悄然滑过那个刻度,三点三十分。
听诊器突然落在了地上,她的世界在那一瞬只剩下一片死寂。
秒针又转过了一个轮回,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三十一分。
白子惜不甘心地拾起了那个听诊器。
戴上耳管,把胸件狠狠的压了上去。
仍然是……
死寂……
这……
这到底是……
怎么会……
我……死了?!
她跌倒在地,用尽平生的力气克制住自己没用再发出杀猪似的惨叫。
她瞪着双眼,想哭,她想哭。身体却无法分泌出泪水。
我不相信……
这不可能啊!!
白子惜失魂落魄地冲进了厨房,把左手放在水池子上,右手抄起菜刀。
手起刀落,她的理智在那一刻全部泯灭。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三十五分。
车间里值夜班的工人疲惫地打了个哈欠,民房中备考的学生困倦地收起了书本,别墅区内几个孩子的母亲慵懒地发出一声梦呓,车道旁洁白的蛇床花静静开放。
她的鲜血溅落在不锈钢的水槽里,就像是随手泼出的颜料。
没有痛觉……
手腕上的创口怵目惊心。
失去了活力的血液慢慢地淌着,在水槽里慢慢地汇聚成了一片,又慢慢的流入了肮脏的下水道。
她莫名地想到了杀猪放血。
没有办法,她只能站在这里等着血液流尽。此刻白子惜的思绪反而很安静,仿佛世界都静了,只剩下……她自己鲜血不断滴入下水道那微弱而优美的旋律。
她不知站了几个小时,直到天边泛起第一抹狐狸毛似的水红,东方已明,水红又渐渐的变成了鱼肚白。
天亮了……
她像根木头一样呆呆的伫立着迎接着来自遥远东方的日光。
我要怎么办……这一定只是个梦吧?
那就快点醒来吧……
天色不管不顾地变得越来越明亮。
房间里传来了母亲的哈欠声。
白子惜感受到了恐惧,越发的恐惧,就像是只能游走在暗夜中的鬼魂惧怕着白天的到来。猛然想起很久前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我要溺毙于恐惧的海洋”,真的是这样,她像是身处于极寒的地方,即将因恐惧而窒息。阳光照在身上,肌肤却丝毫感觉不到温度,所谓极寒也不过是并不恰当的比喻罢了。
在那旖旎的日光下,她就会像是一只被扔在人群里的怪兽一样无所遁形……
逃,此刻的她只有这一个想法,快逃!
白子惜在披上大衣戴上口罩又从抽屉里拿走了两张银行卡后,便头也不回地冲进了这繁华都市迷宫一样错杂的街道里。
未亡 (二)
楔子,夜未央
是夜,她走在小路上,路灯下的梧桐影影绰绰,风冷的刺骨,在寒风呼啸之中,夜半的小路寂寥无人。她能听到自己的高跟鞋一声声地敲击着沥青路面,两侧的低矮的围墙间是空旷的回响。
有些害怕,她加紧了步伐。
在那摇摆不定的梧桐树影里,又会有谁在暗暗窥瞧。
她变得紧张,甚至有点慌乱。这不能怪她,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对黑暗和未知的恐惧早已被写入了人类的基因密码。
她更加加快了步伐,频频四顾,几乎是出于身体的本能,她要马上离开这里,不容得一刻的停留。早在那遥远的上古时代,这就已成为了她猿猴祖先的保命哲学。
快要过去了,前面就是新城区,她几乎能看见那里隐隐透出来的万家灯火霓虹流转,她在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公寓,在找到男友之前,她不得不和母亲住在一起。
高跟鞋敲打着地面又向前落了一步,但在这一下过后,却再没有了后续的脚步声。
小巷中是死一般的寂静,风呼啸着打磨着古老的砖瓦墙,空气流通过墙砖的缝隙是一种沉沉的笛鸣声,仿佛是在这千百年来的悠悠岁月中,从未停歇过的魂灵的悲泣。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响很响。在这死气沉沉的青石小道上,兀自律动着格格不入的生命的气息。
“你……是?”
用尽全力发出的声音却是如此微弱。
那只枯朽但无比有力的手,仍然死死的勾住了她的肩膀。
她动都不敢动一下,身后是融入那无尽的黑暗中的死寂。没有回答,也并不需要。
一张布满皱纹的狰狞的面孔从她的肩头探了过来。
我要你死……
滚开,她惊恐地尖叫,双手狠狠地推在那张脸上,你是谁,快放了我!
她是个有文化的都市女性,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她不信鬼神,虽然身后突然出现的这个怪人使她惊恐万分,然而这并不代表她可以放弃抵抗,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希望,她也要拼死一搏!
她将自己的挎包猛的抡起向他劈头盖脸地砸去,走夜路没带防狼辣椒水真是太失策了,她恨恨的想。
直到看着那人头部流血缓缓地向后倒去,她一咬牙关拔腿便跑。
然而就在下一瞬间,她惊叫一声,挎包脱手飞出,在夜空下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落入了小巷石墙投下的深深暗影中。
伴随着脚腕的剧痛,她整个人失去控制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
有温热的液体顺着她的发际线缓缓流下,绕过鼻梁,氤氲在覆盖着桃红色唇彩的薄唇间。
缓缓地抬起头,看着卡在石板砖缝间的高跟鞋跟,她咬咬牙,艰难地试图移动双脚,然而回答她的是一阵抗议般的剧痛。
扭伤了……
几片乌云飘过,连月亮的光华也被笼罩了起来。
可恶……
她艰难地试探拔出鞋跟。
不行,还是……卡得太紧……
此时的这个女人,满身泥水,蓬头垢面,她诅咒似的叫着,那声音回响在砖瓦间,对于小巷石墙千百年的寿命来说,也只不过是浮光掠影的瞬息罢了。
包括她的生命。
浊重的喘息声断断续续地,在一片黑暗中在她的耳边炸响。
我要你死……
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脚踝扭伤的厉害,连基本的发力都做不到。
在她惊恐而绝望的惊叫声中,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男人——仿佛是索命的厉鬼,挣扎着一步一步地爬向自己,嘴里重复着可怕的诅咒。
我要你死……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她双手拖着身体向后蹭去,我不认识你,和你没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那个男人突然停了下来,歪歪头愣愣地看着她,突然嘴角一咧,在黑暗中,她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脸孔,那双黑如点漆的人眼中透出的是近乎扭曲的疯狂光彩,毫不掩饰的杀意,就像是黑夜丛林中发现猎物的饥饿的野狼。
杀你不需要理由……你该死……
她惊慌地向后爬去,那个男人喘息着艰难地向她蹭过来,头上的伤口不停地冒着血,一滴一滴的猩红落下,被脚下的青石板贪婪地吸收殆尽。
她拼尽全力地挪动,双手和膝盖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痛的汗如雨下,但是她不敢,也不能有一刻的停歇。
鲜血从他头部的创口源源不断地淌下,上衣被浸透,他痛苦地摔倒,但是又爬起来,向她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两个生命个体——准确地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这繁忙的都市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着一场绝望的赛跑。
终于,趁着她体力不支喘息的当,他猛的扑了上去压住了她,在她绝望至极的尖叫声中,他缓缓地抬起那双长满老茧,枯瘦但是有力的手,像野兽一样发狠地钳住了她细弱的脖颈。
直到她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发不出声音,她的世界在此刻窒息的痛苦和他疯狂的目光中渐渐下沉,一片死寂。
白皙的双手无力地垂下,落在了泥水洼中,溅起了一片肮脏的水花。
未亡 (三)
第二章,精神病
她跟在护士长身后小心翼翼地走进狭长的走廊,例行查房,在病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她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
这里是本市最大的一所精神病医院。
从那天起,白子惜逃离了她原本的生活轨迹,她用了假身份,改头换面地在城北的贫民区里开了一家杂货店。
这个女老板很奇怪,她不分春夏秋冬地穿着长衣长裤,脸上永远戴着白色的棉质口罩,少言寡语。久而久之,街坊里关于她的传闻多了起来,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无非是这个人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所以才不敢和别人有什么交集。
生意越做越差,不过白子惜无所谓。
对于这样一个连人也算不上的东西来说,还有什么是有所谓的呢?
她失去了呼吸,惨白得吓人的皮肤是因为本身就没有血液。
不用进食,也不用睡眠。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子惜总喜欢一个人在贫民区漆黑肮脏的小巷子里徘徊。地上的树影交错成了一片芜杂的颜色,灰色黑色棕色,一片片的就像是那个梦中诡异的男人密布皱纹的斑驳的肌肤。
那算是梦吗……
佛祖说过,我们在这人世间经历的这一切终都为幻象,包括这身腐朽的皮囊。她兀自呵呵地笑了,那我现在算是个什么样子?已经超脱在六道之外了吗?如来佛祖可真是会开玩笑啊……
真即是幻,幻即是真……她就像是生活在真实与虚幻的夹缝之中。说不定真实的她早已经死去多年,而过去几十年所谓的活着才是场不愿醒来的幻梦。
不知是为什么,她竟有些盼望能够再见上那个男人一面。
看着投映在肮脏污水上街灯昏黄的光影,白子惜莫名其妙地呵呵笑了起来。
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竟传来了一声似是回应她的呵呵笑声。
她自知碰上了精神病,但还是好奇地想过去看看。
白子惜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向那个发出声音的角落缓缓地走了过去。
一团模糊的人形影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那里。
白子惜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缓缓地照了过去。
雪白的光束将黑暗在刹那间驱散,周遭笼罩在一种令人安定的纯白色光晕中。这就像是自己每天下班回家后打开客厅大灯的时候。白子惜暗暗地想着。
那个苍老的女人缓缓地抬起了头。
她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喉头不自然的紧了紧,紧接着白子惜看到那个女精神病的脸上绽开了一个无比温柔的笑容。
她猛的冲上去抱住了她,毁坏的嗓子里发出了一声几乎不可辨的“女儿啊”
白子惜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吓得够呛,被花甲女人紧紧抱住的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不知所措。
这是个精神病,她知道的。
可她的心中却还是有那么一种隐秘的感情被轻轻触动。
自己的母亲到现在也大概是这么个岁数吧……
在这个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是因为失去了她最亲爱女儿吗……
那么自己的母亲现在……
她狠狠的咬着嘴唇,不敢再想下去了。
她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我做错了什么啊……
老女人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一面紧紧地拥抱住她一面在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别怕”
白子惜颤抖得越发痛苦。
她缓缓地伸出了双手一面在脑海里想象着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