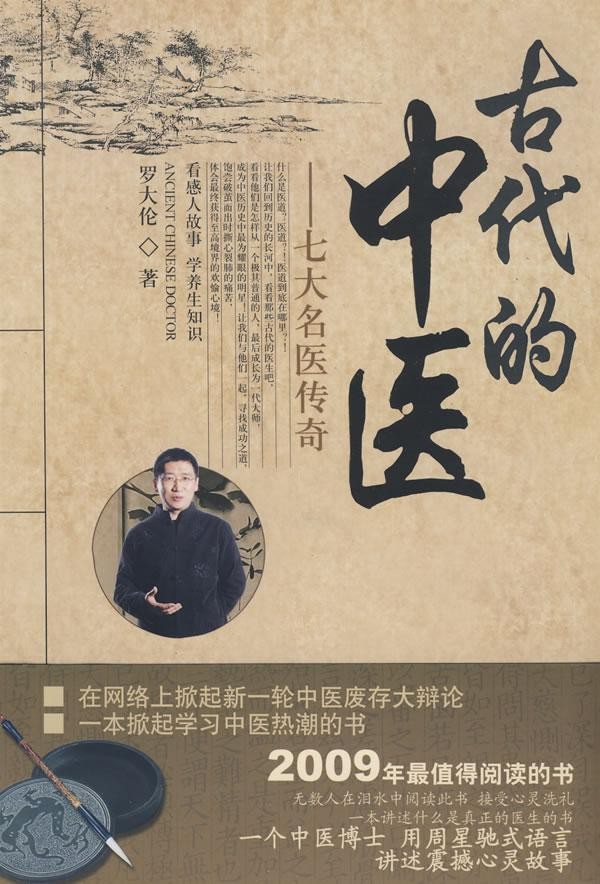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来一些只带着很少资金、自称为“生口牙人”的人。他们对家长说有人想找一个姑娘做妻子或养女,怂恿家长交出一个女儿或婢女。这个姑娘会被藏起来一段日子,然后偷偷送到很远的地方转手卖掉。家长发现上当受骗后,即便立刻报告县令,寻人搜索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他们将永远不知道女儿在哪里,甚至永远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宋代史料还经常提到公开的绑架。洪迈记录了一位十七八岁的224宗室女乘轿子到附近亲戚家的路上遭绑架后还挨了打,被交给生口牙人,卖给一个男人做妾,那个男人知道她的身世并且认为那就是她的魅力所在。洪迈还说有一位官员的妻和妾在乘轿子途经杭州时双双被绑架。绑架者当然会受到蔑视。一部训诫故事集里的以绑架和诱拐为生的男人,到后来遭到报应,浑身奇痒难耐,萎缩成一个废人。
大多数描写买卖妾的市场的人似乎都有一点观淫僻的眼光,感觉他们的读者会从中分享想像可爱女子的快感,这种场景的吸引力绝不会因为知道女子是被迫的而且还经受了苦涩和悲哀而减少。但是,至少有几个作者明确地谴责了买卖妾的市场。比如北宋学者徐积(1028—1103),试图用一首诗打消那些让女儿做妾的人的念头,他的诗假想了一位经历了不幸、变成一个大户人家的妾的女孩子:
妾家本住吴山侧,曾与吴姬斗颜色。
燕脂两脸绿双鬟,有貌有才为第一。
十岁能吟谢女诗,十五为文学班姬。
十六七后渐多难,一身困瘁成流离。
尔后孤贫事更多,教妾一身无奈何。
其时痴呆被人误,遂入朱门披绮罗。
朱门美人多嫉妒,教妾一身无所措。
眉不敢画眼不抬,饮气吞声过朝暮。
受尽苦辛人不知,却待归时不得归?
尽管徐积意在移风易俗,但是这首诗引起的感觉多半是人们被那位虽遭蹂躏,但仍敏感、可爱的年轻女子所吸引。
第十三部分:妾妾 4
男人和妾
225一般情况下,男人在进入中年以后开始纳妾,这时候他们多半当上了一家之长,对相处了15年或更久的妻子有点厌倦。比如苏轼(1036—1101)38岁时把11岁的王朝云(1063—1096)接回家做妾。但是还有许多与这种模式不同的情况。年轻男子婚前纳妾并不少见。我们得知,有一个男人,不到二十岁就有几十个妾。还有七八十岁纳妾的老翁。财力雄厚的男人似乎经常有好几个妾。11世纪富有的官员周高,有几十个姬妾,韩侂胄(逝于1207)号称有14个妾。洪迈记录的故事里,一位富有的官有七八个妾,但在他又老又病时,她们都打算离开他。
男人怎样对待他们的妾?一般说来很不相同,有的宠爱青年女人,忽视妻子,有的把她们当欲望的对象,有的急于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妾。然而,特定的模式还是值得注意。男人一般不为妻子改名,但是差不多为所有的妾和婢女改了名,这象征着这些女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妻子一般正式地以姓相称,妾们则通常用个人化的本名相称,这个名字多半是主人起的。我们发现,妾的名字经常含有“奴”字,如“柔奴”,“莲奴”,“馨奴”或“进奴”。高文虎(1134—1212)给妾何氏起名“银花”,雪片的雅称。其他文人士子也为妾起文诌诌的名字,有人爱起直截、明快、无路数可寻的名字,比如辛弃疾(1140—1207)给两个妾起名,就用姓做名,因此二人被叫做“田田”、“钱钱”。
下层阶级的女孩子受到的准备做上层阶级男人的妾的训练就像在等着当妓女,而且很多男人喜欢让妾在家里像妓女那样招待客人,逗客人取乐。寇准(961—1023)以喜好彻夜的华宴知名于世,宴会上还要有歌舞姬跳舞、奏乐,还必须有一位能即兴作诗、吟诗的女子。袁采提醒说教婢女和妾学会招待客人会引起麻烦: 如果女人美丽过人或才艺高超,“虑有恶客起觊觎之心”,引起灾难性后果。魏泰(约1050—1110)描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杨绘让自家唱曲的姑娘们招待客人,客人中有一位喝多了,对一个姑娘做得太过分,226激怒了藏在屏风后面看热闹的妻子。妻子招呼众姬妾打那个姑娘。而那位客人却要求姑娘回来,继续玩笑取乐。杨绘此刻打算结束宴会,但这只不过惹得客人更生气。客人开始动手打杨绘,结果众宾客一拥而上,才把他救出来。
因为得到的对待像妓女一样,妾也就容易像妓女那样为人行事。我们得知,苏轼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源于他发现一个最近刚去世的朋友最宠爱的妾在另一个男人家里招待客人。“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苏轼显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 妾们经常没事人似的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手里。
只有很少的士人写过妾及自己与她们的关系。刘克庄(1187—1269)声明他出于对妻子的忠诚而纳妾;她死后,出于对她的尊敬,他决定不再续娶。“余年四十二,哭林淑人哀逝者之贤而夭。遂不再婚。既葬淑人,左右无侍巾栉者。或言里中有孤女陈氏,本大族母征,携以适人。长无所归。先亲魏国为余纳之”。刘克庄赞扬比他年轻24岁的陈氏(1211—1262),在后来的35年里照管着所有的家务,记着每一件事,管好每一笔钱财。他不把她当作妾而称她为小儿子的“生母”,也不认为自己是丈夫,只是她的“主君”。
高文虎(1134—1212)提供了男人与妾的关系最完整的记录。在一封信里高文虎写到,妻子在他30岁那年,1163年去世了,在后来的27年里,出于为孩子着想,他既没再娶也没纳妾。只不过在1200年的正月里,他66岁时,与何氏签订了一个3年的合同。
高文虎说,何氏的职责就是为他熬药、收拾东西,照料他。她经常为他做早饭和晚饭,照管他的衣服: 洗,缝补,按时令变换准备好应季衣服。晚上如果他有点儿咳嗽或睡不着觉,她就起床,升火,为他熬药。她也能读、写,常为他找东西、写回信。她来了一年以后,高文虎退休辞官,到儿子任职的徽州住。他带着何氏,在徽州度过非常和谐的两年,游玩了当地所有著名景点。此后他们就回到高文虎的老家明州(宁波)。
227在这封信里,高文虎有点含糊地透露,无论会引起什么样的猜测,他都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何氏进行性活动,自己已经老了,不再对常人热衷的事感兴趣。何氏在11年里没有生孩子,看起来支持了他的声明。但是高家其他成员显然都认为他被何氏迷住了,而且担心他会把家产浪费在她身上。
第十三部分:妾妾 5
高文虎非常喜欢何氏,希望亲眼看到她得到他曾许诺给她的钱财。他写到,问题在于“余身旁无分文,用取于宅库,常有推托牵掣,不应余求”。为了解除这种困境,他决定卖掉家里一块地收获的600石谷物,但是刚刚卖了五六十石,管理庄园的僧人就告诉他,他的儿子和儿媳打算用卖谷物的钱建一座粮仓。后来,儿子前来劝慰他,说他可以从宅库里支取钱财,哪怕他需要一千贯,也会给他。然而,每次高文虎到宅库去,得到的回答都说现在没有钱。最后,又过了两年,高文虎再次下令卖掉庄园里的谷物,这次卖谷得到1080贯钱,其中800贯是给何氏的。
按照高文虎所写,何氏愿意在他死后作为寡妾住在高家。高文虎深知这件事难以实现,所以到了1210年,他认为到了让何氏回娘家的时候了。在信的结尾之处,他概括了何氏应该得到1000贯钱的正当理由。第一,钱是他的,他为家庭赚到很多钱,而儿子并没有。第二,何氏应该得到这笔钱: 照顾他11年以来她自己从未要求得到家产,没从宅库支取过钱,也没有干预过家庭财务。甚至何氏穿的衣服都是用高文虎自己的钱做的。因此,用1000贯钱给她做嫁妆并不过分。如果有人嫉妒,挑起无端的指控,何氏可以把此信做为证据,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妾在家庭里的边缘位置
妾是家庭里的一员,但是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很不稳固,她们与主人、主人的孩子,甚至与自己生的孩子之间的联系都是脆弱的。
中国作者们惟一详细列出妾与其加入的家庭里其他成员间的联系的地方是对丧服的阐释。已婚女子在婚后为娘家人服丧的义务比原来减低一等,但是几乎要为夫家所有成员(比如丈夫的兄弟、叔伯和本家)服丧,丧期与丈夫一样。这些成员间的义务是双向的,如果妻子去世,别人应当为她服丧。228对比之下,妾就像未婚女人一样,对娘家人还有服丧的义务,虽然实际上可能很少执行。妾对男主人家庭的义务很少。妾只为男主人、女主人和主人的孩子服丧。妾只有在生了孩子以后,男主人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与她之间才有双向的服丧义务(不过与她为他们服的等级不同)。男女主人都不为妾服丧,即便她生了孩子。
更复杂的问题是妾的孩子为她服什么等级的丧。这些孩子为父亲的妻服丧,是在为法律上的母亲服丧,与妻生的孩子一样。但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孩子们对法律上的母亲比对与父亲有瓜葛的女人更尊重,后者包括孩子的生母、离婚的出母、奶妈和保姆。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只能为一位作为母亲的女人服丧。如果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后,继母也去世了,那么儿子应该为每一位法律上的母亲服丧。儿子为身为妾的生母服什么等级的丧,在宋代没有统一认识。张载(1020—1077)说只有在法律上的母亲活着时,儿子为生母服低一个等级的丧。朱熹在回一封信时说,张载认为,为生母服较低等级的、专为“妾母”制定的丧,这是错误的;她是他的生母,他就应该为她服3年丧。
妾在家里的地位毫无疑问取决于女主人是否健在。即便妻子活着,但是如果她没有能力,妾就可以像家里的女主人那样行动。宋朝末年,朝廷规定,如果妻子病得很重而丈夫又不愿休掉她,男人可以按照通常的婚礼礼仪娶一位“小妻”。但是无论用什么称呼,法律上不是妻的女子都是妾。刘克庄(1187—1269)的一项判决涉及两个被家人视为身份相当不同的女人——一位在男主人活着时就管理着一切家务,并瞧不起另一位;另一位是主人儿子的妾——但是刘克庄说,因为两位都没有正式结婚(“非礼婚”),因此都不能被当作妻子。有女主人的妾不仅在人身上依附于她,还会失去与孩子间的大部分联系,而由女主人掌控着孩子。妻子的传记经常说她们养大了妾的孩子。但是从未提到这种意思,即她们应该事前请求妾的允许。舒岳祥(1217—1301)形容他的妻子王氏(1212—1284)如何“性多容少妬姬。侍生子抚育如己出,寒暑燥湿一皆共之”。很容易想像妾对妻照管她的229孩子怀有什么样的仇恨,绝不会认为是对孩子的爱和慈悲心。
妾的边缘位置可以持续到死后。在父亲、法律上的母亲和生母都死去很久后,韩琦(1008—1075)在新的家族墓地重新安葬了他们。他采取大胆步骤,把身为妾的生母葬在父亲与法律上的母亲的合葬墓的一侧,作为“侍葬”。他声明这样做没有冒犯父母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事,比如棺木的质量,下葬的仪式,都是按照比父母低一级的规格办的。考虑到其他人会谴责他失礼,他说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捍卫自己,“夫礼非天降地出,本于情而已矣”。
洪迈记录的下面的故事清楚地表现了妾在家庭里的边缘位置:
第十三部分:妾妾 6
朱景先铨,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马。男逊,买成都张氏女为妾,曰福娘。明年,娶于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强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离成都,福娘欲随东归,不果。后四十日,生一子,小名为寄儿。
朱居姑苏,吴蜀杳隔,彼此不相知闻。庚子岁,逊亡,范妇无出,朱又无他儿,悲痛殊甚。乙巳岁,朱持母丧,后茶马使者王渥少卿遣驶卒赍书致唁,卒乃旧服役左右者。方买福娘时,其妻实为牙侩,因从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后,甘贫守节,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岁,从学读书,眉目疏秀,每自称官人,非里巷群儿比也。”
朱虽喜而未深信,其与卒携来者巡检邹圭,亦故吏,呼扣之,尽得其实。即令圭达书王卿及其制帅留尚书,祈致其母子。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妾,方便的时候可以有,不方便的时候可以丢掉,如果家庭后来需要她生的孩子,还可把他们要回来。
为母的妾
230生儿子提高了女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不管这个女人是妻子、妾还是婢。对妻子而言,生了儿子就去掉一个可能休弃她的理由。对于妾,生了儿子就可以确立她与主人家庭成员间的亲属关系。对于婢,她得到了升格为妾的机会。进一步而言,如果妻子已经有了孩子,生儿子会使妾卷入与妻子和她的儿子之间更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司马光写道:“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异母或前后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异党。”
妾的儿子肯定经常发觉自己面临的形势比较混乱,压力比较大。一个妾的儿子毕竟要对两位女人尽孝,而她们之间多半不太和睦。此外,他的父亲会视他的生母为妓女,而他法律上的母亲则认为他妈妈是婢女。不幸的是没有史料可供分析所有这些引起的心理后果。当然妾的孩子们会长大而没有明显的社会和心理的残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高官之一——韩琦,就是妾的儿子。他父亲韩国华(957—1011)的妻子生了4个儿子,第三个生于989年。那时韩国华多半已经有了妾——胡氏(968—1030),胡氏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韩琦出生时父亲52岁,父亲去世时他3岁。身为妾的生母在韩家住了几乎有二十年之久。韩琦被两个女人养大,很有些像被妈妈和奶奶同时照顾的小孩子。韩琦写道,无论何时生母打他,法律上的母亲都会站出来保护他,并且气得一整天都不和他生母说话。
然而,很多孩子恐怕不这么幸运。比照妻子生的孩子,妾的孩子似乎更可能被牺牲因而更可能被送给别人当养子,或一出生就被溺死。陈亮(1143—1194)父亲的妾1160年生了一个男孩,3个月后就送人了。同样,刘宰(1166—1239)的一个妾生的弟弟,很小就被送给别人收养。第9章提到的几件杀婴事件涉及的就是妾生子。父亲抛弃了为妾的母亲,孩子也跟着屡受磨难。官员和商人们离家在外时纳妾陪侍他们,待到离开那个地方时就把妾遣散的事也不是很少见。他们还会因妻子的嫉妒赶走妾,哪怕她已经生了孩子。这些妾的孩子经常失掉与生母的所有联系。
231儿子与被父亲排斥的妾母之间的关系在11世纪末期引起较多讨论。当王安石(1021—108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