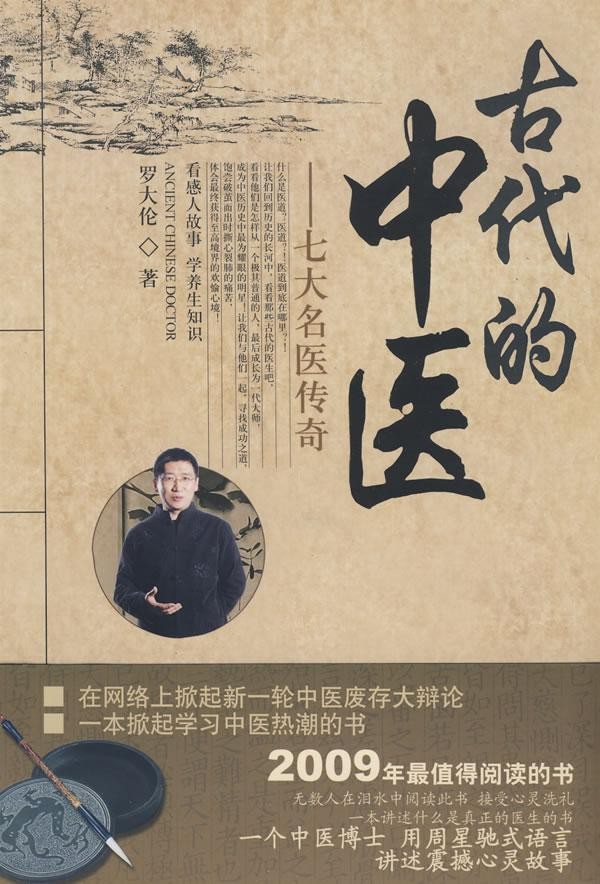����-�δ��Ļ����븾Ů����-��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ʹ���ǿ��������ᵽ�����Ӻ�Ů������Ȩ���Ŀ����ԡ������ܹ����ɳ����Լ�ӵ�еIJƲ���û�ж��ӵļ�ͥ�ɰѲƲ�����Ů����Ů����Ů������ִ��һ��ָ������ִ�е��������������ᡣ�������Ҳ����˷���ij�ͻ��������֪�������������ɷ�IJ�ͬ��������ͬʱ����Ҳǿ������Ҽ�ֵ�۵����ԣ�ƫ��ͨ�������ϵ�Ŭ�������ͻ��û�����ּ�ֵ�ۣ�Ů���Ͳ���Ѹ�ĸ������һ�𣬺����ȷ����Υ��˫�������˵���Ը��������ǿ���������ȫ��ͬ�ġ������ϵ���ʵ�������˵�ǿ����Ů�˵����Ƕ�ı����������������ĸ�������ں��ӵ����������������������г�Ļ�����ĸһ��ļ�ֵ�ۡ���������
������������������������ɼ���������ȵĹ��¡�����ͨ�����͡����С�������ż�������ˡ����ط���ʱ��ͬ�µȸ������ռ���������¡����ļ�־���ִ�汾��2��692�����¶������е��������ɷ�����ij���������棬����������ֵ��¶������ڼ������������¶��һЩ��ͥ����Ļ��ơ������Ĺ���û������ѵ�����ģʽд����Ҳ�������ܻ�����ͨ��˼�����ì�ܡ��������ǰ����Ĺ��½��Ϊ�����鹹�Ĺ����£������������ǵ�����ʵ������ʵ�ؼ�����������Ҳ�������Խ��͵��£���ȴ�����������˵��¡���������
���������������������������д�˸�Ů�����С���¡����кܶ�����������Դ��Χ�������˵���̸����̸����֤ϸ�ڵľ�ȷ�ԣ���Ҳ������ʷ���塣Ϊ�����۶Ե¸����ص��˵���д�����ǻ���Ҫ֪��ʲô���Ӳ�����ϲ��������ʱ�ˣ�������֪�߳ܡ��������¡���̸������ʱ���ⷽ����б����������ǻ���Ҫ���и�֪����˵���ǶԲ��õ���Ϊ���˺����Ľ��͡��������ᵽ�Ļ��������ڶ����˽�����Ϊʲô����檸�������Ϊʲô�뿪�ɷ�������
�����������ܣ�1232��1308����¼��һ�����ſ��Ե���������ϵĵ��͡����Լ鳼�����У�����1207������������˷��顣��������
��������13�����ӳ�Ϊ̫ѧ��ʿ����һ����ж��������ڣ���֮Ů��֮�ҡ��nƽԭ֮��ͬ�磬��֮ͬ�������ӣ���������������⣬���������֮��δ�����У���ƽԭҲ����������
������������������µ��˶�֪�������еĸ�����Ҫһ�����ӣ����ѻ��е��Ů��Ϊ�õ����ӵĻ��ᣬ������ӿ��Ա��������������������ǻ����������µ���ʵ�ԣ�����ʱ���˲������ɣ���ȷ����������ʱ���ռ�¼�ڡ���ʷ������������磬���̣�890��966���Ĵ��Ǽ�¼��������¼�������������
��������������Ϊ��У����ƽ½�������ƣ���������Ϊ�榡��̼ȹ��˱��ˣ��˲���ƽ��������������Ի����������֮����������ˣ���Ի�����ҷ���ҽ�����Թ�����ʱֹһ�ޣ��������ڣ��÷Ǵ��㿷֮�����·�������ɼ�Ү�����ܳ�ȥŮ�̣�����֮����������������Ϊ���������������£�Ϥ��������ޡ���������
�����������������ر������ڶ��쵱���˶��Ժ�������������ʵ�뷨�������ϲ��������Ů���г��Ĺ�ϵ�����ǿ���������Ů����檣��������д��Լ��Ŀ��ˣ��������Ʋ�ס����ʱ�����뷳�ա����ǿ����������Ʋ�ס���ʵ����������������븸����в���֮�С����ǻ������²���ĸ�ĸ�װ�����϶�Ư��Ů�ӵ�������������;����������Щ����ʹ�����˼���һЩ�Լ�����ᣬ��������Ů�˹�ϵ�����ڵĴ�����Σ���ԡ���������
��������
��һ���֣�Ŀ¼���ԡ�6
����������ͳʷ��Ҳ���Ե����ض���Ů������ʷ�ϵı��⡣����˵�����������������������ж��ٶ���ʱ����ٸ��ļ�ͥ���װ�����������Ϊʿ�˵��й�д�����������������и��ײ����ͨ�ˡ��뱾���ϵ���еİ����������漰���ף�ȷ�������ĺϷ��ԣ�Ů����14���ӺѸ��Լ�ױ�������Ʋ������Ѹ�Ҫ�����̺ʹ���������ͥ�����Ȩ�����ȵȡ���������
�������������ļ����д�����Ĺ־������Ϊ�������֣���ЩĹ־����ѭ�̶��ĸ�ʽ�����Ҳ��ҵ��ǽ�����Ϊʿ�˽ײ��Ա��д��ÿƪĹ־�������Ĺ���Ļ���������������ꡢ���ȡ��������ڵء���ż�����á��Ը��ܺ�����Ĺ��ͨ���ǹ�Ա�����ǵ��С�Ů���ݣ��ܶ������������˵�������ѣ���Ϊֻ�����ǵ��ļ��Ż�ܺõر�����������������
�����������ˣ�ż��Ҳ��Ů�ˣ����Ǿ����������Լ������ѹ�Ů�ˡ���ĸ�ס����á����ӡ�Ů�����ϱʱ�����̻�������Ҳ��ӳ�������Լ��������ݡ���Щ��Ϣ��һ�����ó�д�������ˣ�ͨ����һ�����ˣ���֯�����룬�����Ȼ��Ȼ��մȾ��Խ��Խ�����ѧ��������ɫ������Ĺ־����ȫ����ѧ��������д����֪��Ĺ����˭ʱ���ر���д�Լ���ĸ�ס����Ӻͽ���ʱ�����ߵĸ����������¶���������磬��������ܻ���ʵд�������ϸ���������̺��ŷḻ��ϸ�ڣ����о�����Ϊ��Ů��ż�ı��dz����á�Ĺ־��Ҳ�ṩ���δ��������ü�ֵ�Ŀɿ����ݣ�����䡢��Ů���������������˶�á��Ӷ����ꡣΪ��������Щ���ݣ����ռ��ɷ�Ĵ�������Ҳ����������Ů�˵�Ĺ־�������˴������������ҵ�189��˫�����д������ϵķ�����˫���������м�¼����166�ԣ���ʹ���Ǹ��������������á�166�Ե���135�����ɷ��ԭ�����ӣ�31�����ɷ�͵ڶ������������λ���ӡ���������ĸ���ͳ�ƶ�Դ����Щ˫�����м��صķ���������
����������������һ���dz����͵�Ĺ־����ǰһ�룬�ɺ�Ԫ����1118��1187��Ϊ���˵�ĸ���Ϲ��ϣ�1094��1178��д����������
���������ٹ�̫�����Ϲ���Ĺ־����������
�������������Ϲ��ϣ�����֮����Ҳ������֮��������ѧ��Ϊ���д�������ˣ�ʼ�����š�����������ר��������Ц���д�֮���������á��ʻ������ɼ���������̫ѧ��15������ߪ�ڣ����˹��ɡ����ɼҴ���֮��Ȫ����¶�ƶ�����˲�������˹ã�����ʱ�������Ƽ����ޣ��ؾ��Խࡣ��������Ľ����������ߡ���̾Ի������Ϊ���Ҹ���������������Ҳ����������Ϊ��Ӻֱ��������֮���в����ߣ�����������ƽ��֮��ɽ������ɮ�¡������˸�飬����֮��»���������������ˡ�������Ի�����Ḹĸ�������ߣ���Ϊ������Ҳ�����ɘ����Ա����ᰲ�����ɣ�����������������ɽ�����������������㣬��®����֮��Ի�����º���֪�Ծ��ã�������ԤҲ�������Ǽ���֮����С�ԳƷ���֮�ͣ��ҷ���ʶ������н�ܲ�������Ĺ�֣�Ի�������Ϲٷ��˴�Ҳ���������Ի������ƣ����Թ��ݡ������꣬��������ӣ�δȥ����⡣����δ�ڣ����˻���ɥ��������ǧ���y��ƽ֮�㣬�����������Ѷ���ȻԻ�������ڼ������ӣ����������ӣ�ʹ�ó���ʿ����֮����Ȼ����������������Ḹĸ����������Я���ӣ��о���������д�ʱ�д����ӽ�������Ψ�����ڡ�������������ף�����������ϰ��ҹ�����£�����Ϊ�����д�������ˣ���Ծ�ʮ���ա�����ʼȥ����֮�ᣬ���ҿ��ǣ��۾�ʮָ���������ڣ������ܳƣ����������ʷ��ǧʯ������ʮ�࣬����������Ԥ��������������ˣ��������ţ�����ָΪ���¡�Ȼ����ʮ����䣬������ǰ�䣬����Ϣ�������ҡ��������Ѱ�ʮ����������ǣ�16���������ٹ۸������飬��Ȼ��������֮�ۡ�����֮Ϧ������С�����̺�Ŀ�������л��Ͼ���������һ��������������
�������������ļ�¼���������Ժ�Ԫ����д���Ϲ��ϵĶ����������д�����ģ���������˵���ϵ���������Ľ�������¡���Ԫ������ϸ�ؼ�¼���Ϲ��ϵ����桢4�����ӵ�������ְ��16�����Ӽ�8����Ů������������������
��������������Ĺ־��һ������ƪ���ĸ�Ĺ���������൱�ߡ��Ϲ���ӵ�й̶�ģʽ��Ů�˶������£������Ӳ�����˵Ц���������������һ��ҵ����ݵİ����м����������ҲΪ����д���ṩ�˺ܶ��м�ֵ����Ϣ��������Ԫ�������˷�����˵��澳ӡ����̣�����Ů���ܽ������Ի����Ŀ϶�������������֮�ڶ��ӵĽ���ʱ������Ϊ�������ʱ���ܱ��о��ĵ�Ů��ֵ����Ľ����Ϊ�������߿�����Ϊ�����ڽ����衣�����ܶ����������ĺ����Ǿͻ��˽�����������߶�Ů�˵�������������Ϊʲô���ر𣬵������뵽��ͥ����ʱʲôʹ���Ǹе���ů����������
��������������Ȼ��Ϊ��Щʷ��¶��ԶԶ��������ԭ�����۵���Ϣ������������Ϊ������д�����Ϲ���һ���ش��¼��ľ���ϸ�ڡ����ڱ��鲻���������������������磬������һ�������˲�ͬ����֮��Ļ���ĸ�����Ҳ��40��45��֮������ĸ�����������������һλ��ĸ�Ҿ���ԣ��������̡������ɷ���εط��ٵ��ܹ�������Ů�Ե����ӡ������Ĺ־�����ǿ���Ԥ�����������Աȷ�Ҹ���ԣ�ļ�ͥʱ�����ʲô��������������ü���ʵ����Ĺ�������ļ�ͥĿ�ꣻ����������ɥ������Ů�����ס��ȥ����������
��������
��һ���֣�Ŀ¼���ԡ�7
����������Ȼ������ʷ�Ϻ��ѶԻ������з����о���Ҳ�������ҵ��������츾Ů�����;���������ǽ����ᄈ�����ָ��Ӷ�����Ωһ��·�����������ܺͺ�Ԫ������˾�����Ԭ�������ģ�����д���������Ѹ���������¡����ǵĸ�������Ϊ�˽����ǵ�˼�����Ȥ��֤�ݣ�����Զ��������ض�Ů�˵Ĵ������ϼ���Ů�����ض����������������Ĺ��״����ܶ�����ʷ���Ժ��ҷ���һ�����δ����ߵĸ�������������ʵ�ģ�17���ںܶ���������Ǻ�����һ����Ҫ���֣������巢����ʲô�����磬�ӽ�ƫ������������ĸ�ĸ��飬����Щ��еĽ����ڸ������ı�����Ա����ԣ��������ض�����Ĵ���������ȴ�����ظ��ֳ���������������
��������ʷ������ڽ�������Ա��ƫ����������
����������ʹ����һ����һ�����Ի�����ʷ�ϣ�������û�ж��Ҵ����ٵ�ÿ�������ṩͬ�����֤�ݡ����ֱ���Ů�Ժͻ�����ʷ����ࡣ�漰���˺�Ů�˵�˼�롢�������Ϊ��ʽ��ʷ��Ҳ�ܶࡣ�ᄈ�����⡪�����ֻ������������ж�����Ҳ�ܺõر��������ˡ������ж�ʵ����ij����Ϊ�ķ����ʼ����Dz����ܵġ�ʷ�ϳ�������˵һ���ж��dz����ġ����dz�����ͬ���¼����������Ѿ�����ʶ���ģ����Dz���˵��������һ���ط��ٷ�֮ʮ����ʮ����ʮ���ˡ���������
�����������DZ�����ʶ��ʷ������ڵĽ���ƫ�����������õ�ʷ�϶���дʿ�˽ײ�������ˣ�����������ɰ����еĵ����ˡ����������������µ���̸���Ĵ�Լ����������ͨ�ˣ��Ȳ��ǹ�Ա��Ҳ���ǹ�Ա�����ݣ�����Ҳ��һ���ܹ����������������������ˣ������Ӷ��һ���ֲ�ʶ���й��е�Ů�ҵ���������ͨ�顢���ס���顢�Ѹ����������ٻ�ĹѸ���ϸ�ڣ���������������ص��С����֮�£�Ĺ־����Ϊ�ܹ����֤���й�Ů�Ե����������µ�ʷ�ϣ������ľ������������ʿ�˼��������ߣ�����檡����衢��ķ�����������ȫ���ԳƵģ������������Ů�˵����϶������ϲ����Ů����ļ���ʷ���У�Ȼ�����ڲ��ҵĻ���������ӵ���Ϊ�Ͳ��ҵĻ����ļ��ض���������ͨ��Ů�������������
������������û���˻��϶��������µ���ȫ��������ѧʿ�����������Ϊȫ���������ˣ��Ҿ����Ŭ��������κ�һ����Ϊ�ͽ��Ļ�������һ���෴���Ұ��������ϵIJ��Գƽ���Ϊ���ġ����֡�������ʿ�˽ײ��Ů�˾������¼�ǿ��ʿ�˽ײ��Ȩ����������������۵Ļ��Ᵽ�־��룬��ôͨ�顢���Ȼ����Ƚ�����̸�𣺡�������Ϊ�ǵ��¹���淶���˵�����ⲻ����˵��Ϊ�ͼ�ֵ�۵���û�н��IJ��졣�ж�ũ���Ƿ����������ʱ��18˳�Ӻ���̬��ǫ���Ͳ������ϲ��Ů��������ô��Ҫ��û�в�����檵������ݵ�û�����ӵ����ӻ�����̫�����¶�����û����������˱ȼ̳������ص����˸����ܸ����ֵܺ����ֵܵ����������ļ̳��ˣ�Ȼ�����Լ��Ķ��ӡ�����ʷ���д���ƫ����ʹ֤ʵ��Щ�����֤�ݲ��õ�����������
��������ʷ�ϸ����ص���һ�־������������Ǽ�����������д�ġ���Ωһ����ȫ����Ů�����������գ�1084��Լ1160�ݣ����齫�����ᵽ�����������±���Ĵ���ǰ��顢���˺;������漰�������ϸ�ڵ�ʷ�Ϻ��١��������ߵ�Ȼ����Ů�����������⡣û��һ�����������ŮŮ����״̬���е�Ů�˻�����ֻ��Ů�ˡ��ر�����Ϥ��Ů��Ȧ���������ж��������ڳ�ʱ��Ů���ƺ���ȫ��ͬ����ֻ��ͬ��ʱ��Ů�˻���ǵ������˵��Ը���ƫ������Ц��ȡ�֡�һ����й�ũ�帾Ů������ѧ�о����֣�Ů��ֻ�������˲��ڳ�ʱ��Ը������Լ�Ҳ��Ȩ�������⣬�й�Ů������Ļ��⡪���¾������С��Ե������������ϡ����϶���ֻ��Ů��ʱ��������Ů����ʱ̸�۵ñȽ϶ࡣ���磬Ů�˻�̸����Լ��ĺ�Ů���Ľŵ��£������˵ļ�¼��û����Щ�Ի����ѵ�Ů��û��̸���ճ�����Ŀ��ֺ��������ӵľ��飿���ǣ��������˽�ֻ��Ů��ʱ����˵ʲô��д����Ů�˺ܴ�̶���ͣ�������˶��Ļ��⣬����ֱ��Ĺ�Թ��������Щϲ��Ů�˵���顢��ĸ�ס����Ӻ�Ů���Ĺ�ϵ���е����˿���ʮ��ͬ�顢��ʵ�ؼ�¼���ǵ��������ţ��������Կ��ܻ�������;˵����Ϣ�����������������ַ���Ů�˵�Ʒ�й��Ϊ�õģ��º͡��ɰ����ɿ����������Ϳ��µģ����ʡ����¡�С���������Ļ�������ڲ��ܷ���ʹ������ô����ɰ���ʹ����Ů�����Σ�յ����ֹ�ͬ�㡣����Ҳ��ϵ������Լ�������ʷ�ϵĽ��Ӧ���ƽ������֧��������������ʷ�Ϸ�ӳ���ǵ����������ڱ����������۾��ǣ��ҵ���������ǵIJ�ͬ�����������������۾��ǣ��δ�������֪�����ǵ�������ĸ������飬����ȴ�����͵����Ų��ܵ�֪���������Ҷ�ʷ��ʱ���ֱ��Լ��������յ����ҵ�������ܵ�̫Զ����ϣ�����ܹ��ﵽ������ƽ��㡣�Һ����ѵ�֪����������Ľ�ʾ����״���ķ�ʽ�������δ�����Ů���ù���19�����Ҿ�������ʷ�ϣ���ָ��ʷ������˭��ijλŮʿ��һ�������ϵ�Ů��˵��Щʲô����������
��������
��һ���֣�Ŀ¼���ԡ�8
����������ʾ�����͡��仯����������
���������ᴩȫ��������DZ仯����Ů�����ٵ�����ͨ��ʲô��ʽ�����仯����ν����Ѿ������ĺ�û�з����ı仯�������ƴ���ʷ�ϲ����δ���ô�࣬���Ҳ�һ���߿ɱ��ԣ������Ҫ���Dz��ܹ��߹��Ʊ仯�ķ�Χ����������Ϊʷ�ϸ������ζ��������Ϊ���ࡣ�����ǹᴩ����һ���ı仯Ҳ���ѳ��֤ʵ����Ϊ���Ǹ���ʱ�ڶ��߱��㹻�����ʱȽϵ�ʷ�ϡ����еķ����о��鼸������13�����Ժ�ġ��Ƚ�֮�£����ɺͷ��������ȽϿ�ǰ��������������ּ���¼������ʶ11����ĩ��12�������á�����ʹ���Ǹ�ʱ�ڶ��е�Ĺ־����ҲӦ���־��裬����֮��IJ�ͬ��һ����ʱ���ı仯�йأ��෴�����ǿ��ܷ�ӳ�˽��������IJ�ͬ��Ҳ���ܷ�ӳ�˸��˱����е�żȻ���أ���ɥż���䣩���µIJ�������ʹȻ�IJ��졣����м�ǧ���������ҿ���ͨ��ͳ�Ʒ����ų�һЩ�����ԣ�����ֻ�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