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那些回忆,或许搞笑,或许悲伤-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半年多后,有一回聚会喝酒时谈起这个人,大家又说起那次的事情,越说越觉得事情有些诡异,特别是在我提示下。那个好事的兄弟立即掏出手机给他电话,接电话的是他母亲,说这老孩子病了,已经住院几个月。
大家都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好占小便宜的朋友身材魁梧健壮,不像那种会病倒的人。那天的酒喝的没了味道,分手时约好第二天去医院探望。结果第二天去的人却只有三个人,其他人都有种种理由,说白了是怕他的病会传染,更怕是因为半年前的那件事里有什么不可知的东西作祟。
我们到病房后,看到那个朋友已经瘦的不成人形,两眼目光散淡,像是随时都会熄灭。他看到我后立即便出骷髅般的手抓过来,紧的让我都有点痛了。
即使没什么智商的人也能看出来,他命不久矣。
朋友抓着我的手泪流满面,说悔不该贪小便宜,接了那个电话后动了心,结果现在什么都要没了。朋友的话不明不白,可我还是听出点什么。可就在他要说出接了那个电话后发生的事情时,他的心跳开始紊乱,护士用美丽的大眼睛瞪我们三个。
在护士走后,朋友才接着讲下去。在那天夜里他回到家,又接到那个电话,对方问他真的想好没有,朋友本着有便宜不占的原则,说想好了,电话里的人便说那明天就把东西送到,然后又像是忍不住的笑,说世间要那东西的可没几个,当真有趣的紧。第二天他害怕了,本不想去,结果没料到我们这堆损友逼着他上路了。
没错,就是上路了。
在约定的时间到后没见到一个人影,可他却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他的身体。那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滋味,朋友说就像是整个太阳坠了下来,生生挤进他的血肉之躯。等到那东西完全进入他的身体后,他终于明白了那是什么。
但是,就在朋友要说出那东西是什么时,他的心跳已经快到危险的地步。护士看不下去,把我们三个好心人哄走了。
外面阳光很好,可我们三个却感到浑身发冷,有什么东西紧附在身上不肯离去。
几天后,我们决定再去探望他时,却收到了他的死讯。
人都有一死,可像他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死,却让人想要远远逃开。
我曾说过,有些事连我也要远离,而这个好占小便宜的朋友的死,就属于其中。只是,我还说过,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在这个朋友去逝后不久,我去了他家。说明来意后,老阿姨让我自己去他的房间。
房间里的墙壁上到处都写满字,不过一个都认不出来是什么,他的日记只简单记着进入到他体内的东西是死亡。
事情太过诡异,在离开朋友的家后,我便告诫自己不再查究这件事了。
七十二:少年事
曾经有一个同学,就坐在我后边,是个让人喜欢的奇怪的家伙。他的同桌是个胖胖的不怎么漂亮的但却有着阳光般灿烂笑容的女孩,也很招人喜欢。
那是中学的故事,所以少不了年少时无聊的骄傲和小小的浪漫。
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不过不打算在这里写出来,所以暂且起两个正经的名字,以示友谊地久天长。咳咳,就叫:于凡名,孔少芬。
我记得,中学那许多学生看琼瑶走火放魔,叫人都只叫名不叫姓,于是乎,教室里一片阿虹、阿鹏、阿雷、阿……以至无穷。我常想,如果某个丫头的名字只有一个蝶字,那叫起来岂不成了阿爹?当然,除了阿派,还有单纯的名派,所以这个故事里没有阿什么的鸟物,只有凡名和少芬。
现在开始这个故事吧!
凡名和我一样有鼻炎,而他从不因为上课而减轻发出音量,所以少有老师喜欢他。不过凡名是个心胸开阔的人,根本不把别人的喜恶当作自己行为的规尺,我行我素。按说这个样子不该有女生喜欢他,但总会有例外,少芬即是。
少芬喜欢凡名很久了,那还是刚入学时的事,有一回少芬被几个同学嘲笑长的胖,那几个同学用词恶毒,口水上达列祖下通万代,少芬被气的粉拳紧握。就在这个血案一触即发的时刻,流着鼻涕的王子出现了,他首先用一块蘸满浓浓黄色可疑液体的卫生纸解决叫嚣最凶的家伙,然后跳进圈内,只见他嘴唇翻动,立即有无数不带一个脏字的国骂汹涌而出,集中华五千年历史精华于一嘴,单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将几个同学镇住了。那一刻,他就是国骂界的奇葩,那一刻,他就是新中国外交界未来的希望。骂退同学们后,凡名孤独的走开了,对于少芬的感谢,他只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块卫生纸。
从那后,少芬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流鼻涕的黑马王子,默默的坐在他身边,从初一直到初三。
众所周知,我是个喜好观察的人,所以早在少芬还未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前就已经发现了她心中的秘密,例如少芬经常看书时微歪着头看凡名,课间休息时总缠着凡名讲故事,或问化学题,其实都只是借口,少芬只想和凡名呆在一起罢了。老师提问时她的眼睛里有紧张有关切,如果答错了,她就会第一时间写下正确答案给凡名看。
如果你问我是前排的怎么会知道后排的事,咳咳,整天转着脖子是件很辛苦的事,更不用说上课这么严肃的时刻,我还冒着被点名的危险在扭头观察一个暗恋中的女同学和傻蛋男生的心理变化……
时光荏苒,两年的时间飞快的过去,初三了,我们面临分别。
虽然两年多的时间里,凡名一直大大咧咧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事实并非表面那样,凡名也有一颗容易感动的心,他早发觉了少芬的异常,可却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逾越的举动。初三了,少芬被保送高中,凡名则选择了所技校,两个的世界注定交错而过。
前面说过,凡名是个骄傲的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在克制自己。
前面的故事里还曾说过,我是个热心的人,看到一个煎熬的少年和被相思折磨的日渐消瘦的姑娘,我的爱心又泛滥了,于是心生一计。
那是毕业前的事,有一天我单独和凡名在操场上聊天,说到同学之谊,说到可能存在的初恋。我蛊惑凡名少年人不犯点少年事简直就是没有少年过,而什么样的事算是少年事呢?恋爱,人生最美好的初恋。
凡名心中的火被我挑动了,坐在操场上发起呆。
我又跑回教室,和少芬谈,我说曾有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但因为他们将来可能处在不同的世界而选择了沉默,可是他的内心还是喜欢这个女孩的。我问少芬,如果她就是那个女孩,应该怎么办?少芬红了脸,目光由迷茫到坚定,她说爱情是不分贵贱的。我深沉的点点头,立即窜出了教室,冲到了凡名身边,对他讲了对少芬讲过的话,然后又把少芬的选择告诉了他,凡名的脸也红了,他不再迟疑,让我转告少芬,放学后在校门口见,一起到山顶的小树林谈谈。
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把凡名的话转达完时,上课铃响了。
那天放学后,凡名和少芬在校门口碰面,然后一前一后去了山上。我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后,立即飞快的抄小路直奔山顶。
我前面似乎大概还说过,我嗜好看热闹,特别是自己充当红娘亲手撮合的事,不看眼死也不会瞑目。
我在山顶宜人的小风中伏在草丛中,不多时,凡名和少芬出现了,他们首先进行了翻羞羞答答的告白。我一直没想到凡名竟然如此肉麻,比我写酸诗时肉麻百倍不止。然后两个人的手牵在了一起,对着落日发誓永远都在一起,不离不弃。
在他们走后,泪流满面的俺走了草丛,身上裸露的地方布满被蚊子亲出来的包,当红娘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可是第二天上学,凡名和少芬竟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两个人,两个世界,直到毕业,凡名去了技校,少芬进了高中。后来又过了许多年,有一回碰到少芬,那时她大学退学在家,说起过去的事,满脸是泪。她说凡名的心就像是块铁,那天在去山顶的路上,凡名说现在年龄还小,不应该考虑这种事,然后转身就走,对于少芬的呼唤只是挥了挥手。
我愣住了,这怎么可能?我明明看见听到他们俩在山顶的告白,还有夕阳下两个少年恋人的背影。这么浪漫的场面我怎么会记错?我说了那天的事后,少芬一脸困惑,因为她也曾有过那样的梦,和我说的分毫不差。
那天的事真的没发生过?可为什么少芬会有那样的梦?或许凡名还是喜欢少芬的,两个人虽然没到达山顶,但他们的心还是去了,表白和许下誓言。
人生有太多无奈事,或许有时,不该深究。
七十三:圣痕
曾经认识一位天主教的信徒,是个小男孩,六七岁,天真烂漫很是可爱。
那时偶尔去教堂听传教,我不是天主教徒,但对《圣经》很有兴趣,所以有意旁听。我要说传教士的言论非常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再加上教堂那五色的琉璃折射进来的光线和肃穆神秘的气氛,使人不自觉的想要匍匐皈依。传教士还十分注重新人,对每一个新人都要特别关照。
我就曾在传教后被拉去做特别传教,那位老人家握着我的手,直视过来,说事就要成了,凡天底下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如果不是我意志坚定,大概这会就是个天主教徒了。
那个小朋友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当时是随姥姥去做礼拜,稚嫩的面孔虔诚纯洁,一举一动都透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我当时就想:这就是个未来的圣徒啊,最不济,也能成圣骑士。圣徒啊,圣骑士啊,那是什么概念?这样的朋友要交就要乘早,晚了再没机会。所以我就扑了上去。
只可惜,现在连他的名字叫什么都忘了。
小家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父亲是个水手,死在海上,母亲是医生,很少有时间照顾他,可小家伙从小就懂事,不哭不闹,特别喜欢姥姥带他去教堂。有回一位传教士提出一个问题,在场所有人的回答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个时候,小家伙开口了,他的口所说便如天父的口述,那位教士惊讶不已。又有一回,传教进行到一半时,小家伙被请上讲坛,按自己的理解述说天父的意,几名旁听的隐修教士听的泪流满面。
故事到这里,大家大概已经在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有前途的人,在天主教中却默默无闻?那和我多少有点原故,是我让他隐藏在人海中。
有一回去教堂时在门外遇到小家伙,他怀里抱着个布娃娃,安静的跟在姥姥身边。虽然小家伙只有七八岁,但不管怎么是个男孩,而且心中有天父的存在,抱着个娃娃实在不像回事。我问小家伙抱个娃娃干什么?要请天父施展神迹,让娃娃活过来?我是在开玩笑,但小家伙很认真的点点头,然后把娃娃递过来。我一看,心中立即就是一惊,因为布娃娃的两只手掌心各有一个洞,边沿有点点血迹。小家伙说那是圣痕。
是圣痕,圣痕居然施展在了一个布娃娃身上!
或许有人不明白圣痕意味着什么,那是耶稣殉道时被钉的伤痕,肋下还有一处刀伤。只要信奉天父的道,就都对圣痕异常看重,全世界被宣布是真正圣痕的人都将成为圣徒。
可是现在,圣痕居然出现在一个布娃娃身上,这怎么可能?
我拉着小家伙远离教堂,问是怎么回事,小家伙说他晚上抱着布娃娃睡觉时突然听到声响,一个声音对他说:时间要到了,天父的国将重临人间。当小家伙醒来时,发现布娃娃落在地上,拾起来时看到布娃娃的掌心出现了两个洞。小家伙立即就知道了,那是天父留下的印迹,是圣痕。
小家伙信誓旦旦的说,可我清楚,如果他的这些话到了教堂里说,那将被当作异端。虽然不至于被处以火刑,但从此再不得进教堂是肯定的。圣痕啊,天父会把圣痕降在一个布娃娃身上?这简直是天父的亵渎。
就在我给小家伙讲解为什么不能进教堂时,天突然暗了下来,小巷子里涌起狂风,我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布娃娃飘到半空中,我仿佛听到了什么,有哭声和神圣的说语。小家伙说天父来了,然后虔诚的跪下,聆听天父的道。而我,抱着根柱子,在狂风中飘摇。等到风停下时,天空突然亮了,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小家伙拾起布娃娃,递到我面前,它的身上一次性补齐了全部圣痕,鲜血淋漓,让人心惊肉跳。
圣痕,那真的是圣痕。
小家伙说他听到了天父的声音,天父向他说了许多话,确切的说,是向布娃娃说了许多的话。我眨了眨眼,心想这世界乱了套。不管怎么说,小家伙不可以在教堂说他向我说的话,那太危险了。
小家伙问我该怎么办,我以一个智者的身份教导他,找个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用心感受天父的话,直到时机到了才可以再出来。小家伙点点头,这时他姥姥找来,小家伙把布娃娃藏进怀里,顺从的去继续做礼拜。我则匆匆离开,从那时起就再没进过教堂一步。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网上查中国的圣痕事迹,没有发现与当年有半点关系的事,看来小家伙一直按照我所说的隐藏自己,成了一名隐修士。
只是,布娃娃身上出现的真是圣痕吗?又或者是魔鬼伪托天父所做的手脚?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天上的事,人间还是太平的好。
七十四:倒影
曾认识一个神经兮兮的书呆子,他研究的西方文明里的偏科,是什么姑且不说,大家慢慢看便知。
这个书呆子姓柯,叫什么忘了,只记得曾给他起外号叫马克。马克长的瘦瘦高高,喜欢穿长袍一样的衣服,到了秋冬春就总是一身灰色风衣,手里捧着本厚厚的书籍,风衣里还总插了根短细的桃木棍,一端镶嵌着难得一见的黑水晶。
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能猜出来了,这家伙自以为是个魔法师。
马克为人孤僻,比我还不爱说话,有时甚至连点头都省略了,只眨眨眼,或咧咧嘴表示同意或反对。不过他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半醉时话就多了。
我和马克并不熟悉,只能算是酒友。马克和其他纨绔子弟一样,家境殷实,所以根本不担心生计,也从没想过正经工作,找了个大企业当图书室管理员。当然,只是挂个名,很少去上班,他只醉心于所谓的魔法研究。
据说马克研究魔法很多年了,也曾在酒桌上公布他的魔法理论。马克认为世界充满魔法的力量,这些力量都只不过是天界在人间的倒影,但即使是倒影,如果人类能掌握其中微小的部分力量,就会成为传说中的魔法师。我对马克的理论感到好笑,如果是倒影,那怎么可能掌握呢?除非让影子的主人按马克的意志行动,那倒影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算确有魔法,马克的研究方向也错了。
有一回聚会喝酒时,他宣布已经掌握召唤风之精灵的魔法,于大家鼓动他表演个。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兄弟们七八人在海边一家酒店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马克说自己会魔法时刚好是傍晚六点,海面上还有残阳的余辉,海波平静,温柔得像初遇情人的姑娘。大家喧嚣簇拥着马克到了露台,我也挤在中间,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魔法。马克让大家后退,然后开始诵读古怪的咒语,还拿着他那根桃木棍摇个不停。不过除了本就有的海风外,我没感受到马克所说的那种魔法的风。兄弟们哄笑着把脸红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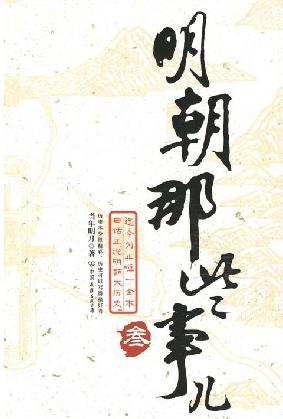
![同学会[番外] 我所爱的那个人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