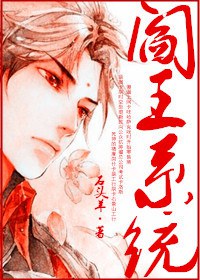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康雍乾-第2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便笑道:“是你在这里?衡臣呢?”鄂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地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答道:“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胤祥知道,鄂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三章谏止,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因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又要奏谁的本?”
“回十三爷,”鄂尔善略一躬说道,“凤阳署理知府李绂,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绂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讳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折子要请张中堂转奏朝廷。”胤祥笑道:“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绂是谁的门生?”鄂尔善看了两个阿哥一眼,不冷不热地说道:“知道,是张中堂的高足。惟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胤上下打量着鄂尔善,三十多岁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竟然敢碰张廷玉的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道:“依着我说,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也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点烦恼不好?”
“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鄂尔善垂头一躬,款款说道:“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愈是自己门生愈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一表率。”
胤盯视鄂尔善良久,见鄂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遂点了点头,说道:“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
到了批本处,胤才知道是施世纶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施来了,都察院右督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施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纶因久不见胤祥胤,请了安,扎手窝脚地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笑道:“老货,你倒结实,吃得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廷玉,你只管下札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说得施世纶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
“就在这里聊聊吧。”胤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个蓝理,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一百多人。蓝理征台湾时盘肠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希福纳就这么难?张伯行奉部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缴印?”张廷玉点点头,说道:“希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施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宪谕,只凭一纸部文,济什么事?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
吏治如此,胤真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地一笑,说道:“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还有验尸的!”
“阿哥爷们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施世纶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辟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项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十八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肉血模糊煞是吓人,其实筋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得不错!”
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纶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胤祥便问:“衡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汇汇总儿。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倒的,可怎么好?”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道:“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待几句。倒是一路关防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捕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使料理停当就行了。”胤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胤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
“四爷,十三爷,”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道:“臣还想问件事。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了毓庆宫太子爷那里?”
胤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答道:“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是我送回去的。”胤祥诧异地问道,“这是规矩。怎么了?”
“没什么。”张廷玉一笑道,“昨日陈嘉猷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才没再问。”说罢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沉吟片刻,问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
胤祥一怔,随即笑道:“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保。这算什么屁事?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揣一叠子回执揩屁股用么?”胤再思量,这事不是大事,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道:“看这天像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件油衣,该回府了。”
深秋季节淫雨连绵,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豪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儿,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传开:“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
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冰炭不共炉,在执政五十一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一致: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胤复立太子连连黜罚保举过胤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晏驾,接踵而来的大变不问可知,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生请见座师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缙绅出面到庙里唱戏,明是恳乞停雨放晴,暗里乞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檀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
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九月十六过去了,九月二十六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启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着称的宰相也梦魂不安一夜数惊。二十六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便见家人进来禀道:“相爷,内廷有旨!”
“谁来了?”张廷玉一骨碌翻身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快快请!”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生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得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硬地点了点头道:“老李稍候,容我换了官服。”
“不必了。”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圣躬安!”李德全顿了一下,又道:“张相请起!”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的,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道:“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齐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里都不知道!”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李德全说道,“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檀柘寺上香乞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澹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说罢换了笑脸,一个千儿打下去,又道:“方才是传旨。这里咱给张相叩安了!”
张廷玉张大了嘴,怔了移时才回过神来,忙忙地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皇上还叫的有谁?”李德全压低了嗓子道:“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皇上召见您,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了!”张廷玉但觉“嗡”地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再不说话,也不乘轿,命人牵马,换了油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腿一夹,那马泼风般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时,还不到戌正,用了半刻的工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说道:“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跟着往里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箭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的竹林茂树,不分个儿响成一片,哨风袭来,冷得人通身寒彻。待到澹宁居前丹陛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时,却是方苞在说话:“先忠宣的忆江梅,主子说注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拘,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注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既是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宁下来,轻咳了一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廷玉来了?”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道:“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趋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儿。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你也有儿女子气?朕这不是好好的么?起来吧!”
张廷玉揩了揩眼站起来,勉强笑道:“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得先谏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点头,说道:“你说的很是,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捕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押解咸安宫暂行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十三贝勒胤祥!”张廷玉尽自心里已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喃喃问道:“不知太——二爷又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八月十二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醮乞福。清场时挖出了魇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致爽斋十几处地方都起出了魇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凌普支使。十三日拿到凌普,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凌普交出了他和托合齐、朱天保、耿索图等十四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凌普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劫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九月十六回京,以观动静。其实九月十六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峰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齐说得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马齐说道:“过了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
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说道:“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辈希图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是有的。”方苞格格一笑,说道:“衡臣,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这样的人?”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实在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有伤皇上圣明之治奴才的意思,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聊存天家体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差的阿哥!”
“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康熙叹息一声趿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说道:“你起来,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被汗湿得贴在背上,援笔濡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前因胤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伊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着将胤拘执看守!”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物议。”
“好,删去。”康熙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样写——胤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躬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已详载起居注。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黜。”他说完,张廷玉也已停笔。康熙接过来看了看,说道:“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工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杜妄言!钦此!”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渖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齐说道:“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默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便抬头看康熙。
“不立了。”康熙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