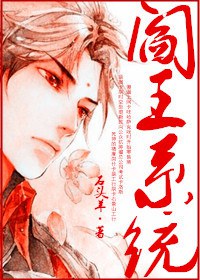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康雍乾-第50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廷玉在庄有恭搀扶下坐在安乐椅里,不胜疲惫地长长叹息一声,抚着前额上稀疏的白发,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苍老深沉:“这是先朝有例的。当年于成龙在清江擅自开仓赈济灾民,部议夺官、锁拿京师议罪。圣祖爷龙颜大怒,说于成龙一门贤良、爱养百姓、为君分忧,本当褒扬,反遭弹劾,连索额图都被扫得一点面子都没有。如今军机处里我与鄂尔泰的位置和当年索相是一样的。贸然循着这例保叙请功,皇上也许说这是沽名钓誉,拉帮结派;若照章程处分,皇上或许又搬出于成龙前例申斥,岂不是自讨没脸?所以先刊在邸报上,不言是非,放一放不妨。”庄有恭没想到这么件小事张廷玉竟深思熟虑如此周详,不禁由衷佩服。太老师为相四十余年,同朝为官的革的革、罢的罢、抄的抄、杀的杀,惟独他荣宠始终,岿然不动。思量着,却笑道:“悬的日子久了,皇上恐怕要问的。”
张廷玉听了一笑,却没有再说话,眯缝着眼望着天棚,许久,只粗重地透了一口气。此时天已黄昏,云色晦暗树影萧索,缕缕冷风透门而入,掀得墙上字画簌簌作响,更显得寂寞难耐。庄有恭本来求问自己前程,见太老师如此冷淡,便讪讪地干笑道:“我就要回河工上去了。太老师,有余暇给我写一幅字儿可成?”张廷玉点点头,养了这一会子神,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扶着椅背站起身来,说道:“我这会子就给你写。”一边挽袖濡墨,又道:“你的心思再明白不过,想进翰林院也很自然,你是状元,立马就能授侍讲学士,然后放几任学政,稳稳当当做一个太子少傅、太子太傅,门生多了,捧场的自然多,不但面儿上光鲜,升官也是极容易的。只要不出纰漏,十年内一个汉尚书是跑不掉的——可这都是一厢情愿的事,你懂么?”说着目视庄有恭。庄有恭正喜滋滋地抚着纸,听到这里不禁怔住,微笑道:“请太老师训诲!”张廷玉将笔放在墨海里,取过案头一把扇子,展开了,只见上面写着:
能慎独则器自重
一笔仿米楷书十分端正。张廷玉笑道:“你的想头并不过分,多少二甲进士都想走这条路,何况你是状元!但你太热衷了,中状元神志失常,连皇上都知道了。人主不怕臣下热衷功名,但人主聪敏过人,国家升平,求才不免就苛一点。国家重器亲戚父子间尚且不轻授受,何况你一个汉人进士!所以我放你外任,一则做事容易见功,二则做事不见功,离着皇上远,也不易见罪。待到真做出大事业,挣得大功名自然另有一番话说。后生,你说是不是呢?”
一席话说得庄有恭满面羞惭,红了脸,扶着纸的手也微微打抖。他方才心里一直不服,自己也在河工,也是满手老茧腕背上血痕累累,就坐在乾隆身边,偏偏却表彰了躲在侧影里的鄂善,此刻才明白皇上对自己另有一份苛求!半晌,才讷讷说道:“老相国这话,学生如醍醐灌顶。中榜那年,确实是和几个同年吃酒多了,所以失态了。但这个冤没处告诉,学生只有自己加勉,兢兢业业为朝廷做事,以求功名之心修养德性,不辜负太老师栽培苦心。”
“这就对了!”张廷玉那核桃皮一样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援笔濡墨,在宣纸上写了尺幅大小两个字:
戒得
又密密缀上几行小字,“乾隆六年十月壬午,庄思泉公嘱余作字。因思及昔年扈从圣祖幸避暑山庄事,得此二字。昔年亦是同季同时,是日雪大如掌,风啸如狂,圣祖垂戒诸子于戒得居。吾辈臣子,思及‘戒得’之义,可不慎乎?”
写罢,正觅图章时,却见小路子抱着一叠文书跟着一个太监进来。张廷玉问道:“小路子,怎么这早晚来了?你的腿怎么了,看着有点瘸?”小路子小心地把文书奏折放在长条卷案上,笑着回道:“院里苔藓贼滑的,摔了一跤,又防着湿了这些宝贝,腿就有点扭了筋相爷正写字儿呐,这可是我的好福气,我这就要放外任办差去,跟了您这几年,总见您给大员们写字儿,我官太小没敢张口。今儿既凑上来了,求相爷给点面子,另禀相爷,我如今改名字了,还是万岁爷亲自起的呢”说着便将乾隆去军机处“觐见”的情形说了。张廷玉是素来不轻易给人写字题句的,今日给庄有恭写条幅,已觉破例,正思量着婉拒,听是乾隆给肖路正名,便改了主意,笑道:“我的字并不好,官做得大了,人们就虚捧起来,其实自己心里明镜一样,因此只好藏拙,倒也不为拿大的。今儿你既有福气觐见主子给你定名字,我索性也给你凑个趣儿。”便又扯过一张小一点的纸,心里想:这是个地道的土佬儿,如今又放外任,应以君子小人之义儆戒,便写道:
行仁义者为君子,不行仁义者为小人,此统而言之也。君子中有百千等级,小人中亦有百千等级,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内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内君子者有之。大道无恒,唯修德而已矣。张廷玉谨识。
笔走龙蛇似的一篇草书,墨汁淋漓地递给了肖路,说道:“你初入宦途,又是捐的官,千言万语,也只是要你做个君子官,造福一方立功圣朝,也就不辜负我这一片苦心了。”
“谢相爷赐字,谢相爷教导。”肖路高兴得满面红光,双手接过那纸,小心吹干了,说道:“我原是德州客栈的小伙计,能有今日,全亏了杨大人和相爷的提携。杨大人是第一清官,相爷又是第一名臣。你们都是君子,我也不好意思当小人。我虽读书少,从小就听鼓儿词,樊哙是个杀猪的出身,黥布是个死囚,吕蒙正讨过饭,当时不也是小人?后来都成‘君子’了。我这一去做起来,准叫老相国满意”
二人听他说“不好意思”当小人,都不禁莞尔一笑。后来听他搬来的人物,才晓得这跑堂的在军机处耳濡目染大有长进。张廷玉送庄有恭出轩时,肖路见没人,便将那把扇子掖袖子藏起。又张罗着把送来的文书分门别类一札札叠起,眼见晚饭上来,肖路才告辞出来,一溜烟儿回到下处。
此刻,傅恒已到了岳钟麒府中。他的家眷都还在四川。北京的这一处旧宅,坐落在城隍庙南街原是奋威将军晋升一等公时雍正皇帝所赐,儿子岳浚任山东巡抚,来往京师不便,岳钟麒便将宅子让给了儿子。他来北京闭门思过等待部议听勘,自然还住了这里。岳钟麒从张廷玉处闷闷不乐回府,屏绝家人,独自足坐了半个时辰,只一口又一口喝着又苦又涩的酽茶,嘘着心里的寒气。傅恒奉旨前来抚慰,却没有宣旨的名分,因此不让门上通禀,只带了家下小奚奴一同进来,见岳钟麒半闭着眼坐在安乐椅上,双手扶膝,仿佛入定的模样,不禁笑道:“东美公,独个儿在家参禅啦?”
“是傅相!”岳钟麒猛地一颤,坐直了身子,见屋里已经暗下来,忙命:“快掌灯!——傅相,有旨意么?”颤巍巍起身便欲行礼,傅恒抢上两步按住了,呵呵笑道:“哪有那么多旨意!我去十四爷府瞧他的病,顺便来看看你。也亏了是你,这院里没有内眷,家丁长随几十号,前院到后院鸦雀无声,荒得像座古庙,我在这样地方住一天也就闷煞了。你还该将夫人和儿女们接到京里来的”岳钟麒笑了笑,让座上茶以后也坐了,喟然叹道:“六爷天璜贵胄,我这一辈子从兵营里打滚出来的,怎么相比呢?这院里的长随家人,其实都是我带出来的兵,中军营里跟着我厮杀过来的,有的老病,有的无家无业,左右横竖跟着我就是。”他揣摩着傅恒的来意,略一缓又道:“六爷不但能诗会画,上次带着岳浚去拜望,您一手琵琶弹得也叫人入神,我听着就好似又在千军万马的战阵里兵戈交锋呢。您,兵带得好,仗打得也精唉!我老了,皇上神圣武威,上次还言及西疆军事、南疆平乱,儿子们必能亲眼见到六爷杀伐立功,您是本朝一代名将名相,那是没说的了。”
傅恒跷足而坐,手持一把素纸湘妃竹扇,展开了合起一遍遍把玩着,灯烛下越发见得目如朗星面如冠玉,一条油光漆亮的大辫子随意搭在肩上,更显着气度宏深。他边听边微笑,从容地点着头,直到岳钟麒一大车奉迎话说完才笑道,“岳大将军不要拍我的马屁。你从龙西征的时候,这世上还没有我呢!打我一生下来,耳里听的我朝两大将军,一个年羹尧,一个便是你!这些日子你紧着往张衡臣那儿跑,为的是和通泊一战输得不服气,要到大小金川捞回来老面子,可是的么?”
“六爷太精明了。”岳钟麒笑道,“衡臣相公还在支吾我,您就一语道破了。既如此,索性就请六爷成全,也不要六爷为我这败军之将打保票,只说得万岁爷肯单独召见,我力陈金川军事势态,用我的不用由万岁做主,可成?”
傅恒双眉微微颦起,凝视着岳钟麒,半晌才道:“你以为皇上不肯用你,是因为你无能?”
“啊?”
“你以为皇上不晓得你急着立功赎罪?”
“知道”
“你不全知道。”傅恒望着悠悠跳动的烛光,徐徐说道:“你的和通泊之败,是先帝调度失宜,皇上对此心中雪亮,你明白么?”
第419章 老成宿将陈说边事 多情女子勇赴火刑()
傅恒见岳钟麒愕然不知所措,一笑起身,踱了几步,边踱边道:“准葛尔远离内地,有万里之遥,在紫禁城里指挥前线军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哪有个不败的?”
岳钟麒瞠目望着傅恒,这些话当然是“当今”的话,但傅恒居然侃侃而言,也太大胆的了。忽地心念一转,莫非他是奉旨而来?想着,已兴奋得连呼吸也急促起来。
“和通泊战败,你是全军而退。”傅恒瞟了一眼岳钟麒,又道,“北路军全军覆没。看模样你是全军主帅,理应负责。但仅仅北路军就有两位主将,锡保和马尔赛都是先帝简拔任命的,两个草包将军又互不统属!这样的阵势怎么能打得过噶尔丹策零三万骠营铁骑?所以皇上说,岳钟麒能在败兵如潮中镇定不乱,站稳脚跟,逼噶尔丹策零退回阿尔泰山之北,不失名将之风。”
乾隆这些话,是傅恒从山西回京第一天,君臣二人纵谈军事,酒酣耳热时说的,不但岳钟麒,连张廷玉、讷亲这些心腹臣子也是全然不知。岳钟麒听着这些话,不觉五内俱沸,心都紧紧缩了起来,万没想到,这些话竟比自己肺腑里掏出来的更中肯。自己不敢说,也不敢想的话都被这位年轻主子说了。涔涔的泪水在岳钟麒的眼眶中滚来滚去,终于还是夺眶而出
“主子还说,你在主帅位上调度失当,也难辞其咎。”傅恒又道:“一条敌方使用间谍惑我视听,你不能明查特磊之奸,犹疑不决,纵他进京混淆视听;一条不能严格维护满洲绿营军纪,致使北路军不遵军令一意孤行,深入不测;再一条你的那个车骑营,攻是那样的不紧不慢,退也是那么不急不速,阵势一乱,立刻就成了摆布不开的累赘,像条死蛇一样只有挨打的份儿。还有,战前为讨皇上欢喜,几次妄报祥瑞;凶危之道以喜庆妆饰,也很不合你勋臣名将身分”傅恒口说手比,滔滔不绝。岳钟麒战败的因由,被他分析得犹如亲见目睹。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他在剿匪时和李侍尧谈论西北战局得来的心得。在和乾隆奏对时,也曾谈过,这次,他想趁此机会搬出来当面验证。自然说得滴水不漏、得心应手。岳钟麒自下野以来每日烦闷不安恐惧获罪,从来没想到会有人这样公道地评介和通泊之战,更没想到竟是皇帝对自己如此体贴,此刻满心感激,恨不得立刻奔赴前线杀敌立功,报效皇上。哪有工夫分辨哪是乾隆的话,哪是傅恒的见解?他低着头,先是激动得抽泣,浑身颤抖,接着便号啕大哭道:“傅相,傅相你若得便替老奴才回回奏主子。岳钟麒一门世受国恩,自己也侍候了三代主子由于思虑不周、谋划不精,丧师辱国,是死有余辜的人罪何能辞?主子既知钟麒忠心不二,奴才就是身死万军之中,或受炮烙之刑,也都甘之如饴!但求主子再给奴才一次机会,由奴才去征讨大小金川。一年之内,若不能敉平,主子就不处分我,奴才亦必一死以谢君恩主德”说罢,泪水像开闸之渠一涌而出。
“东美公不要这样,”傅恒也颇为感慨,取出手帕拭拭眼角,颤声透了一口气,说道:“你想立功赎罪,想再次带兵出征,明眼人一望可知,何况皇上睿智圣明,早就洞鉴烛照了!但你知道,庆复如今在朝。上下瞻对在总兵宋宗璋手里,班滚生死不明,朝廷怎好无缘无故拜你为将再征瞻对?”
“班滚没有死!”岳钟麒喊道,“班滚若死,上下瞻对根本不用重兵驻守,留几百人看守粮库就够用了!班滚不死,逃亡金川,大小金川也要乱,趁他们将乱未乱之时,派我回四川,凭我和莎罗奔的交情、叫他交出班滚也不是难事!”傅恒听他说得如此笃定,不禁诧异,心里一动坐回椅上,关切地问道:“你和莎罗奔到底什么交情?我听人说过,今儿又两次听你说,倒真想知道其中的底细。”
岳钟麒拭干了泪,双手捧茶呷了一口,自失地一笑,说道:“这个说来话长。我其实更熟悉的是莎罗奔的大哥色勒奔”他两眼露出怅惘的神色,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康熙五十八年,准葛尔的策妄阿拉布坦派他的部将策零敦多卜进袭西藏。圣祖命正红旗都统法拉从打箭炉出兵,平定里塘、巴塘。我当时还只是个副将,担任前锋主将,带了七千兵士包围里塘,连战三天三夜,拿下了里塘,里塘第巴也死在乱军之中。巴塘和里塘原来暗地勾结迎策零入藏的,见我攻势猛烈、士卒用命,而且还有二百枝火枪,他吓破了胆。我占领里塘的第二天,巴塘守将第巴仁错就带着户籍到大营来献地投顺。接着乍丫、察木多、察哇也都献图向我投降
“本来仗打胜了是件喜事,可我不该胜得太快。一个前锋副将七天之内扫平巴塘、里塘,中军都没有用上,这就把主将法拉弄得有点尴尬。我在写报捷书的时候,只写了一句‘法军门坐镇打箭炉,指挥有方,将士奋勇’没有把他的‘功劳’写足,竟招惹得这位都统爷大不欢喜。因此,接到我的捷报,他也不向朝廷转奏,竟亲自带着两个中军,马不停蹄地星夜赶往巴塘。
“法拉脸色铁青,一见面就给来个下马威,申斥我:‘你打了胜仗,满得意的,是吧?啊哈!不要得意得不知东西南北了!’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我在前头给你打了胜仗,你没头没脑地给我这一下,算怎么一回事?强忍着气,说‘标下犯了什么错,惹怒了军门?请明示!’
“‘你犯了贪功冒进之罪!’法拉一脸狞笑,急躁地在帐中来回踱步,‘朝廷这次进藏剿匪,兵分两路,一路是我军,一路是定西将军噶尔弼,采用稳扎稳打,务求全歼入藏准葛尔部的战法,你这样打,策零敦多卜岂不吓得逃走了?你叫我怎么跟十四爷交待?’
“‘我进兵里塘之前,军门没有这个话!’
“‘我一到成都,在总督行辕召集会议,头一条讲的就是要在西藏关门打狗,生擒策零敦多卜。’
“你讲这话不足为据,军事会议布置方略,要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半点含糊其辞!我记得你这话,是在宴会上说的,当时刘正襄喝得脸通红,挥着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