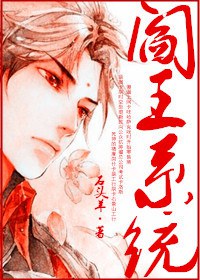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康雍乾-第5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派员赴阙谢罪请封;礼送大人离境,我亲自设酒相送。就是这些。”
讷亲听听,没有一条没有道理,也没有一条自己擅能做主的。格格一笑说道:“我要是不答应呢?”“那你就只能长留在这里,由我供应。”莎罗奔也是一笑,“不管哪路兵,敢妄入金川,或者想突围,大人和张军门只有玉碎在此。”他顿了顿,“至于以后,那要看天意。我只是个宣慰使,比不上朝廷一个州县官大。和大人同归于尽,也没什么不值得的。以今夜为限,大人不谈,明日我或许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讷亲思量着,知道这人言出必行,沉默一会儿说道:“可以谈。你明天派能做主的人进来说话。不过,我带这些兵要跟我进寨!”
“可以——放行!”
莎罗奔说完,一掉身子便去了。讷亲当即催马进寨,只见腾空了的大粮库里挤挤挨挨住的都是兵,粮库外边也临时搭了草棚、毡帐,无数破衣烂衫的兵士或蹲或站、没头没脸往嘴里扒饭,见他和兆惠、海兰察一行进来,只让条路,连个行礼的都没有。讷亲无心计较,因见吴雄鸿过来,忙问道:“大帅呢?”
“在粮库账房——游击以上弁佑还有二十一个,都在议事厅集合,等着讷相”
“我先见见广泗。”
“要不要稍歇息一下,吃过饭洗漱过再——”
“不要。”
讷亲头也不章,边走边说:“兆惠和海兰察休息一下,然后到议事厅。今晚要会议军政。”说着,和吴雄鸿一道去了帐房。
张广泗颓坐在东壁一张安乐椅上。零乱不堪的屋子只有两楹,破账本子、散了珠的算盘子儿,瓦砚、烂笔头都丢在地下,一片狼藉不堪。张广泗的身躯仿佛缩得很小,两只枯瘦的手支着膝,头深埋在臂间,一头蓬乱的苍发都在丝丝颤抖,完全是个垮掉的人。听着有人进来,他连动都没动。
“平湖公”,讷亲小心地走到他跟前轻声叫道。见他不应,讷亲叹息一声,说道:“大家心情一样,现在我不怨你,你也不要怨我。从军政两头,都要有个计较,还要向朝廷有个交待。”
张广泗抬起了头,脸色苍白得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仿佛不认识讷亲似的,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他,许久才道:“军事军事还有什么议的?你和我都是罪人,等着朝廷来锁拿就是了”讷亲看了吴雄鸿一眼,说道:“吴师爷,把门关上,你到外边守着,不要人打扰。”章坐了旁边又一个安乐椅,隔几侧身说道:“这一仗是失利了,北路军已经瘫痪,这我知道。但军事的事,我想了许久,并不是毫无指望。假如西南两路推进金川,我们能固守,莎罗奔仍旧难逃厄运。现在最难的是将令传不过去,金川并没有多少藏兵,他的老巢要被捣,立时战局就要翻转过来。”
“这我都想到了。”张广泗叹道:“莎罗奔恐怕也想到了,所以才放我到松岗。这真是个人物!你该思量,绕道成都,再到川西南传这个将令,就是没有阻难,也得一个月。这两路军知道我们被困,敢不敢来救?他们要是索饷,四川藩库供应不供应?别看这些武官,扯皮的本领大着呢!”讷亲点点头,说道:“四川藩台金辉是我的门生,我垮了,他也要失势,不能不勉力成全。一个月就一个月,让送粮来的民夫悄悄带出将令,由金辉发过去。总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嘛!”张广泗道:“莎罗奔难对付,更难的是无法向圣上交待。天威不测啊!”
讷亲缓缓站起身来,萤火虫一样的豆油灯幽幽地照着他颀长的身子,他深深地思索着,踱着方步,眼神暗得像深不见底的古井。良久,说道:“我军失陷刷经寺,可以请罪;北军占领下寨,可以报功。只要最后打赢,仍旧是无罪有功!这要看文章怎么写。”
“怎么写?”张广泗眼中放出光来。须臾又道:“海兰察和兆惠恐怕不肯替你我瞒着。”讷亲咬咬牙,硬着心肠说道:“刷经寺被困,海兰察救援不力,使莎罗奔佯攻得逞。兆惠是随中军行动的护军将领,不能预防敌人偷袭,致使我军伤亡惨重。都是可杀之�罪”�
在外边守风的吴雄鸿,听他二人计议怎样恩将仇报杀人灭口,浑身汗毛直炸,一阵一阵颤栗。他跟张广泗多年,张广泗刚愎跋扈是有的,但待下罚重赏也厚,坏心术的事不多见。这个讷亲冷峭寡言,但素来温文尔雅,待下礼遇丝毫不苟——怎想到事到急处,两个人都如此阴险狠毒?吴雄鸿恐惧得不能自持,屋里讷亲轻咳一声,竟吓得他一阵哆嗦。正恐惧间却听张广泗道:
“吴老夫子进来,商量一下写折子。”
天近五鼓时,一个黑影倏地闪进了兆惠、海兰察合住的帐篷。轻微的毡帘响动,立即惊动了二人。几乎同时,海兰察和兆惠都睁开了眼,不言声四目炯炯盯着来人动作。黑影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下,似乎在适应帐里的黑暗,接着便蹑手蹑脚向两个板床中间的茶几走去,摸索着端起杯子,窸窸窣窣向下塞了一件什么东西。海兰察见他要走,“唿”地一声坐起来,双手钳子般握住那人手臂,低喝一声:
“什么人?奶奶的,敢打我的主意!”
“别,别别动手!我、我、我是吴、吴雄鸿!”
“吴什么玩艺?老子不认得!”
“就就就是吴师爷!”
兆惠一下子晃亮了火折子,海兰察也丢开了手,都愣了神,看着几乎被海兰察唬瘫了的师爷。海兰察平日和他挺熟稔的,不禁笑道:“你这么鬼鬼祟祟的,还是个读书人!我还以为哪个饿兵进来摸索牛肉吃呢!”吴雄鸿的脸兀自煞白,用嘴努努茶几,兆惠走过去,从茶杯下抽出一张纸,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八个字:
恩将报以仇速作计
�兆惠便问:“左手写的?”
“什么玩艺?”
海兰察见兆惠变了颜色,接过他手中纸条,只看了一眼,心里也“轰”地一声,立刻弼弼急跳,遂急问道:“到底是怎么章事?”吴雄鸿不敢久待,只拣要紧的说了个约略。又要过纸条,在灯上燃着,看着它烧尽,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眼光看着呆若木鸡的兆惠和海兰察,说道:“我得赶紧走,你们好自为之——信不信由你们!”说着一闪便出了帐。
兆惠和海兰察木雕泥塑般站着。许久,才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转脸四目一对,都是火花一闪。二人都是天分极高的人,顷刻间便意识到自己命在须臾之间。
“怪不得夜里布置军务,讷亲一句不提你我,也不检讨刷经寺之败。”兆惠凄冷地一笑,“原来要拿我二人开刀!”
“他现在还不能动我们,”海兰察咬着嘴唇,紧张地思量着说道,“松岗的兵都是我们带出来的,出死力救他们,兵士们都知道,他怕哗变!”兆惠点点头,他已经恢复了镇静,闷声说道:“我们现在不能逃,那样他就更有口实,这里形势凶险,他不敢动我们。一待莎罗奔兵退,就要下手了——我们现在不是没差使吗?天亮和那个桑措会谈,我们两个要个差使,管刷经寺到松岗这段路和藏兵交接粮食的事。这样,我们行动手脚就放开了,在刷经寺寻逃路,比这里容易得多!”“光我们两个逃不行,我有十几个弟兄,都在大粮库当分库佐领。”海兰察手捏下巴,沉吟着道,“要让他们知道点影子,到时候策应一下。万一不成,也有人报告朝廷——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他们就这样报我们的救命之恩!”
兆惠佩服地看一眼永远带着稚气的海兰察,在与兵士交往这一条上,他确实自知不如。海兰察做到副将衔,什么马夫、伙头、哨伍长之类的狐朋狗友还有一大帮,和兵士们一块吃偷来的狗肉他秉性严重,不苟言笑,临急时才晓得鸡鸣狗盗之辈也大有用处。兆惠心里嗟叹着,章答海兰察道:“大利大害面前,没有情理仁义可言。他们的身家性命、功名利禄比我们的命要紧得多!”
讷亲和张广泗的“报捷”奏折递到北京,恰是五月端午。当时在军机处值差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一见是报捷的奏章,粗粗浏览一遍,便起身径到永巷口,却见养心殿廊下侍候的太监王耻抱着一堆东西出来,因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还是在乾清宫?”
“万岁爷和娘娘刚刚启动銮驾,先祭天坛,再到先农坛籍耕,午时才得章来呢!”
乾隆身边十三个大太监。贴身的五个,卜孝、卜义、卜礼、卜智和卜信在内殿侍候起居;外廊八个,王孝、王悌、王忠、王信、王礼、王义、王廉、王耻专管内外奔走,随行传呼一应事务。这位王耻排在最末,却因伶俐解人,言语乖巧,上下殷勤奉迎周到,倒最得乾隆任用。当下王耻答着刘统勋的话,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又道:“主子、主子娘娘惦记着当值的军机大臣,说过端阳节的,算不小的节气,既不能章家,叫赏的米粽、蒸糕、雄黄酒、芷术酒糟。主子娘娘听说是您刘延清大人当值,说您素来心脾不受用,又要添了苏合香酒,加赐一碟子宫点——怕着米粽您克化不了——还有槟榔包儿麝香袋,紫金活络丹,就赏了这大一包叫我送过来。我的爷!张老相国当了四十年宰相,也没有这个体面呢!”
刘统勋听乾隆不在大内,原本章身要走的,见说这话,忙又躬身站定,聆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热。待王耻说完,颤着手捋下马蹄袖跪地谢恩,说道:“刘统勋何德何能?受主子、主子娘娘如此厚恩!只合拼了这把老骨头报效君恩”起身又道:“烦请公公把赏赐物件送军机处。我去一趟傅相府,章头就进去给皇上请安奏事。”说罢,径自出景运门,从东华门出宫,向侍卫处借了一匹马,也不带从人,加鞭直奔鲜花深处胡同西街,来见军机大臣傅恒。
待到傅恒门首,踏石下马,刘统勋掏出怀表看时,刚到巳时正牌。他是常来走动的大臣,门政老王头早已迎出来,恭恭敬敬过来,哈腰打千儿行礼,吩咐“给爷的马遛遛,喂点料水”!对刘统勋道:“老奴才陪爷进去。我们老爷夜来还说起来着,延清老爷公子中了进士,得便儿要设个席面贺贺”刘统勋听他絮絮叨叨,随着往西花厅而来,是时万里晴爽,骄阳似火,但见满院修篁森森浓绿似染,夹道花篱斑驳陆离,洁净得纤尘不染的卵石甬道,被树影花阴遮得几乎不见阳光,石上苔藓茵茵如毯。偌大府邸绿瓦粉墙、亭榭阁房俱都隐在烟柳老木婆娑之中。刘统勋刚从骄阳蒸地里奔马而来,一身燥汗顿时化尽。一路进来,逶迤行间,但闻树阴间鸟声啾啾,草中虫鸣唧唧,月季、石榴,还有多少不知名的花香清芬弥漫,真是说不出的适意受用。刘统勋心中不禁慨叹:到底是侯门国戚、簪缨世勋之家,穷措大寒窗十年,就是做到极品之官,哪里讨这份富贵?正自胡思乱想,一个总角小童带着个人从月洞门迎了出来,一见面便笑道:
“延清公,总有一个月没见面了吧?你好稀客!”
刘统勋从遐想中章过神来,才见是傅恒,只见他穿着月白实地纱袍,套着件玫瑰紫宁绸巴图鲁背心,脚蹬黑市布千层底软鞋,剃得黢青的头后甩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三十六七的人了,仍旧双眸如星面似冠玉,英气中带着儒雅,令人一见忘俗。刘统勋见他行礼,忙着拱手还礼,笑道:“六爷好逍遥!部里事繁,我们又不同值,见面自然就少了六爷的养生之道得便也给我传授传授,您是越出落越年轻了,看去好像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翩翩佳公子呢!”
“我的养生之道你学不来!”傅恒一把扯了刘统勋联袂而入,吩咐老王头:“福康安带你儿子吃过早点就出去了,看章来没有,叫他到花园射靶子练布库,然后照例章书房读书!”这才又对刘统勋笑说:“你是个苦行僧把式,除了公务一无所好,又整日价批公文下火签,拿人捉贼坐堂断案,和汪洋大盗贼匪叛逆打交道,一肚皮的焦躁,怎么能学我呢?你来得正好,和亲王五爷、庄老亲王还有一帮子朋友,都趁着过节放假来我这讨酒吃呢!咱们索性一乐子!”
他这一说,刘统勋便止住了步。半晌才道:“我是有事来领教呢!讷相发来奏捷折子,军事我又不懂,怕皇上问话难章”傅恒笑道:“皇上这会子还在天坛,籍耕下来怕要午过了,章来总得进了膳才能见你吧?这不是军情有变的急报,你甭犯嘀咕,且松泛一时,一点事也误不了你的”说着便听西花厅里云拍铿然,一个男声捏着嗓子唱:
�脸霞宜笑,几度惜春宵。翠锦银泥,十二青楼拂袖招。杏花梢,暖破寒消
�一个嗲声嗲气的男腔假嗓子插问:“樱桃姐,你看陌上游郎,好不娇俊!”那位捏着嗓子的又唱:
�贪看宝鞭年少,眼色轻撩。
�假嗓门儿又道:“樱桃,怎的又说那年少?”便听接着又唱:
�琐香奁王燕金虫,淡翠眉峰只自描!
�刘统勋一脚跨进去,立时便怔住了:原来里边满屋子坐得挤挤挨挨,牙板鼓箫俱全,正唱着紫箫记。扮六娘的是恂郡王允�的长世子弘春,二十七贝子弘皓扮“小玉”,二人正当少年,倒也粉黛樱唇窈窕翩翩。再看青衣“樱桃”,居然便是弘皓的父亲庄亲王允禄本人!也是一身戏妆,翠珰步摇云鬓宝钗,干瘪的嘴唇上涂着胭脂,满是枯皱纹的瘦脸打了厚厚的官粉,也在那里“眉蹙春山、眼横秋波”,当儿子的“丫头”。方才捏着嗓子唱的,就是“她”了。见他二人进来,众人一笑停戏。旁观的钱度、阿桂、纪昀、高恒都是部院大臣或外任大员,纷纷起身和刘统勋见礼。允禄一边摘“耳环”,一边笑问:“延清公,又不演铡美案,你这黑老包来作么事?——你听见我唱得怎么样?”
“端的是歌有裂石之音!”刘统勋道,“闻声不如见面,见了面真是颜如天魔临凡!”说罢紧盯着允禄,半晌“扑哧”一笑,又道:“王爷这一扮,还真像软玉温香呢!不过您别眨眼,一眨眼脸上的粉就掉渣儿了。”
这一说立时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排场的总管是和亲王弘昼,掌乐的几位是弘瞻、弘谦、弘�、弘闰,都是近枝龙子凤孙,弃了鼓板笙箫,嘻天哈地鼓掌大笑。一众清客相公也都前仰后合,嬉笑着凑趣儿:“王爷扮起来就是菩萨,怎么说是‘天魔’?”立即有人接话:“没听金刚经里说,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阿修罗就是‘天魔’,是绝美仙葩!”一个清客笑得打跌,说道:“我家老爷子爱扮牡丹亭里的小春香。那天扮好了问我‘像不像’,我说‘神似形不是,细看叫人毛骨悚然!’气得老爷子啪地赏我一记耳光”
“来来,”允禄笑得满脸开花,“粉渣”儿脱落得一道一道儿,亲手端一盘鲜藕递给刘统勋一块,“延清,这是我南边庄子里新出的,六百里加紧给我送了二十斤,又清又脆又甜,几乎没有渣儿,我贡给皇上十斤,这点咱们分用。你尝尝!那些粽子、包子、玻璃肉都是荤的,苦行僧一用就犯戒,葡萄呀西瓜呀这些你倒合用的。”“谢庄王爷!”刘统勋接过轻咬一口,笑道:“果然是好!我其实也不忌讳吃肉,只是有心疾,一吃就头晕心跳。太医吩咐素食,不许抽烟,所以连烟也戒了。”坐在窗前的一个黑大个子笑道:“这正好!我不吃素的,人都叫我纪昀‘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