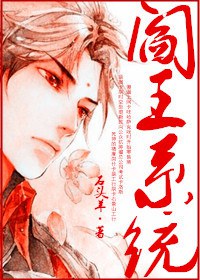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康雍乾-第6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州人才知道,棉袍子还是要的。
亭午时分,绛红的冬云愈压愈重,阴沉广袤的穹隆上烟霾滚动,像刚刚冷却的烙铁般灰暗中隐带着殷红。终于一片,又一片,两三片,柳絮棉绒一样的雪花时紧时慢,试探着渐渐密集起来,不一刻功夫便是乱羽纷纷万花狂翔,把个裹红自矜妖娆玲珑的维扬陷进蝴蝶阵中。
雪下得正紧间,一头毛驴驮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书生逶迤过了关帝庙西迎恩桥,径至扬州府衙照壁前下骑。他抹了一把头脸上的雪水,握着驴缰绳,对搓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望了望黑洞洞的府衙大门,寻望良久才见下马石旁挨墙立着几根拴马木桩,因牵着驴过去,解开蓑衣带子脱掉了,正要拴驴。衙门洞里一个衙役正和同伴说笑闲磕牙儿,一眼见了,却不肯冒雪出来,闪身出来站在滴水檐下,远远地斥呼道:
“喂!你瞎了不是——说你呢!你张望个哩?——那是大人们歇轿拴马的地方儿!”
那青年一愣,望着门洞说道:“请问我的驴该拴哪里?”那衙役还要呵斥,旁边一个衙役笑骂道:“何富贵,你他娘的把我们一群都骂了进去——他在看我们,你说‘张望个’。”何富贵本来板着面孔,泄了气扑哧一笑,对那青年喊道:“从东旁门进去。牵到马厩那边,自然有人照料。”那青年嗫嚅了一下,大声说道:“我是——”
“知道得知道得!”何富贵不耐烦地一口打断了,摆手指着衙东说道:“你主子不是会议迎驾的事的么——东角门进去——老高接着说,他两个正日得高兴,她男人回来了,这婆娘怎么料理?”
那青年听他这般话说,顿时如堕五里雾中,府衙会议他是知道的,但“你主子”三个字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叫窦光鼐,别看文弱纤秀貌若女子,其实不是等闲之辈,自幼在塾读书乡里便有神童之曰。十二岁进学为秀才,十五岁赴南京贡院乡试,赫然高中第三名举人;次年公车进京会试,春风得意之人,一发的精神焕发,制艺?、策论、诗俱都作得花团锦簇一般;试官暗中揣摩,居然取中第三名,待下来看履历,才知窦光鼐不过是个刚过志学的少年。主考官讷亲见他如此青云直上,皱眉说道:“太年轻了,得挫磨一下性子。取得高了太惊动物听,也怕折了他的福——你们看他的字,带着点飞扬跋扈味道,锋芒太露了嘛”生生向后推了十名,险些一个一甲进士被他夺在手中。但凡淹博才智杰出之士多犯一宗毛病,易于傲物不群。他虽被黜在二甲,毕竟仍在前茅之中,按例分发,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本来这是枢密清要,进士们巴望难得的差使,敬老师敦同僚安生混差使,出几个学差红了,稳稳当当授掌院、内阁学士、大学士,自然地就宣麻拜相了,至不济也混个外任学政,也是官场人人心向往之的要缺。却因礼部侍郎王文韶到翰林院讲学,痛诋宋儒道学,他竟当场挺身而起与这位名满天下的前朝老状元哓哓折辩。两个饱学之士一老一少一台上一台下反复折难反诘,清秘堂中人人听得心旌动摇。幸而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纪昀正好要从翰林院抽调文词之臣编纂四库全书,就腿搓绳儿的事,掌院学士便将这个二杆子翰林“优叙”了出去。
窦光鼐站在琼花淆乱的衙前发了一会子呆,毕竟心中懵懂;自己要来衙拜望扬州府同知鱼登水,说征集图书的事,昨天驿站已经知会了知府衙门,鱼登水怎敢如此怠慢?再说“你主子”三字愈思愈觉殊不可解,想再上前问询,却听那个姓高的衙役说得起劲:“那女的半点也不慌张,蹬裤子穿齐整了,见野男人唬得没做手脚处,脸色煞白满头冷汗发呆,对他耳边嚼了几句悄悄话,到门前提了只柳条笆头,‘哗’地打开门。她丈夫还紧着问:‘大白天怎么把门拴得死死的不开?’话没说完,‘唿’地一声,头上已被女人套了个笆斗。女人两只手擂鼓价猛捶笆斗,使着眼色教野汉子逃,一边破口啐骂,‘王家唱大戏混元盒子,杀千刀的,只顾你自己去看!也不带我——我教你看!我教你看!!我教你看!!!老娘懒得给你开门’她男人头震得发懵,一时间瞎子聋子似的,不住口价解说着‘没有看戏’,野汉子早一溜烟儿走了”
衙役们顿时一阵哄堂大笑,纷纷笑骂:“日娘鸟撮的,家里有这么个婆娘,绿帽子要戴到棺材里去了!”“她男人混元盒子没看上,野汉子在家倒看上了”“贼才贼智,真真不可思量!”“当场脱逃,缉拿无案”嘻嘻,哈哈,格格,嘿嘿一片嘈乱的笑声中,窦光鼐摇摇头,牵着驴去了。
沿着衙门南墙向东走了约一箭之地,果见尽东头有一道门。却也不是寻常独人出入的“角门”,颇似骡马干店的车马门,约可丈许宽窄,无阶无槛也无门洞,满地稀得受潮了的白糖似的雪水,地上车痕蹄迹脚印并骡马粪狼藉一片。窦光鼐心知这就是了,牵着驴进来,抹了一把被雪迷了的眼,果见这座大院落靠北沿东都是厩棚,马嘶骡踢腾的甚是嘈杂。进门向西却是一排拐角房,里边坐满了人,也都在喝茶说笑话。茶炉弥漫的白气缓缓从窗口檐下吞吐漶散。因见这些闲汉一色都是厮仆长随打扮,恍然之间窦光鼐已经明白,这都是本地织行染坊盐商阔主们的家人,自己这身装裹,骑这头蚂蚁似的黑叫驴,连个从人也没带,一准是那个杀才把自己当成哪一家的仆从了!窦光鼐不禁莞尔一笑,牵着他的“黑蚂蚁”绕过一片放得横七竖八的轿车、暖轿、驮轿,在一群高骡子大马中拴好了,出来,便见一个衙役从内衙提着大茶壶出来,因问道:“鱼二府在哪个堂?”
“孕——妇?”那衙役冷丁地被他一问,怔了一下,吞地一笑说道,“孕妇自然在接生堂——你这人真有意思!”
“集省堂?集省堂在哪里?”
“接生堂有好几处呢,你问的哪一处?黄家的?刘家的?还是卢家的?”
窦光鼐怔了半晌,才明白和这位满口吴语的家伙闹了个满拧,一笑即敛,咬着京派官话一字一顿说道:“我要见你们鱼登水大人——知府裴兴仁已经革职拿问,鱼登水现在署理扬州知府,他还是同知,所以叫他鱼二府——听明白了么?”
“你是要见我们太尊大人嘛,早说不就明白了。”那衙役惊讶地闪了他一眼,这才正目打量,只见这年轻人穿着灰府绸挂面儿棉袍,蓑衣上满是雪,里边露出套扣天青缎巴图鲁背心,脚下乌拉草木底履套着黑冲泥千层底鞋,穿着蓑衣却没有戴笠,一顶黑缎六合一统瓜皮帽上还嵌着一块白玉镶片。这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也不贱,说不清是个什么来头,因道,“鱼大人出衙拜客去了。原说今儿会议本府士绅,商计乾隆爷巡幸扬州迎驾的事儿,人早到齐了,大人还没回来。二堂那边——”他用手指指衙内院向南拐弯处,“人都在候着他老人家。您先生敢问官讳、台甫?要到签押房得等胡师爷午饭后才得开门,不然先屈驾到二堂等着也好,鱼老爷不会在外时辰长了。”这次他也咬一口蹩脚京腔说话,虽是不伦不类倒也明白。窦光鼐听了只点点头,一边走,解着蓑衣带子径到府衙二堂后,蓑衣木履脱在廊下,便听里边人声嗡嗡嘤嘤,啜茶的、窃窃私议的、咳嗽的、打呵欠的,叽叽格格似乎在说笑的什么样的都有。
猛听得有人说:“窦光鼐这么作践别人,踩人肩头向上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窦光鼐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会有人在背后骂自己,而且咬牙切齿恨得想将自己投畀豺虎,心里轰地一阵耳鸣,立刻涨红了脸。站在门口觑着眼往里瞧时,外面雪光映着,屋里格外暗,烟腾雾绕朦朦胧胧老少富商足有四十多个,杂坐在六七张八仙桌旁吃茶抽烟嗑瓜子儿品果点说闲话,根本看不出方才是谁发话,正发愣间,二堂西南角几个人已经纷纷附和。
“邢二爷说的是。”一个肥得水桶似的绅士,用手绢擦着油光光的鼻子,打着哈欠呜噜不清地说道:“裴太尊挂靴离任,我去看他,他说自己只想造福一方百姓,不防头就得罪了言利之臣。这姓窦的就是个言利之臣,货真价实的个小人!”
“是小人之尤!”
挨着邢二爷坐着的一个干瘦中年人捋着山羊胡子,斩钉截铁说道:“他按着治河涸田?不许卖,裴太尊卖了他眼红——裴太尊难道卖田填了自己腰包?”说着便吭吭地咳。旁边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个子却似乎不关痛痒,笑道:“无非窦某人弹劾裴太尊,断了诸公一条生财之路,你们才恨他。说句公道话,朝廷的涸田卖得也太贱了。老邢,把你清河庄子上的地二十两银子一亩盘给我,不,三十两也成——你卖不卖?”窦光鼐这才看见那个叫邢二爷的,却是个方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鬓边一块朱砂痣一抽一动。“那是我爷爷手里从靳河帅手里买的——你老万开什么玩笑——我是说,这些涸田荒着也是荒着,朝廷自己不种,卖给老百姓种不也是善政?他窦光鼐凭什么拦着,还弹掉了裴太尊,连靳镇台也跟着吃挂落!”
旁边几个土财主模样的立刻响应:
“天道好还,窦光鼐也不得好死!”
“拿别人血染自己的红顶子,他还算是个才子?”
“鸡巴才子——就是才子,也是个妨主精儿——我听说他娘,他太太都妨死了。这样的人,能在乾隆爷跟前呆长?”
“大凡才子,多是短命的。”邢二爷道:“孔子跟前的颜渊,才子吧?三十三岁呜呼哀哉。汉朝的贾谊,才子,三十三岁哽儿屁朝天”
窦光鼐弹劾裴兴仁和靳文魁,原为他们攀结盐政使高恒,连小妾都献出去供“国舅”淫乐,没想到竟招惹了这群地主,疯狗似的恨不得咬死自己。听他们夹枪带棒辱及家门,更气得手颤心摇,身子一挺进了二堂,正要说话,一个白净脸中年人早已迎上来让座,扯着他袖子递着眼色小声说道:“兰卿老师,我看你多时了。不怕真小人但畏伪君子。和他们怄气,没的小了老师的身份。来坐,听他们胡嘈,一会子难堪死他们!”窦光鼐一看,却是在纪昀府里几次见过面的熟人,人都叫马二侉子,是专为内务府采办贡品的皇商,为人最是散漫不羁的,本名自己却不知道。窦光鼐恶狠狠盯了西南角一眼,粗重地透了一口气,挨着马二侉子在公座旁第一桌坐下,阴郁地说道:“民间口碑,指摘官员操节,原是寻常事。但家母健在高堂,他竟敢如此诅咒!”
“要整治他们也不在这一时。”马二侉子一条辫子散懒地盘脖子一圈搭在胸前,端茶唏溜一口,嬉笑道,“这几个都是扬州富粉行的粮绅,地地道道的土佬儿。您当场和他们拌嘴,板平了身份不是?胜之不武么!”说着,便见那桌上那位獐头鼠目的先生伸着脖子挤眉弄眼问道:“涂维孝,你说得活灵活现,见过窦大人?”“见过,”那个姓涂的舐舐嘴唇,扮个鬼脸儿笑道,“那样子呐,和尊范一模一样,伶伶仃仃的,像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一句话说得西南角满桌哗笑。窦光鼐满腹气恼,也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其余各桌士绅,经营茶盐瓷器漆器染织行当不一,彼此似乎也不甚相熟,却仍只顾各说各话不大理会。
闲话神聊间,外间的雪下得越发大了。
风似乎停了,一团团一片片,或如乱羽,或似绒球,不飘不荡,在黯淡的门洞檐下格外显眼,竟是个直落硬降的味道。满地稀浆样的雪搅水已被骤雪盖得严严实实,房瓦上的雪已积得三寸有余,瓦溜子的滴水也渐渐停了。不知谁说了句:“雅静,鱼太尊回来了!”满屋嘈杂立刻停了下来。
一片鸦没雀静中,窦光鼐留神向外看,果然见一乘四人大轿,蒙着的纳象眼毡幕上覆了厚厚的一层雪,抬杠的轿夫人人雪水淋漓,踹着步子踩得雪地咯咕咯咕响,从大堂东道绕到天井院里,“噢——”地一声号子,大轿稳稳落了下来。那个提茶的衙役一溜小跑出去,挑起毡帘,赔笑说道:“老爷回来了?客人们早就到齐了,恭候着您呐——爷揩一把脸再出来,外头贼冷的,着凉感冒了不是顽的”接着便见一个官员哈腰出来,却是一位清癯老者,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瘦骨嶙峋的,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折了的老竹竿,下轿来双手对搓着一头走一头问道:“兰卿大人来了没有?”
“没呢。”那衙役小心翼翼搀着他上阶,忙不迭用手拂去落在白鹇补服上的雪,拉拉袍摆抖抖褂襟,笑得鼻子眼挤在一处,说道,“老爷一升轿,我就吩咐了门上,今儿不开衙理事,有大人来访惊醒着些儿快些报进来。这大的雪,小虹桥那边梅花开得好,兰卿大人敢是赏梅去了吧”
此时众士绅早已起身迎出堂口,打躬的、作揖的、拜稽的、请安问好一片声响:“太守”、“太尊”、“黄堂”、“五马”胡喊乱叫一气。那鱼登水却甚是眼明,隔着众人一眼便瞧见窦光鼐缓缓起身,忙用手分开人群,几步抢进去,双手拉着窦光鼐的手,晃着胳臂笑道:“老兄倒先来一步!你说‘登门来拜’,我怎么敢当呢?今儿一早起,赶紧就过驿站拜望,谁知路过镇台衙门,靳文魁正在搬家,这大的雪,箱笼行李都撂在泥水里,一家子妻女哭哭啼啼——我们共事相与一场,他开缺问罪,下头人这么着作践,不好袖手旁观的,就在那里料理一下,谁知就去迟了,更不想你独个儿骑驴到我这边来,真好雅兴”又说又笑嘘寒问暖,家常殷勤十分。马二侉子在旁笑道:“靳家的雪天扫地出门,也少不了叫撞天屈,骂窦光鼐的吧?”窦光鼐也道:“看来这个窦光鼐真是十恶不赦之徒。这边几位先生也骂得兴起,窦某人先雪水浸身,然后狗血淋头”说着,便笑。但在场的人除了鱼登水和马二侉子,谁也不知“兰卿”是窦光鼐的字,他们的话,立即引起邢二爷几个人一片声“共鸣”:
“大雪天封门闭户,硬赶人家搬家?镇台衙门的人真他娘势利——这都是窦光鼐做的好事!”
“靳大人那是多好的人啊,本事也大,开得两石弓呢——落架凤凰不如鸡!”
“还是我们鱼太尊,前头裴太尊家眷动都没动!”
“平常生意人家,还讲个‘信’字呢!前头裴太尊批给我们的涸田田契,加着府台印信,鱼太尊得给我们做主!”
“这话对,没的叫窦光鼐这枭獍忒得意了!”
众人七嘴八舌中,鱼登水身在窦光鼐面前,尴尬得脸色灰青,脖子上的筋绷起老高,沉着脸断喝一声道:“住口!窦兰卿大人名臣风骨,弹章一上,朝野震悚,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侮辱毁骂?”窦光鼐进前一步,双手一拱笑道:“学生就是窦光鼐,窦光鼐即是窦兰卿,着实得罪了!”
所有的人立时僵住,木雕泥塑般呆住,沉寂得连天井落雪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好一阵子,邢二爷几个人回过神来,知道今天触了大霉头。先是那胖子撑不住,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叭”地抡臂打自己一个耳光,说道:“小人昨晚醉了黄汤跑了这里来胡说八道——临走老婆子还说,多喝茶少闲话——我竟是个猪托生的,没耳性!”他“叭”地又是一掌。几个犯口舌的米蛀虫土财东也都纷纷效颦,骂自己“死王八”、“不要脸”、“发昏”、“吃屎长大的”,花样百出。其余盐商、瓷器、漆器、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