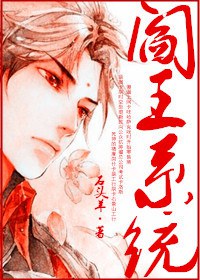���ºӵ���ϵ�С���ӺǬ-��69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ó�������Ҫ���꣬�����˲�����ġ��ϴ��ڸ��ߵ�������ү��ð�˷磬����Ȯ�ͽн�ȥһ�ٳ��������ү���Լ������˲���û�¶�����˵�ţ�ͻȻ��ͷ���˽ᣬ�������ż���������Ӽ���è�Ƶ�����ή����ȥ������Ц����������ɱ����ʲô����������ģ�����ġ�����һ��ͷ�Լ�Ҳ��ˣ�ԭ����Ǭ¡��֪ʲôʱ��������ʱ��ͳѫҲ�����ˣ�ת�����������ͼ������������밲��
��������Ǭ¡��ȥ���ã��������ͷ�ϴ�һ�����ᶥ�ڶй�Ƥñ�������������ͼ³�������Ž�ɫ�������ӣ������ü����µı�����˿���Ҵ����Ժ�����һ���������ӣ������ƵĴ������䣬һ��������ֽ���ӣ�һ����̧һ�½������Ͷ��ˣ�Ц��������Ҳ����������д�����ᣬ�������ߣ�������˵�����������ӡ���̫����������ˣ���ô��ôû��ɫ�������������ʵ�ڲ�����Ǹ�������Գ������ߡ�����ͳѫ�����ۿ��˿�Ǭ¡��˵���������������۾��е㷢���أ����黹��û˯�õĹ�����Щ�����ܻ��ŵ�ģ��������������Żر��������������;�У������ֲ��ܷ��ͣ����ϱ�ƴ���ӹǶ�����Ǭ¡��������������Ŭ������վ�ɰ������ţ��ǻ��о���¾��������ɢɢ�����ɣ�������������������ɽ������ȥ�������ֻع���ȥ�ˡ���������������ĵ��Ҫ��������һ�裬����Ҳ�������Ǵ��ţ�˵���¾ͻأ���Σ�����ͳѫ�������ѵ��������ɢһ�£���Ȼ��ϲ�ġ�ֻһ�������ϲ��ܳ�����Ҫ��ȥ���һ���ȥ���ùط�����Ǭ¡Ц��������ң����ͳѫ��˵�����������������ѽ�ã�������ģ�����ģ������Ǵ�ͷ���ߣ���ͳѫ�ͼ����������棬���˳ܲ����ź������ļ���̫�ಢ���ض�������������������ңң�˸�������������������������ӱ�ӵ�ʱ����ɫ�������հ�����ȫ�����ˡ�
���������ߴ����»�������֮�����ȫ����������һ���ڷ���ų�ʪ�����⣬�������˻��������������˵��۰������ϸߡ�Ũ����һ������ѹ�õ͵͵ģ����·�����ػ��༷ѹ�š�������������ʮ������ҫ�ľ��������һ���ӱ�����̣�Ũ���������ĵ���ī���ٲ��㸲����ɽ�ͣ������������ü������ʯ���ϲ�����̦��������������ʱ��ʱ�֣���ҡҷ������Ũ�����Ե÷����������ء�һ·�ߣ�������Ǭ¡�渳������簢������衣��֪Ǭ¡���鲻�죬����˵��������������������������ƺ����˸�����ϸ���ģ��������ţ������ɱ���࣬�����Į���ɹ�ƽ�۹������������������ijﻮ��Ҳ�����밸����β�С�������ͳѫ�����Ź�̥��������������Ǭ¡����ŭ����������������Ǭ¡���ú����ģ��䵭���ų�������ͷ��βһ��Ҳû֨��ֻż��ת������������һ�ۣ���������·������������˳��ţ��������ģ���ϸ�����м���������֤��˵������һ�����µ���ʥ���ж����ţ�������ͳѫ���飬����ʥ�ϼ�֪�ţ�����֮���ʹ���û�ˡ��ɴ˾�һ�����������Ƹ���֮��������ʡ��Ҳ���Ҷ��Խ��о��ޡ��Ըߺ�Ǯ�Ȱ��ʹ˰�����һ�����٣����������Բ����ԡ��������³�ƽʢ����¡֮ʱ��˹�ģ�������Σ���������ǧ��һ�۾����۹⣬�������������߷緶����
�������������ǵ�����������ߣ������ء����к���������Ⱦָ̰�ߵĹ�Ա��һǧ�����ϵ�Ҫ�������ý��������������鴦�����ؾ��ߺ�һ���������ã�һǧ�����µ�������֡���Ǭ¡վס�˽š�����ɽ���һ���սǴ���ƾ������������ӽ�����������ˮ���������续������������������ǡ��̹�����Ƶ�һ������ֱ���쵽�ʵ��쾡ͷ������������Զ�������ţ���ɫ�����˯�ѵĺ�������ƽ��������������ˣ�������ֻ���㾡������������ô�����ǹ���Ѭ��֮ʱ���ս��˿���һЩ����ٵ��Ƕ��ˣ�������ҵҲ���ŵ��㣬�Կ�Ϊ�����ˣ����Ͽ������˲��ܿ��������׳��¡�һζ��ͬ�������������ݣ����ݵñ�ض���̰�٣����ݵ����Ի߳ɣ�����һ�����´��ҡ����Ի���Ӧȡ��ӹ����ͷƫ�˷�һ�£��ǹ������ܽ����ģ���Ȩ�ҹ���һ�£����Ǿ�����Σ���
���������������˵�ͷ̾������������һ������һ�ף����ϵǼ��������污����ҵ��Ϣ�⼱��ƶ�����²Ƹ���֮���������屶��ֹ����ҵ���̳�ƽ���ξ�������һЩ����֮϶��Ҳ����Ȼ֮��������ʱʱ���裬�����������������������û��������Դ�ġ��¾����������ն�������̰�٣������Ǻ�ͬ�����������ո���Ҳ��������Ҳ���˼���һ�������ա��������������ӹ��ݣ�����������壬����������Ǯ���۾�Ű��ɥ�IJ������ص���Σ�һ��Ҫ�����ӵġ�����ͳѫ��ü�����������ͼ�������ҹ̸��ȷ����������������Կ�Ϊ��������������ƽ��������է�ޱ�������������һ����ȴ����ͷʩŰ����ֻҪ���ٷ��ƣ�ʲô���캦������㣷����¶�����������Ű�����ﳪ�ġ���������Թ���ߡ�����Թ����֮ʱ�������������֣��ɺޣ���
��������������Ű���裿��Ǭ¡�ʵ�������˭���ģ���
������������Ű��ҥ��ǰ������̫��̰Ű�����ذ����˵�ҥ�裬û�г���ע����������æ�����������ͼ�飬�ھ��ݸ�־������ģ�����ż��˵�𣬲ű�����ͳѫ��������һ��һ���е���
��������ʳ»�����Ž��ۣ���֪����ֺ���
����������������ǧ��Ѫ��ϸ�з������ոࡣ
����������������ԩ��Σ���������Թ���ߣ�
��������Ⱥ���ڲ�������������͢�ö��ܣ�
�����������յ�ͷ���
��������һ�������ǵ���ν�Ǭ¡������������û���һ�������������������������Եľ��·���һ���������˵������Ҫ�����ˣ����ǻع���ȥ�������ż������꣬��һ·С�ܸ���������һ���ɫ��멸�Ǭ¡���ϣ�һ��Ц������С��������ˣ������һ�����������ӵ��£�һʱ�ܲ��š���߳�ȥ��ڵķ綾���أ����ӼӺ�Щ������ð�˲�����ġ�Ǭ¡��������ͣ���ˣ��Ծ�һ�Բ�������ɽ��������¡���ͳѫ�ͼ�������һ��Ŀ�⣬æ���Ÿ�����ȥ���µ�һ�����أ�һ��ʯ����ȥ�������й�����Ժ�ڣ������Ѿ���������ó��������ˡ�
���������й�������ɽ���ϴ�����ɽɫ�����İ���Ժ�м���ϱ��ֵ���ͩ���ڱ�����⣬�Ե��������е���ɭ�����ź������е����������Ĺ��ޣ��ڵ����ſڴ�Ϣ�����Ǽ�����������ͦ��վ�����º�Ժ�У��������ŵ��ͥԺ������˿�˼��̻�����Ǭ¡�ƺ���Ը�����У��������Ͷ����ڳ���������������߮�����òŵ����������沢̫���������ļ���ƶ�ļ�ƶ���Ų���ʵɽ�¸�ԥ³��ʡ���ػ�ɽ���ɵ��ض����������ѣ����������꿼����һ�����������������壬��������������ģ�������Ҫ���á������Ǵ���������Ѱ��ϸ������Ҫ�������ġ�����������ͳѫ��һ������֪�⻰��Ű��ҥ������ȷʵ���ǡ�Ѱ��ϸ���Ƕ�����Դ�Ĵ�Ƹ�����æ������Ӧ�����ǣ���
����������Բ������Ҫ�ޡ���Ǭ¡��������ͩ��ɳɳ��������˵������������������������ʵ�˶�֮�������ٲ���ʩ�ã��ɹ������˼ල�����Ǵ���֧�����ӣ����������ܲ��Ų��ʡ���
�����������ǣ���
��������Ǭ¡��������������ͩ����֦�⣬�·��е���ʧ���ӹ�һ˿Ц�ݣ��ֵ�������ּ��¬�̣��������������ƺӿ��迣�ˣ�������ҲҪ�迣���ٳ��ĺ�̲���ƽ�������˾ɹ�Ρ��ƺ��ٺ���øߺ�İ��ӽ������顣���С��������Ѳ��û�������ع���ӭ�ͳ���Ҳ�в��ٹ��ڣ���ּ���£��ٴ���������Ǯ������
����������ͨ�ƺӡ����ӽ��뺣�ڣ����γ�������������ͳѫ��û��˵������������Ǯ������������������ȥ��ǧ�������룬�����˱㲻�ⷸ�����������ԥ�Ÿ�˵�˾䡰������̫�ࡱ���㱻Ǭ¡����ˣ������к�����̰��������������������ġ�ֻ��Ҫί����̫����öȣ��������ڶ����Խڼ�Щ���ġ����������ˡ�����������أ���������ĵ�������������������������ĴӶ���������������һ���Լ�����������վ�ڵ�ܯ���������Ⱥ�֪�ʺ��DZ����£�����̾�˿�����ȴ���ֽй���������������ĵ���أ��������ˣ����������������ͳѫ�ͼ��������ֵ�������������һ����ϸ��һ�£��������ɣ����ǰ��⼸�����ã�����û����ʧ��©�������ּ�����ٿ�����
��������˵���䲷���Ѷ���С����̫��̧��������������ʱ�����軨��Լ�����߸߰�����������ɫ�ģ�һ�ꡰκ�ϡ�һ�ꡰҦ�ơ�������������ŭ��ʢ���ģ��������������������֦�Ƕ����������ī����֦Ҷ��մӵ�������Ų������ӨӨ��ΡΡ�����¶���̴�Լ��ϲ������Ц������Ψ��ĵ�����ɫ������ʱ�ڶ����ա��������Է����ܺ���Ӱ������Ӻ�������С�����ͳѫЦ������ǰ�ռ�����ʫ����������ĵ�����������λ�ϲ�÷�ħ�ˣ���������æ����ߵл���͡�Ǭ¡Ц�ʣ�������᰻�������ĵ����ʫ����������������
������������Ҳ��������Ǩ����ĵ���������ѣ�����ʵָ�������������ϵ����ˡ�������Ц��������ʱ˵���������͵ļκ̣�һ�����룬�Ͼ�ûһ���Ѷ�����˵��ĵ����������Ԫ��һ��ʫ�����滨��С�ܳ�ʵ��ɣҶ��ֽ���˿��Ω��ĵ���綷����һ���ֿ�֦������˵��ʫ����Ȼ���Ƿ��ϣ��վ���ɷ�羰������ֱӲ��˵������һЦ���ѡ���
��������Ǭ¡��ͷ˵�������㲻�ñ�⣬�ⲻ��ӽĵ�����ǽ����������ʫ��ѧ���������£���½����ӽ��˵�����Ǵ�����ΰ�ˣ��ܿ�������˳��������ϧ��������δ����ɽ�����ס��������Ǿ�����û�ˣ�δ���ѧ��̫�أ�һ����˼������֪��д����ʫ�ͺ�����Ȥ������ȡ��������������ûʱ����Ūʫ���ˡ����˳ܣ���ͳѫ�ͼ�����ƫ����ţ��������̺��ͻ���λ�������ٽ�������˵�ţ������������ʰ�����ף�����ܯ�������һ���½ף�һ���ʵ����������ģ�����Ӷ���˭�ڻʺ������
���������������ӻ���������������������Ǭ¡�������ţ��ص����������Ϸ�ү���������ž��������DZ߽��ġ�����������Ҳ�����˵ģ�������������˯���ˣ������Ϸ�ү��ȥ�ˡ�����������������ɫ���ã��ؿ��ƶµûţ�����һͷ���亹��Ҷ��ʿ���ڸ������룬ū�ſ������е���ͳ���������֪������
����������˵�ţ�Ǭ¡�������һ�����Ԥ�У������Ѽӿ��˲��ӣ��ӵ���ų�������һ��ʪ��������������ʯС����Ҳ��ѭ���������Ӻ�Ҵ�Ž�ȥ��һ·����ϸ�����ţ������ʺ��������ˮ���£�����������������ˮ�顣����ī�մ��鼸����Ѿͷ���ѿ�������һ��������Ÿ������¡��������������ѥ������һ˫�����ɵij������������ˣ�ֻ��һ���������ߺ��������ۣ�������ſ�����
������������������Ũ�ҵ�ҩ�㣬��������Ǽ����������ļ�į���յ�̴����Ϣ�������������ϵĻƸ���������ǰ�İݵ澲���ذ��������Χ����λ�������Ŷ�ʮ������Ů̫�࣬�Կ�ȥ�տ�᯼ŵ���һ�������������ϱ�һɫ���Ǵ���Ƕ��Ĵ�����է���������Ǿ��ð�����������ǰ���˶��·�Ҫ��һ��ѹ�ֵ�����������������Ƭ�̵���微���Ʋ���ů��������������һ������Ϊ���������ӣ������ʺ�����ü������������������ǻ������˰��������ǰ����һ�㡱
��������ů����ֻ�����ĸ���Ů������ִ�����ڽ��䡣Ҷ��ʿ������β��С�ĵ������������ù��˵��룬����������ģ������ӷ�������ʲô���ţ������Դ�����£����������ϻ����ż��κ��顣Ǭ¡������һ�ۣ��ս��ʺ��������ˣ���������˵�������ռ��˼�������ͳѫ������˵�Ƿ��Ų�����������������
�����������������˳�ȥ�������¡�
���������ʺ����ɫ���죬����ϸ����Ӻ�Զ�ķ���ﴫ��һ���������ذ��˰���˵����Ǭ¡�㿴���ˣ������Ĵ���һ��������Ҷ��ʿ�ͼ�������������Ϣ����������˳�ȥ��Ǭ¡ϸ�������������������ģ���ô֣�����µģ�˵ʲô�������ǻ���й¶���ɣ�߯��ϸ���ˡ��������ʺ������ֹס����������ͫ���ƺ�����û�����������ƣ���������Ŭ���������ɷ·��ھۼ��������������������Ž������ٵĺ�����أ������üͷ������ʲô�����ǻ�Ҫ���������־䡣Ǭ¡������ǰ�����㣬˵������������Щ��˵˵�ż����Ұ��ľ������Ҿ������������š�˵�ţ������Ѿ����ʡ����ҿ��¾�Ҫ�����ˡ��ʺ�һ�仰˵����Ǭ¡�����������Ŀڣ��������ƿ������֣�ȴ���ñ�������ָ߬�ţ���ȻһЦ˵�����������ڹ����й����Ѿ������յģ��ܻ������ҵ���Ը����ϲ�����������Ҳ�����Ҷ��ʿ����ҽ�ǵij�ȫ���Բ�����Ҫ��������Ҫ�������ӻ��硣���Ѵ�Ӧ�����ġ�
�������������ǡ�����
�����������ڹ�����ȷʵ���˾���Ҳ����������������ӡ�����û�˸�ί���ң������������廣�����ҡ��ʺ���Ŀ������������ɫ�������������Ƶ�һ˿Ѫɫû�У�������һ��ʲô˵�����������ֻ�в���֪�����ϣ��������������������࣬�����š�
���������������ѳ�����齱ߣ���Ǭ¡Ŀʾ�Լ�������һ����ң�ߵ��ͷ����һЩ��ȴ��˵�������״Σ������ϣ������ū�������������ɷ�˵ġ����������DZߣ�����ҹ����Ǿ���˵�Ļ�Ҳ���ѻ����ӣ���Щ����ϵ���ֲ��ܲ������ӡ�Ǭ¡֪��������ԣ�����ԶԶ�鰴һ�£�˵��������ƽ���̺��ʹ˵�����������������ػʺ�̫����������ǰ�������������ף���Щ�ϻ������ˡ�������æߵͷ���ǡ����������ޱ�ͷ���������ѱ�ô���������
���������������������䷭�ij��ϵ����ӣ��������Ž���������Ҷ��պ��С���ӣ����Ǽ�����Ѿͷ�����ڸ����↑��һ���ӽ������������Ż���ʳ�������������ᆱ��ã���ߥ���ų�����Ժ��ɢɢ���������dz���ʱ���Ͻ��Ķ��ᣬ���������˳����ſ������ӷԸ��˼���ʲô����Ҷ�û���⡣
����������������������Ӳ�ʣ�ֻ���ų��˵�Ͳ������Ƿ��ˡ���ʱ����Ѻڶ��������ȵ���Է��ʯɽͤ�DZ�ת����һ��������̫�ܣ����ŵƺ�ɭɭ�ġ�С����˵�����DZ������еĻ���Ҫͨҹ�õ��գ���������˯�����д��쿪�ľջ���������������ܿ�������������е���ˣ���������˵�������Ǹ���ɢ�ſ������ɣ��Ҿ������ſ��������������������ӹǶ�����֪��������������û�˵ģ�ū澾��ڸ�ǰ�̺�
����������ƫ��ʱ��������������������ᱱ���ﴫ������������������������������ŵ�û�ˣ�����������˵����ô�����ŵƣ�����Ҳ��֣����Ų�����ȥ����ʱ��������ˬ����һ��һŮ����ͷ����֪����ʲô���¶���˵���Ļ�����������ã���
�������������ڵغ�������Ҫ����ֹס�ˡ�Ǭ¡����һ��������ͷ��ʱ���ˡ����ǵ��ϴ�Ҵ���һ������ˣ���˵ã���������һ���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