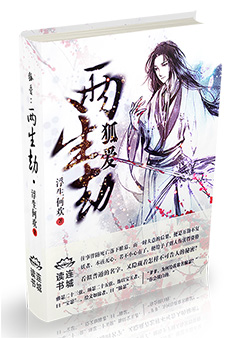梦在大唐爱-第1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状,武婉仪似有愧怀道:“怎好使得?”
江采苹浅勾了勾唇际,解颐道:“有何使得使不得的?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何足挂齿?姊不怪吾喧宾夺主便好。只要姊的身子,早日见好起来,今下做甚么都是值得的。”
武婉仪幽幽长叹息了声,反手握住江采苹玉手,好半晌的无言以对。而此刻,云儿已然步于外,抄起搁于庭院一角的扫帚扫起满堆于庭中的落叶来。
之前出阁时,原是月儿自荐去尚药局请太医,江采苹却遣了彩儿去,看来,江采苹早有先见之明,甚晓这趟差事并不如想象中好干,不无顾及月儿才从大理寺天牢特赦回宫,故才差遣彩儿去尚药局,将月儿留于梅阁看管那两竹匾唐梨子干。自月儿回宫以来,后。宫中那些专爱嚼舌根的长舌妇见日里断是未少叽咕流言蜚语,连日来之所以让月儿好生待在阁内休养,在云儿琢磨来,外出办事的差事儿江采苹不是交由其来做便是全权委以彩儿,实则是为月儿着想,不想阁外的闲言碎语传入月儿耳中,再者说,月儿关押在天牢足有三五个月之久,期间梅阁里里外外大小事全是由其与彩儿两人承担下来,近来与宫中多位太医混得也较为相熟,故,从面子上而言也罢攀交情也罢,凡是凡事总比月儿才乍一回宫要好说话的多。
“方才江梅妃说及武贤仪,倒叫嫔妾想起一事来。”良久相对无语,武婉仪不咸不淡的打破了沉寂,闷咳了声,才又蹙了蹙眉道,“说来也是旧时人之旧时事。”
江采苹看似饶有兴致的“哦?”了声,跟着轻蹙了下娥眉:“姊若不嫌厌烦,不如讲古与吾听。”
邢御医未至前,江采苹与武婉仪刚好说提起当日家宴之上的事,刚才人多嘴杂,自也不便多说,此时殿内已无第三人在场,江采苹倒也不急于这一时半刻催问武婉仪,彼此既然俱心照不宣,便看谁坐得住耐性。倘或武婉仪早已洞若观火,有心替江采苹解惑,即使江采苹不催问,武婉仪想说总会说,反之,若不想告知其中隐情,纵使江采苹磨破嘴皮子也不见得即可从武婉仪口中讨出半句真话来。
反观武婉仪,低垂臻首,貌似须臾沉吟,才不急不缓启唇道:“那是开元初的事了,嫔妾犹记得。那一年间,花萼楼才落建于宫中未久。当时亦值疾风扫落叶的时气,有日宁王出猎回府,带回一女子,杏眼桃腮,冰肌玉肤。宛似出水芙蓉,整个一美人坯子。”
江采苹心下巍巍一颤。听着武婉仪回述,脑海没来由的一闪而过一抹窈窕影儿——杨玉环天生丽质、娇媚迷人、回眸一笑的眉眼。月前的那场家宴,寿王李瑁并未携带时为寿王妃的杨玉环一块入宫赴宴,今刻思量来,当时一见李瑁是孤身一人出席时分,身边只有咸宜公主及其驸马杨洄,江采苹可谓既暗暗庆幸不已又心绪不宁,加之宴飨之上又扯出高都公主府上黄女一事,切实无暇细究。事隔多日。这刻江采苹尽管心中有数,武婉仪口中所述女子绝不可能是杨玉环,然而,许是压于心头的这桩心病由来久矣。第一反应上仍忍不住闪过杨玉环的那张脸……
顿了顿,武婉仪方又像极是在自言自语般苦笑了下,全未察觉江采苹面上的晃神,只徒自平添了分哀戚之色,道:“宁王的府邸建于胜业坊,由花萼楼便可眺望见宁王府。自那一日宁王出猎回府,府上夜夜便有女子高亢清唱秦声,如娇莺初啭,一唱便直冲云霄,声声妙音隔着宫墙。于花萼楼上便可细闻见。”
“莫不是。陛下召了那女子入宫?”江采苹情不自禁插了句嘴,直觉心上剜过一丝莫名的绞疼。
凝目江采苹。武婉仪凄苦无比的哧笑了声:“何止是召见入宫?一入宫,陛下便为其美。色所迷,封为莫才人。宫人美其名曰‘莫才人啭’。”
美人美。色妙音,试问世上有几个男人不为之心动?江采苹微觉朱唇苦涩,垂目未吱声,秦声是种古老的唱曲,李斯曾云,“夫击甕扣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简而言之,古老的秦声即为仰天击缶而歌之。莫才人既善之,可想而知,足以令人动容情动。
但听武婉仪闲闲说道:“圣宠之下,焉能不招人妒恨?半年之后,莫才人怀上皇嗣,十月怀胎,眼看临盆在即时候,宫中却生出一场大乱子,有宫婢泄露,莫才人养了姘头藏于宫外,隔三差五扮成小给使混入宫来幽会,行苟且之事。”
江采苹心下一震,沉声追问道:“怎会有这等事?莫才人不是出自宁王府上?难不成……”
瞭眄江采苹,武婉仪斜倚于榻上,语味不轻不重道:“空穴不来风,兹事体大,龙颜盛怒之下,下令彻查此事,不成想事发三日之后,果是在莫才人寝殿中逮住一名趁夜潜入宫中的男人,且是个光头僧人。家丑不可外扬,圣谕未着三司会审,就地动了板子,连夜于御前严审,起初那人闭口不招,后经不住毒打,才供认不讳,招认是入宫来与莫才人私会,苦于风声紧,数月未见却又耐不住相思,故才出此下下策。”
江采苹心上一紧,少顷怔愣,紧声关切道:“之后如何?”
武婉仪暗吁口气,叹息道:“唉,还能如何?龙颜震怒,当场命人把那人拉下去杖毙了。”
“莫才人及其腹中皇儿呢?”不知何故,江采苹忽而颇感心凉,不知是为武婉仪口中的莫才人而悲,究是在徒自伤感。
武婉仪紧蹙下烟眉:“莫才人受惊过度,从头到尾亲睹了整个杖毙,血淋淋溅了一衣身血腥气,一口气未提上来硬生生昏厥过去,以致一尸两命,母子俱未得以保住。”
四下的氛围,一丝风也无,有分窒息。透过纹丝不动的层重帷帐,可见殿外的日色越发暗淡无光,不觉间已是黄昏时辰,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吱呀”一声轻响,倏然卷入门内来一阵凉风,吹得竹笼中的光点瞬间忽明忽暗摇曳于帷幔上,殿内一室的光影斑驳。
“谁?”见从帐幔外飘入一道人影,江采苹下意识侧首瞋叱了声。待来人掀撩起帷幔歩近,才看清竟是云儿。
冷不丁被江采苹一呵,云儿不由脚下一滞,旋即行礼道:“娘子,翠儿、彩儿已回来。奴瞧着,外面天色已沉,像要下雨,娘子可要先行回梅阁?”
“天黑了?”隔着门隙,江采苹望眼外头的天色,突兀觉得眸子酸酸的。
武婉仪适时接话道:“累及江梅妃大半日,眼下时辰已是不早,想是陛下也该用膳,倘使找不见江梅妃,嫔妾着是担待不起,江梅妃且回吧。”
江采苹稍显迟疑,这才步下榻,整了整衣摆,含笑自若道:“那姊姑且好生歇息,吾明儿个再来看探姊。”
云儿立马近前,江采苹搭上云儿臂腕,又道:“姊可有甚么想吃的,回头吾让人备下,隔日带与姊品尝。”
武婉仪抿唇摇了摇头:“不劳江梅妃费心了。改日嫔妾身子见好了,再行上门拜谢江梅妃今日看顾之恩。恕嫔妾今儿个不远送了。”
江采苹颔首展颜道:“瞧姊这话说的,可不又见外了怎地?既如此,姊好生休养几日也罢,若姊身边使唤的人手不够,回头吾差月儿过来侍奉几日也无不可,月儿煎药尚是把好手,只不知姊意下如何?”
武婉仪看似满为感念于怀道:“嫔妾有翠儿侍候左右,早生习以为常了。江梅妃身边的近侍也不多,便不劳旁人来回折腾了。”
秋风起兮白云飞,纷纷坠叶飘香砌,数树深红出浅黄,江采苹提步出婉仪宫时,已是酉时三刻,因变天的缘故,或远或近的宫灯已然早早掌亮。
云儿亦步亦趋于旁搀着江采苹,每走一步均甚为谨翼。彩儿跟于后,边走边扭着脖颈,看时辰早过了夕食的点,想必今个不用忙活着备膳了,今日跑前跑后,这两条腿都快跑断了,肩酸脖僵,简直比备膳还累。
忽而一股风擦着脚底刮过,江采苹抬手遮了遮双眸,云儿连忙关询道:“娘子可是眯了眼?”
“奴为娘子吹吹……”彩儿立刻步上前,却见江采苹摆了摆手,徐眯着清眸道:“无妨。”语毕,面色凝重的继续朝前步去。
彩儿见了,不解的挠挠腮颊,只好作罢,忙不迭紧走几步跟上。
刚才在婉仪宫,云儿便察觉江采苹面有异样,只是不宜多问而已。这会儿出了婉仪宫,走在回梅阁的宫道上,江采苹看起来更为百愁在心满腹惆怅的样子,只不晓得武婉仪到底跟江采苹说了些何事。
正文 第250章 玉殒
听见阁外传来脚步声,月儿立时迎上前,但见果是江采苹带着云儿、彩儿回阁来,忙缉手行礼道:“娘子可算回来了,夏给使候于阁内等了足有一个多时辰了。”
江采苹一愣,云儿、彩儿同时一怔,顺着月儿使的眼色看去,只见小夏子已是于后紧跟向前来:“见过江梅妃。”
江采苹不动声色隐下心下诧异,旋即言笑自若道:“夏给使几时来的梅阁?”
“回江梅妃,仆原是奉陛下口谕过来给江梅妃捎话的,不成想江梅妃未在阁中,故才于此敬候。”小夏子躬身作答着,看不出有甚么异色。
稍作沉吟,江采苹正色关问道:“且不知,陛下有何谕令?”
“白日申时一刻,陛下得报,薛王染疾,情势不妙,闻悉差仆特来告知江梅妃,未料江梅妃不在梅阁。”
小夏子说的不慌不忙,听者却多吃诧不小。尤其是云儿,显是颤栗了下,猛地抬头看向小夏子,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薛王染疾?”感触到云儿搀扶着自己的皓腕一颤,江采苹眼风微扫,从云儿脸庞上一带而过,权当视而未见云儿的失态,顿了顿,方又蹙眉细询道,“何时的事?陛下怎说?”
云儿稍定心神的刹那,但听小夏子回道:“陛下一得知薛王染疾,便摆驾出宫,幸薛王府去了。陛下本意江梅妃随驾,只因一时未找寻见江梅妃,故才遣仆折回,且待江梅妃回阁,及时跟江梅妃言语声,以免江梅妃担忡。”
李隆基既已亲临薛王府,想必宫中奉御、太医一干人等十有九成一并随驾同行在内。多少可免人忧忡。不过,仅就时辰上算来,李隆基出宫的时辰似乎与彩儿前至尚药局请邢御医相吻合,即便彩儿抢先了一步,之后彩儿与翠儿跟随邢御医回尚药局取药的工夫里,想是对此也该有所耳闻才是。
然先时回阁的道上。彩儿却只字未提此事,不晓得其中是为何故。江采苹正丛生纷扰时分,却见彩儿细眉一挑,像极想起甚么一样煞有介事道:“无怪乎奴去取药之时,尚药局连一个太医也不见了……娘子,当时奴跟……”
彩儿正欲说释甚么,一抬眸却正对上江采苹瞋嗔之色,登时欲言又止在原地,杵着身有些手足无措。
白眼彩儿,江采苹敛色向小夏子:“陛下现在何处?”
小夏子如实作应道:“仆一直敬候在梅阁。不曾回南熏殿,想是圣驾尚未回宫。”
无状般环目阁外越发暗沉下来的天色,江采苹凝眉道:“劳烦夏给使了。本宫且让云儿,与夏给使先行一同回南熏殿看下。倘使圣驾已回宫,有何事也便让云儿及时通传与吾。”交代着,看了眼云儿。
“是。”云儿立马屈了屈膝,应声与小夏子疾步下阁阶去。
目注二人行色匆匆朝梅林间的小道走去,身影消失在朦胧的暮霭之中,江采苹这才提步向坐榻,有分倦乏的倚靠下身。今日发生的事,着实有够杂乱,多得叫人闹心不已。先是武婉仪那边,接踵而来的又是薛王府。当真不让人松口气。
见江采苹的面色不是一般的凝重。月儿极谨小慎微的端持过茶盏为江采苹倒了杯清茶。接过月儿奉上的茶,江采苹缓声道:“日间未找见吾。可有责斥于汝?”
月儿摇摇头,不无唯诺道:“只问奴娘子究是去了何处,奴未敢告知夏给使,娘子是去婉仪宫了,只道娘子出阁游园。夏给使跟奴干着急了会儿,倒也未说甚重话。”
江采苹浅啜口茶,暗吁口气。其实,适才一进门,看见月儿率然迎上前来使眼色,足以猜知,月儿定未跟小夏子说实话。反倒是彩儿一根肠子通到底,方才当着小夏子的面,差点说漏了嘴。
睇目彩儿,江采苹温声道:“且去备几样清淡的膳食,以待少时圣驾至,权当用夜宵。切记,管好自个的嘴,少多嘴。”
彩儿悻悻的垂着首未吱声,月儿嗫嚅道:“前刻奴见天色有变,便把晾于庭院里的那两竹匾唐梨子干暂且收进庖厨了。”
搁下茶盅,江采苹莞尔道:“先收着便是,回头装入纱布袋,吊于通风向阳的凉处,时而抖一抖,隔一阵子翻一翻,见日动它两下,莫潮了烂了即可。且下去吧。”
月儿于是和彩儿恭退下,步向庖厨打下手。江采苹独坐于阁内,支颐闭目养神了片刻,奈何心静不下,脑海更是挥之不去在婉仪宫时武婉仪跟其说提及的莫才人一事。
虽说武婉仪只是粗略回述了番罢了,但撺掇于江采苹耳中,女人的直觉告诉其,武婉仪绝不是无缘无故提及莫才人,尽管不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但由武婉仪口中,不难听辩出,当年莫才人之事显是存在诸多疑点,可惜今下早已死无对证。转而一想,只怕此事多与武贤仪脱不了干系,否则,武婉仪断不会由武贤仪身上平白无故扯及莫才人的事,事后忖量来,听似是在刻意暗示些甚么事。
其实,对于武婉仪与武贤仪,甚至乎是已薨的武惠妃,江采苹总觉得这三个人之间仿乎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哪样纠葛,只是其入宫较晚,一时无从查悉而已。至于莫才人一事,眼下唯有待它日得闲,再行向武婉仪私下请教。毕竟,莫才人之事当年可谓宫闱一大丑事,轻易直言不得,省却活人为死人吃罪。
约莫戌时二刻,李隆基才乘坐龙辇驾临梅阁,云儿一块返阁来。闻见仪仗声响,江采苹自知是圣人至,遂起身恭迎圣驾。
李隆基看似一身的疲惫,身上夹带着丝丝夜凉如水的凉息,一步入梅阁,便执过江采苹玉手偎身坐榻上。
江采苹径自斟了杯茶水奉上,凝睇李隆基,忽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忍不住问出声:“陛下。陛下这龙须,怎地短了截儿?”
唐时,女人以小眼肥脸为美,男人贯爱蓄撮小胡子,自以为是成熟有型又不失为帅气的象征,是以。放眼街头,白净又带撮小胡子的男子。最受女子青睐有加。当然,这是在杨玉环由寿王妃摇身一变成为贵妃之前,自杨贵妃宠冠六宫之年起,世人才风行视女子以胖为美。
李隆基下颌上留的胡须,确实微呈卷曲状,好像被火燎过似的。倘若不近观,不仔细看,倒也不易发现。
被江采苹一问,李隆基还未应语。只听高力士已然怨尤道:“陛下,老奴怎说的来?老奴早便说,江梅妃必有此一问,陛下还想瞒着。”
听高力士这般一说。江采苹不由纳闷,抬首道:“究是怎回事?陛下要瞒嫔妾何事?”
斜睨高力士,李隆基吃口茶,才一笑置之道:“爱妃莫担忡,并无甚事。朕的胡须,不过是一不留神儿被火燎了下,并无大碍。”
“龙须怎会被火燎及?”江采苹一叠声打破沙锅问到底道,看一眼李隆基衣身,又紧声关切道,“陛下可有无伤及旁处?”
含情轻拍下江采苹素手。李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