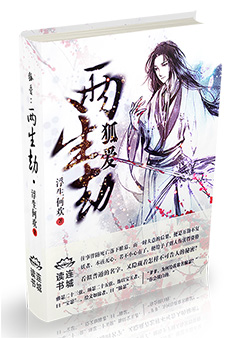梦在大唐爱-第20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话怎讲?难不成教坊中事,与本宫牵有何关扯?”江采苹紧蹙下眉,越发有分费解,宫中教坊掌俳优杂技教习俗乐,属太常寺,且多以宫中给使为教坊使,即便发生男女私通之事说来也该交办太常卿查处,譬如一些琐碎小事亦大可交由司宫台协办,既非淫。乱后。宫之事,八竿子打不着,何时又轮到过后。宫多加过问了。
见江采苹误解其意,高力士忙作释:“是老奴一时急糊涂了,未把话说白,事情是这样的,侯青山所状告之人,不止是其结发之妻裴氏,还有教坊长入艺人赵解愁,正因此,陛下十为恼怒,才命老奴急请江梅妃前来。”
“赵解愁?”江采苹不由吃了诧,“听阿翁言下之意,莫非侯青山之妻裴氏私通之人,是为赵解愁?”
高力士叹惜着点了点头:“侯青山与赵解愁同为教坊长入艺人,二人俱善顶杆之舞,侯青山之妻裴氏,亦是为教坊名唱,弹筝独妙,早年未入教坊之前,便与侯青山结为连理,不知怎地,又与赵解愁生了私情,唉!”
听高力士这般一说,江采苹才略知整桩事情的因由,原来赵解愁与侯青山竟是同行,有道是同行见同行,见面如仇人,侯青山与赵解愁之间的恩怨纠葛或许并不像表象上听起来那般单纯化。至于侯青山之妻裴氏,前日李隆基在花萼楼设宴款待皮罗阁时,江采苹犹记得殿上中场登台一位手抚一把古筝、抚筝极为风月闲好的风韵犹存的歌姬,媚眼桃腮,今刻听高力士一说,直觉那人即为裴氏。
见江采苹似有所思的未置一词,高力士回头看眼南熏殿,适中虚礼做请道:“陛下既召江梅妃来,想是自有其理。江梅妃姑且稍候片刻,老奴这便入殿通禀。”
高力士的话均已说到这份上,江采苹遂随之步上殿阶,暂且候于殿外稍作静待,本以为李隆基是为曹野那姬的事传召,着实未料教坊竟出此丑事,且不管此番召见因何而起,李隆基又是何意,正如高力士所言,都已步至殿门外总要先容人入殿通禀声才是,省却平白无故的害人被迁怒问罪,至于少时是去是留尚在其次。
正文 第323章 毒害
高力士入内通禀不大会儿,江采苹就被请入南熏殿,一步入殿门,就见殿内跪了一地的人。
最先触及于目的即是赵解愁,这个昨日还登台在花萼楼前的千秋节上以顶杆之舞引动整座长安城为之欢呼雀跃的教坊长入艺人,才不过一夜之隔,今刻却沦为与人私通的状告对象,且是一状告到御前来。
在赵解愁身边,还跪有三人,其中的两个男人看上去与赵解愁年岁相仿,皆身着教坊使的衣帽,想是这二人中定有一人是为侯青山才是。至于伏首在最右侧的那个女人,只一眼,江采苹即可凿定,这人必为犯妇裴氏,且单看其侧影已足可辨识出,此人正是在前日的千秋盛宴上弹筝独妙的那个教坊名唱。
教坊总管范安及伏首在最前,从背后瞧去,整个人诚惶诚恐的正伏趴在地,一动也不敢动,像是犯下大过的人是其一般。但话又说回来,三日的千秋盛宴才过,宫城皇城尚沉浸在千秋乐中还未欢兴过劲儿,今日就闹出谋杀亲夫的丑事,范安及身为教坊总管,自也难辞其咎。现下龙颜震怒,但凡有点脑子者,谁人不唯恐被迁怒及身。
“嫔妾参见陛下。”环睇殿内诸人,江采苹轻移莲步,温声细语的朝端坐在御座之上的李隆基盈盈行了礼。云儿趋步在后,随之缉手屈了屈膝。
高力士引请江采苹入殿之后,就自行恭退在一旁,未多言半句。殿内除却与此事相关的一干人等。并无几个宫婢侍奉在下,连御侍均未在旁候着。
闻见江采苹的礼拜声,龙目微皱,李隆基这才微启长目。朝江采苹伸出手,示下江采苹近前。
日晖由半敞开的殿门处斜斜地倾洒入殿,不偏不倚正映落在了殿央。余晖映天红,幕霞缤纷,南熏殿内也笼罩上一层薄薄淡淡的暮光,若有似无染着七彩旖旎之色,只可惜与四下的氛围并不相称,甚至有些大煞风景。夕阳无限好,只是宫中多风云。
江采苹曳地的裙摆从殿央暮光中轻轻拖过。未发出一丝声响,诸人越发的大气儿不敢喘下,直至江采苹搭上李隆基温热的大掌,提步绕上御座旁,范安及等人看似才暗吁了口气。一样的俯首在下未敢抬下头。
“陛下传召嫔妾来,不知所为何事?”凝目近在咫尺的天颜,江采苹不露声色的止步在旁,龙颜貌似有分倦怠,许是在昨夜的温柔乡里太过纵情尽兴之故,以致这时辰点眼睑上都还隐隐可见未消下去的一圈黑眼圈,直叫人觉得刺目又心寒。
昨夜江采苹倒是酣寐了一宿,今个日上三竿才寐醒,这大半日在梅阁独自一人静静地观赏窗外的细雨霏霏。心绪已是平复不少,原以为自己根本不会过于去在乎李隆基的纵情声。色,毕竟,宫中的女人就像百花园的花儿,自古就开不尽,也便无所谓悍妒成性。然而此时此刻,近距离的感触着李隆基神色间掩饰不掉的**,同样身为女人,想要抑制得住心下的刺痛,又谈何容易。
推己及人,难怪自古以来,后。宫的争风吃醋就永无宁日可言,爱之深情之切,即便只为荣华富贵,即使只为争权夺位,宫中的女人势必也须有圣宠才可翻身,才有盼头,而唯有恩宠不绝方可屹立于不败之地。如此一来,大凡不想被人恣意践踏在脚下的女人,不希卑卑贱贱苟延残喘在深宫高墙藩篱之下的女人,又有哪个不会挖空心思费尽心计的去争宠,哪怕只是一搏,指不准即可大显大贵,人性多在扭曲下成长,无休止的宫斗其实仅是这些可怜女人的一种宣泄罢了。
江采苹暗自晃神的刹那,但听李隆基声音浑沉道:“宫中教坊,自高祖置于禁中,开元二年,朕,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于长安置左右教坊,本掌俳优杂技,专司教习俗乐,不成想今时竟丢尽朕的颜面!”
沉声说着,李隆基已是恨恨的一指殿下,直指向伏首在下的范安及、赵解愁等人,显是盛怒尚未消减,略顿,才又霁颜道:“其等无不忝居教坊使,素日有失其职不说,为人师表,却不重德业,更胆敢在宫中私通,尤为不容宽赦!”
眼见李隆基怒不可遏,江采苹环目早已惊恐万状的范安及、赵解愁、裴氏等人,适时轻握了下李隆基的大掌:“陛下息怒,龙体为重。”
虽说前刻在殿外,高力士已将整桩事情的原委大致告知了遍,江采苹也知侯青山今次告御状,是为裴氏与赵解愁私通一事,但“抓贼抓赃,捉奸成双”,且不去细究此事是否另有其它不为人所知的隐情,这会儿李隆基正在气头上,如此的怒发冲冠,稍有不慎只怕被问罪的不止是赵解愁与裴氏,就连整个教坊恐怕也将被迁罪。事关重大,此事一旦闹开,小事闹大,难免又要在宫里宫外传的沸沸扬扬,届时再想大事化小恐将为时晚矣,到时候丢得可就不光是李唐家的体面了。
尤其是今下,日前皮罗阁才晋献入宫三名南诏舞姬,纵管有且只有曹野那姬一人在昨夜一沾雨露,未可知现下留在金花落侍候曹野那姬的另外两名舞姬它日就全无被宠幸的机会,教坊私通一事,说来事发的确实不是时候。可想而知,今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的勃然大怒,想必也不无顾及在此,倘使这桩宫廷丑事传去南诏,大唐声威不免受损,不能安家又何以治国。
何况皮罗阁昨日才起程回太和城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或许皮罗阁还未返回南诏,宫中教坊的丑事已然先由长安传去太和城,严正诲领旨一路护送皮罗阁一行人马回南诏国,如若在途中听闻此事,又当以何言相对皮罗阁一行人的问由,免不了落人笑柄。曹野那姬才为新宠,宫中就生此事端,又怎不让人看笑话。
李隆基是为一国之君,大唐当今天子,本不必为这点小事儿烦忡,大可交由太常寺、司宫台合力一查到底,正是顾及南诏,顾及皮罗阁与曹野那姬,多半才为此大发雷霆之怒,不然,江采苹伴驾这几年,不管宫中发生何变动,也不曾见李隆基动此怒气,当庭火冒三丈,看来,男人的颜面扫地也要分是为何人何事。
龙颜震怒,殿上诸人可谓人人自危,无人敢吭一声,好半晌一片死寂,才听赵解愁哆哆嗦嗦的认罪道:“仆、仆认罪……是、是裴氏勾引仆在先,仆、仆一时意乱情迷,才铸成大错,求陛下宽罪。”
赵解愁这一出声,殿上登时发出一声倒吸气声,只见裴氏立时怒瞪媚眼,难以置信般叱向赵解愁:“你!适才你说甚么?怎地会是奴勾引你在先,当日明明是你喝的酩酊大醉,赖在奴家榻上,硬缠着奴不放!”
裴氏与赵解愁这一对质,虽是狗咬狗一嘴毛,却犹未自觉两人的奸。情已从自个嘴里抖露出来,侯青山听在边上,一张脸早已气得铁青,家丑不可外扬,但事已至此,若不一状告到御前来,只恐终有一日会被裴氏与赵解愁谋害掉,死不瞑目。
“启禀陛下,这个恶毒的女人,原欲在仆的米粥中下毒,赶巧在前两日,仆偶感风寒亦未能在千秋节献技,抱病在榻,幸得衔山发觉裴氏近日行踪诡秘,日间又撞见其与赵解愁一同出现在城中药铺,二人勾肩搭背,便将此事告知仆,仆本也不信,当夜夕食时,却见裴氏果然在仆的那碗米粥中动了手脚……”侯青山埋首在下,一五一十的说到这儿,竟是低低哭啜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大男人家当着这般多人的面竟泪不成声,也着实让人于心不忍。
这时,跪在侯青山一旁的郑衔山接言道:“启禀陛下,仆与青山是为同乡,早年又与青山一年入选教坊,当上长入艺人,仆资质不及青山,这些年在宫里更不敢逾矩半步,对功名利禄从未敢有过非分之想。但青山与仆自小一块儿学艺,看其娶妻成家,仆自为之欢喜,谁曾料,那日在城中街巷上,无意间却撞见裴氏与人商谋下毒毒害青山,仆着是不忍青山白白枉送掉性命,怎奈平日仆与赵解愁亦多少有分交情,两难之下,故才花了点碎银让人及时给青山捎话,交嘱其傍晚倘若有人送米粥上门,万莫吃。”
片刻泪下,侯青山渐渐平复下了激动不已的心情,才又上禀道:“当日,仆见裴氏亲手为仆端来米粥,一碗煮有几颗红枣,一碗清粥,仆一贯不喜吃甜,但躺在病榻上的这几日,一连三日服食汤药,便想吃那碗甜粥。不成想裴氏却一手抢了过去,面带仓惶,还打翻了那碗甜粥,当时仆便心下起疑,裴氏又道清粥有些凉透,要为仆端出屋热下,仆便强撑下榻,果见其背着仆,急急奔出院门……”
正文 第324章 情恨交孽
侯青山见裴氏神色慌张的疾奔出院门,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心下生疑,于是强撑着病体步下榻,欲暗中近观裴氏究竟有何勾当。
裴氏端着那碗清粥夺门而出之后,一时急于与掩身在院墙根底下的赵解愁谋划着如何除掉侯青山,大意之下全未发觉身后暗藏了一双眼睛,一直在不远不近地密切盯视着其的一举一动。
裴氏与赵解愁原合计着在米粥中下毒,侯青山这几日偶感风寒,抱病在榻,一日两餐只吃小半碗清粥,所服食的汤药不便从中动手脚,是以二人商酌之下,才决意在城中药铺买了包无色无味的砒霜,掺和在清粥中让侯青山吃下。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裴氏与赵解愁千算万算却未料及,当二人鬼鬼祟祟的相约在东市一家药铺门外碰头时,刚巧被路过的郑衔山撞了个正着。平日郑衔山与赵解愁也算有分交情,两人与侯青山同为教坊的长入艺人,在宫中教坊当值多年,纵然难免有意见相左之时,又怎会连半分交情也谈不上。当时,郑衔山本欲上前跟赵解愁打了个招呼,毕竟,这几年赵解愁可谓教坊使中的大红人,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说郑衔山与侯青山俱会耍顶杆,却及不上赵解愁之精绝,正因此,今年的千秋盛宴上俩人才讨了个空缺,不必登台献技。
让郑衔山始料未及的却是,刚欲迎上前跟赵解愁寒暄几句,关切下是否连日来勤于练技累坏了身子。故而来药铺抓些补药,不经意间竟看见裴氏偷偷摸摸地从对面布庄走过来,转即与赵解愁神神秘秘的往前方不远处的一条暗巷走去。郑衔山一时纳闷,不知裴氏何时与赵解愁这般相熟。甚至连在大街广众之下都不避嫌,走个路都勾肩搭背,倘使让不知情的人瞧见。指不准会误以为二人是对老夫少妻。好奇害死猫,人都有莫名其妙好事儿的时候,郑衔山一时好奇,遂跟于后欲一探究竟,这一探不打紧,无意间竟窃听见裴氏与赵解愁在暗巷里密谋下毒毒害侯青山一事。
“仆当时着实吓了一跳,不成想裴氏胆敢与赵解愁私通。且欲毒害青山,谋害亲夫。”郑衔山慢条斯理的回述着当日情景,将在城中街巷上的所见所闻如实作禀在下,如此一来,裴氏与赵解愁的私情越发遮掩不住。
天颜高高在上。圣怒难犯,侯青山又细细禀述了一番当夜裴氏与赵解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趁着月黑风高拿土袋谋害其的情状:“仆躲在院门内,纵未来得及看清裴氏慌里慌张急奔出门去是欲与何人见面,却可听得出,院外与裴氏低声说话者的声音,那人正是赵解愁……”
当晚裴氏虽备了两碗米粥,一碗红枣甜粥,一碗清粥。本以为侯青山会吃那碗清粥,裴氏才只在清粥中下了砒霜,怎奈侯青山竟端了那碗甜粥吃,裴氏自知清粥有毒,又岂会自食清粥,当下计上心来。故作惊慌失措之貌打翻了那碗甜粥。眼看下毒失手,裴氏心下自也有些战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故才疾奔出院门找赵解愁商酌另行施策。
先时裴氏带粥回门时,赵解愁就一路相跟,生恐有何差池,一人计短两人计长,万一事情败露也好凑在一块儿谋筹。一听裴氏说侯青山未吃那碗清粥,赵解愁即刻让裴氏回去,还怨尤了好几声裴氏,怨怪裴氏多事,既要在粥中下毒除掉赵解愁何必多此一举备下两碗米粥,若只备下一碗清粥,想那侯青山早已毒发身亡,又哪里还需为此多加烦忡。
江采苹静听在旁,环睇裴氏,心下不由泛上一丝怜悯之情,裴氏纵与赵解愁私通,然而在裴氏心底,毕竟也与侯青山过活了多年,一日夫妻百日恩,欲。火欲。诱下,裴氏纵下定狠心毒害掉亲夫,但未可知就忍得下狠心下得了狠手,即便裴氏备下两碗米粥,只是为了陪侯青山用最后一顿夕食,却也可见裴氏对侯青山并非就全无情分可言,终归还是有那么一分情意搅在其中。或许,这便是女人的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更是身为女人最可悲可怜之处,都道最毒妇人心,真正最毒的又何止是妇人之心。
“奴、奴认罪,奴是想谋害亲夫,但奴思来想去,终不忍下手……”人证物证俱在,这会儿裴氏亦已惊惶不已,忽而像极想起甚么似的,蓦地抬头为己辩白道,“那碗清粥,奴一回去便丢了,未再端入屋。扛土袋杀人的也不是奴,陛下明鉴。”
裴氏这一辩白,矛头显是针指向赵解愁,弦外之音自是说,那一夜扛土袋杀人之事不关其事,全是赵解愁一人所为。想赵解愁有本事担任教坊使,又岂止仅善顶杆,少不得还有其过人之才,譬如待人处事上的圆滑,对于裴氏话里话外的意思又怎会听不明懂,当即就与裴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