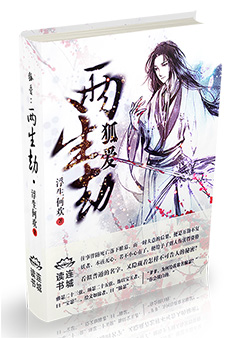梦在大唐爱-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亦正是于这刻,陈桓男也蓦地省悟到,其确实有与楼下者打过照面。且,上次和现下的这次,相隔并不怎久。而是,就在昨日。并且,所遇之地,亦非是旁处,恰是于江家——江家小娘子日前昭布、而于昨个举行的抛绣球招亲上。
这么连贯起来细一回想,陈桓男顿时凿定,之所以看着高力士眼熟,绝非是其凭空造就出的一种虚幻。遂又冲高力士身旁撒瞅了番。
陈桓男记忆犹新,昨个于江家门院内,其不止是与高力士一人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在场者中,尚有一个手摇一把玉柄折扇的男子,谈吐颇具分气魄,尤为招惹人注目。是以,较之于其他平凡无奇者,那人留予陈桓男的印象,自然亦铭记得格外深刻。
可惜,这会高力士身前身后,并无那持扇男子人影。仿乎亦正因此,理不通何故,陈桓男意识见,心底竟是没来由平添了些微失落味。那股子感觉,既说不清,也道不明,甚难以言喻。
有道是,仇人见面理应分外眼红。再度狭路相逢,之于陈桓男而言,少了那玉面男子的存在,无形中似乎欠失了份火候一样。说白了,无非是心理作祟,即便泄了怒,亦尤觉得不够解恨。毕竟,真正让陈桓男出糗的人,时下并未随之出场,其也就没法子与之真格的来场单对单的较量。
“陈明府所等贵客,可是到来了?”陈桓男暗生悱恻之时,仍旧站于边上尚未退却的陈掌柜,反倒犹豫着率先开口询了席,“可需吾下去代为相迎?”
陈掌柜从旁一出音,陈桓男立时被其有所提醒。心下略沉,转就示意陈掌柜向前:“且不急。陈掌柜先行看眼,那茶楼外的人,可熟识否?”
闻陈桓男吩咐,陈掌柜自是唯有听从号令的份。于是不无疑惑的凑靠向窗棂位置迈了小半步,当然也不敢借此为由,妄自将依是占据着大半个窗格的陈桓男挤压下身,仅能顺着陈桓男所指方向,伸长脖颈勉强瞟瞥陈桓男所言之人。
“咦?貌似有点眼熟……”窗格空间本就有限,即便在平日里亦只容得下一人观赏窗外景致,加之陈掌柜当下是与陈桓男同时堵于窗棂处,何况俩人体积原就并属发福的那类。故而初始时分,陈掌柜仅可观得见茶楼下之人映于晨曦中的那抹斜影而已,压根就窥不见来人眉眼。然而,待下立之人稍一侧转身姿,陈掌柜则随即看清楚了这人容貌,霎时低呼出声:
“这,这、这不是,高、高……”
“高力士,高将军?”发觉陈掌柜倏忽看似不是一般的激动,陈桓男刹那间亦幡然醒悟,未待陈掌柜磕巴顺流,便已径自一字一顿地及时插接了句。
闻陈桓男夹置带肯的反问,陈掌柜倍显错愕之余,忙不迭连点了串头。尽管费解,何以陈桓男身为明府,却像极并不识高力士庐山真面目一样?但也未敢冲动得把内里由感而发的这叹心声直白吐露舌尖。
时下的事态,但凡明眼人皆相摩得出,明摆着乃多一事势必不如少一事,可求得明哲保身。
“当今圣人身边,那位威名远扬的高力士、高大将军?”但见陈掌柜笑而不语,陈桓男楞被其笑得发懵,心中愈为没底,忍不住复又一本正经地沉质了遍。
倘若眼前所见所闻俱为真,这一切亦非巧合,此刻于陈桓男觉悟来,其已然犯了人生中某种最低级的错误。想来,又岂还能稳得住神,而不自乱阵脚。
“陈明府,叨扰了。”陈桓男径顾和陈掌柜变相“讨教”,却未来得及说论出个三六九的工夫,高力士本人已是自行踏入如家茶楼,闲步迈上茶楼楼上来。
眼见高力士倒先于诸人面前朝自己拱手,陈桓男越为汗颜,甚觉挂不住薄面。匆忙掠过陈掌柜,疾奔向楼阶:“高、高将军!不知高将军……高将军大驾光临,某有失远迎,真介个……”
陈桓男怀揣忐忑,更尚未从高力士身上反应过劲儿,仓惶之下,难免言不尽意,词不达意。
“哎,陈明府这般客套,岂不外见?”高力士却一如前响,脸上挂着笑呵模样,“同朝为官,即为同僚。将在外,无须讲究虚礼。”
官大一级压死人,高力士如是阐述,陈桓男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高力士彷佛待人挺温善,且并无意苛责其,这令陈桓男着实减掉不小的压力。而另一方面,高力士弦外之音,丝毫不矫揉造作的暗示了今时今日其本身所处的特殊性,话里话外好像皆别有寓指,陈桓男只恐,其是因于当日在江家发生的一系列事,前来咎罪。
“高将军。”陈掌柜见状,亦紧随于陈桓男之后,赶忙跟着朝高力士躬身,“吾不扰高将军、陈明府兴了,且就退下了。少时,如有何吩咐,传唤吾便是。”
正所谓“知人者贵也,自知者明也”。人贵有自知之明。单就目前局势,陈掌柜断不会将自个搅和入眼下的浑局内。见高力士与陈桓男俱未表态,言毕,就悄然压着步调,径直恭退往楼下去。
“高将军,请上座。”陈桓男眼梢的余光夹蔑陈掌柜独自离去的身影,见高力士对此未多加予以理睬,也就不便于额外吱声。但其内心深处,这会实则有些羡妒陈掌柜,恨不得走离开的人是其。
原因很简单。只因陈掌柜净可随性走人,换之于陈桓男,临末却未必亦可由局中全身而退。
高力士倒也未怎与陈桓男拘泥于繁文缛节,索性直接坐至正座上。其实,即使陈桓男不做作的相请高力士上座,这上座的座位,除却高力士,在场一干人等,也不见得有谁敢与其争抢。
“陈明府,请吃茶。”待各自落定座,高力士遂就斟了两杯茶水,并将斟在先的那一杯,递予向陈桓男,“且允某喧宾夺主,姑且以茶代酒,敬陈明府一杯。”
陈桓男屁股尚未坐安稳,却见高力士竟已亲自倒茶端茶于己,立马受宠若惊般从胡凳上窜起身,双手接过高力士手里的茶水。继而杵于原地,眼观鼻鼻观口,必恭必敬应道:“某愧不敢受。”
“陈明府何出此言?想这方偏僻地角,陈明府亦可治理的井然有序,人稠物穰,民风淳厚,钟灵毓秀。区区一杯茶水,理当受之无愧。”谁想,高力士却头头是道的恭维了番陈桓男,且奉承得有板有眼,有条有理。
“高将军盛情难却,某也只有却之不恭了。”陈桓男自不好当众驳高力士面子,唯有迎合人意,一饮而尽杯中茶水。
“坐。”吃完这第一杯茶,高力士方缓抬手,示意陈桓男回坐入座。
察晓高力士意欲继续动手蓄茶,陈桓男连忙眼明手快的接过茶壶,替高力士满了杯茶水。
“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这边,陈桓男刚把茶水倒好,却听高力士坐于座,语气颇掺无奈味的喟叹道,“在其位,则须谋其政,唉!”
“若言操劳,高将军切是为国为民没少鞠躬尽瘁。不像某,见日的只知愚忠。高将军才实乃群臣标榜!”见状,陈桓男忙恬着脸拍高力士马屁。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虽说其拍得有声有色,然其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实为薛王丛那张玉容。
时至现如今,自打接替陈彦方位子上任开始,陈桓男尚从未曾谒见过龙颜。昨个江采苹抛绣球之日,纵使陈桓男只与薛王丛打了几句交道,可其也有旁观于心,高力士似乎对薛王丛分外存份敬畏。于陈桓男狭隘的猜测观念里,这世上,能让高力士俯首的,仅有一人,即当今皇帝。其既未见过李隆基,亦不认识薛王丛,高力士这一来,陈桓男楞是想当然的把前二人合列为一。
“陈明府这席谬赞,万不可随便道于人。树大招风,隔墙有耳,以免招来横祸。”高力士摆摆手,瞻前顾后醒示毕,转而岔开话锋,不动声色的续道,“不过,珍珠村确是块风水宝地呐。某到来的近两日,倍觉心旷神怡。对了,某心中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某曾道听途说得悉,陈明府有意推选江家小娘子入宫?当真果如是?”
无论当讲不当讲,高力士均讲了,陈桓男亦只能洗耳恭听。话题虽拐得猛,却亦在陈桓男意料之内。换言之,对于高力士言及关乎江采苹之事宜,打由这回合一见到来人是高力士那刻起,实际上陈桓男本就已做有心理准备。此时,在陈桓男权衡来,高力士只是终于把此次前来的真正目的,或言,约其的初衷,才绕上正题罢了。
光天化日的,俩大男人干对坐着有一口没一口的吃茶,周遭陪同者除却“榆木疙瘩”,便净余“呆头鹅”,根本就索然无味。及早结束这场全无助兴节目的茶局,亦未尝不是桩叫人呶爽之举。
高力士肯把话明白的摊于桌面上,省却了尔虞我诈。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桓男反也觉得放得开了。半晌面面相笑,亦直接开诚布公承应道:“先时,某确曾有此意。然,昨日情景,高将军亦亲睹见了。某且请教高将军,高将军有何高见?”
陈彦方做了十余年明府,陈彦原则于暗里协助其十余年,陈桓男自幼就耳濡目染于官场中,近年早已懂得何为察言观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何况其身后不单是拥有一个久经官场的狠角。高力士既然单独约见其,已足以表明,江采苹这事,尚有得一搏。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讨不着甜头的事儿,想必断无几人舍得费思量。
正文 第037章 独处
披着缕缕晨曦的江家庭院,沐浴于淡淡的雾霭之中,格外透着分祥和。就连隔院的丛丛梅花,仿乎亦欲提早结骨,绽放芬芳。
“阿郎怎不将其直接送回厢房,反留于己房内?”待把薛王丛扶入江仲逊床榻,采盈嘟着红唇,忍不住嘀咕出声。心下不无腹诽,这约莫小半个时辰之前,薛王丛才尚被其与江采苹藏置于东厢房中,怎生这会竟又出现在了江仲逊眼前。
话说薛王丛既然沉醉了酒,那就老实巴交的闭着眼打呼噜便是。作甚醉酒醉到这般厉害,却还到处瞎遛弯,不让人省心。采盈可是甚晓,这醉酒之人,惯常最易干的事即为酒后吐真言,也不知其和江采苹未到前,薛王丛这家伙,适才有未与江仲逊耍酒疯,胡诌些什么不该说的话没有。
“无碍。怎说亦是客,吾这边离得较近。”反观江仲逊,随手拉过榻上的褥子替薛王丛半搭于身后,倒未有异色之处。
想起先时出屋,自己本是有事。江仲逊整整衣身,转而取过汗巾擦拭了下手。遂慈和的对向江采苹与采盈续道:“苹儿,阿耶且去开院门。这儿暂且就交由你同采盈照看下。只需少时,阿耶便会回来。届时,你再带采盈离去吧。”
“啊?那照阿郎之意说来,岂不是又要伺候薛、某人?”闻江仲逊吩嘱,江采苹立于旁尚未吱应,采盈已然异议道。弯着食指戳挠躺于卧榻方向的薛王丛,小脸一百个不愿意样儿。
“阿耶姑且放心去就是。”生怕采盈乍一犯激动,再没脑子的把前时在东厢房之事抖漏出嘴,江采苹暗里轻拽下意欲呶呶不息的采盈,忙上前作应道,“儿自会守于这,待阿耶返房来。”
被江采苹由背后里一拉,采盈微愣之余,亦立刻领悟到江采苹暗示。复面冲江仲逊,当即改口:“小娘子言之有理,阿郎速去速回便好。奴定会于阿郎房,陪小娘子一块等阿郎回。”
“嗯。”江仲逊见状,并未多加言语,只就似有所思的点点头,随就转身作备迈向门扇。
“阿耶且慢。”
“苹儿尚有何事?”冷不防闻江采苹唤,江仲逊脚底顿滞。
“也无甚事。早起时候,儿与采盈闲来无事,便去庖屋熬了几碗醒酒汤。阿耶先行喝碗,再去开门亦不迟。”说着,江采苹便由搁置于案的托盘上,端了碗汤递予江仲逊。
“对哦。小娘子不提,奴均忘却了。”眨眨杏眼,采盈亦像极记起何般,杵于边上对江仲逊颇显认真地附和道,“阿郎快些喝碗吧。这两碗醒酒汤,可没少耗料耗时。奴可谓煞费苦心,才按照小娘子口述的熬制法,三番五次实验,方终于熬成的。不信阿郎闻闻,为了熬这汤,连奴身上均被熏得满是烟味。”
前刻于院落中时,托盘原是端于采盈之手。因于须帮江仲逊搀扶薛王丛进房,江采苹才接过了采盈手中的托盘,待步入房,搁于案的。
江仲逊闻江采苹和采盈所叙,原本静沉的脸上则有了笑意。其实,刚才其也有留意到这个托盘,只不过压根未多想而已。只当是江采苹与采盈一大清早为今儿个的早饭准备的汤物。
“单论色泽,看似确与吾往日所熬之汤略为不同。”做了半辈子的儒医,对于凡入口之物,江仲逊早已习惯性先观后嗅。宛似为人瞧病般,望闻问切。
“阿郎可要仔细喝。奴亲睹见,小娘子有往汤里加小酸果。”睨瞥江仲逊端于手的那碗醒酒汤,采盈撇撇嘴,禁不住插言。言罢还冲江采苹吐了吐舌头,好似有意存心制造热闹。
“用得着你多嘴?吃哪门子味?”嗔责毕,江采苹没好气地白眼采盈,却也未与之计较。
江采苹自是心知肚明,采盈口中所提的小酸果,亦即而今的小番茄罢了。只是,早在千年以前,这种野生浆果却是被俗称为“狼桃”,仅用作观赏,并无人敢食。皆因,民巷有传,狼桃有毒,吃食者会起疙瘩长瘤子。
为替狼桃正名,江采苹也曾敢为天下先,以身试“毒”。当着采盈面,亲口尝食犹如毒蘑鲜红的狼桃。可恨的是,无论江采苹如何证实,之于采盈而言,依是一根筋的认定此物乃毒物,既碰不得,更食不得。不光如此,眼见江采苹见日摘食狼桃,甚至堪比晨昏定省,就差将其列入家常便饭摆上桌逼人同食,采盈反倒砸巴砸巴嘴巴,一口咬定这是祸于江采苹中毒过深,已然变得百毒不侵缘故。殊不知,小酸果之汁,实乃现成的解酒令佳品。
看着江仲逊丝毫未含糊,即把碗里的汤喝了个净光,江采苹刻意忽略掉采盈反应,莞尔笑曰:“阿耶觉得口感怎样?”
“味甘爽,酸中带清,有够醒目明神。”江仲逊全然不矫饰的陈述着品后感,便把空碗交给了眼神蛮掺怪异的采盈,“打由今儿往后,多备些,以备不时之需。”
“阿郎该不是也和小娘子一样,浑然不觉间中了毒吧?”江仲逊过誉这碗汤也就作罢,反正汤中也有采盈的功劳夹在里面。然,除此之外,江仲逊余外所补充的一席后话,着实叫采盈瞠目结舌。忽闻之下,甚难不怀疑,江仲逊是否亦被江采苹传染,同样中了小酸果的毒,对这小小的酸果,连带着产生毒。瘾。
说白了,仅是一碗清汤,且稀水寡了汤的。江仲逊反楞将其美誉得神乎其神。是以,于采盈旁观来,即便真介有效,也不见得可奏效这般神速。
“少人云亦云,学人以讹传讹。”碍于江仲逊仍在场,江采苹亦不便于过重呵斥采盈。这些年来,其甚镜明,采盈这个被其从半路上捡回家的娃,不单是其待之情同姐妹,江仲逊实则亦早已将采盈视若己出。
今时今日,之所以尤为顾及江仲逊感受,江采苹不为别的,只因,其深知,自个即将面临离家、与亲分离的困境。这一走,前路漫漫,几多凶险,回乡已是遥遥无期,尚需依靠采盈代为尽孝道,陪伴于江仲逊身边,让其可以安度晚年,而不至于老来难,无复泪,无复味。
“稍时,倘贵客醒了,也端碗给其解解酒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