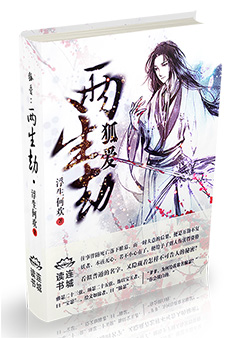梦在大唐爱-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当这一脚踩下去,其实善轩亦不无懊悔。尤其当其亲睹见,善铬促无防备之下,看似极为吃痛般咬牙倒吸了口凉气时分,善轩更觉心虚与不忍。无论怎样,其与善铬,乃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且不论入宫沦为阉人以后,在这宫里事事处处患难与共,即便在幼学之年,尚未被那恶人花言巧语拐骗卖进宫之前,两人沿街遍地过讨乞的日子时,纵然再吃了上顿不知几时才有下顿,时至而今,善轩实则依未忘却,每当有心人施舍了铜钱或是残羹,哪怕只有个凉馍,善铬也往往是忍饥挨饿先哄其吃一半,而后在从其狼吞虎咽吃剩下的那一半上头撕下四分之一来,细嚼慢咽下肚。
至于那剩余下来的一半的四分之三,则是由善铬暂且小心的包裹起来,姑且留待几天几宿实在也乞施不着东西时,再行从怀中取出来充饥抗寒。善轩记忆犹新,即使是在路边捡了个早就变馊的“黑”馍,善铬亦从不例外的如是处理之,更别提倘是幸获它物。
“此事,本即为大王与采盈间的私事。吾与你身为下仆,为大王排忧解难,是为分内之事,至于大王作何安排,大王既未发话,即不在吾等分内。由不得吾与你妄加猜测,或非议之。”
待捱至善轩神色间倏忽平添黯然之色,善铬这才伸出左手,将善轩的鞋脚轻抬起又轻放下,径自从善轩鞋底抽出其已然被踩肿红的手指,稍时缓缓站起身,温声和色迎视向善轩,略顿。方又续道:
“这些年你与吾在宫里头跌打滚爬。旁人的大起大落,断未少见识,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如今也该看懂。宫中诸事,此起彼伏,变化多端。关乎主子的事宜,既为仆奴,封眼封耳封念。有时未尝不好。”
善铬所道之理,善轩实也镜明。只不过,自打不久前善铬被李椒点名提拔成贴身伴读之日起。善轩便开始怎看善铬怎不顺眼。实际上,如若换位思考之,这点亦情有可原。曾经是同日牵着衣角满怀希望入皇城,以为步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宫城,便再无需守着苦日子煎熬。未期,下一刻,随之接踵迎来的却是被十数人群涌而上不由分说按摁于净身房饱受阉割之痛,身体上一并挨了同一把匕刃的残害,失去这辈子生为男人最在乎的东西,又一同受教成长在内侍监直至学成手被分派来百孙院,同为李椒挑中选为近侍,当年所切身历经过的这些旧事,一一列数容易,善轩与善铬却当真吃尽苦头。
或是心结根源于此的缘故,在可谓苦尽甘来的今下,善轩才心有不甘己身不如人高,无一日不在挖空心思的琢磨,跃跃欲试意于李椒面前立功劳,从而让人对其刮目相待。换言之,倘若不是善铬当李椒的伴读,或者由他人取而代之此衔位,兴许善轩的嫉妒心理不会这般重。
善轩的这份“上劲”,善铬连同李椒自然早已了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如非鉴于此,李椒近来又岂会间或将善轩带在身旁侍候。远的不提,且说月前那次,善铬尚有把跟随李椒出宫的机会,以卑体抱恙为借由让与善轩,如若不然,李椒所带之人,理应为善铬才合宜。
善铬对此只当善轩这是在一时扭转不过弯儿,故才拗不过这股子较劲来。并且,当善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非但未与善轩斤斤计较,反是更胜从前宽和待之,惟求能及早化解开善轩心中的疙瘩,而不再偏执于此,以免久而久之积怨加深,等其从中反省过劲时,想回头是岸,却已为时晚矣。李椒之所以不以为意,面上则尽量维持现有的平衡象,皆因李隆基曾告诫过其一句真言——“安一室者安天下。”虽说世人常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但李椒却颇认同李隆基之说,并自以为是的与之共认定,一室不安,便无从谈起安天下。
如果说,那日驾车的人换做是善铬,而非善轩,想来,当日采盈横冲在街头拦截李椒马车时,不见得会闹的丑态百出,双方也不致于近乎峙局至就差没法收场地步。故,或许尚夹有采盈的个人因素搅扰在其中,每每碰到与采盈有关的事,不单是李椒倍感棘手,为之莫名闹心,显而易见,就连善铬及善轩,彼此间那已然仅存不多的默契,亦正因于这么个女子的出现,越来越渐行渐远。
譬如眼下,忖及采盈,善铬的声音更变低沉了分:“吾奉劝你,此事到此为止,别再插手为妙。吾尽言于此,今后怎生行事,全在于你一念之间。时辰已是不早,今日径顾瞎忙,早是延误了夕食时间,吾且去大王那看看,请询下是否需传食,你且留在房内好生思量下吧。”
言毕,善铬即侧转身向厢房门扇方位。
坦诚讲,善轩这时,多少也已有悔意。然,就在两人将要擦肩而过的刹那,但见善轩却又脚底瞬滞:
“你若觉得,做大王的伴读好玩,改日吾自可向大王举荐你……”
有时候,一语可以惊醒梦中人,反之,多余的一句话,亦可伤人于无形。
正如善铬末了这多余的一句话,且不管其说这话的初衷是何,却已刺伤到善轩。且,字字狠刺在善轩心窝上。
余光斜睨善铬背影消失在眼底,就算善轩不愿去承认,原来善铬是在为了个女人,甚至乎甘愿拿伴读的名分,来与其谈条件做交换,连其那一堆谆谆善诱之词,亦是心口不一的空话。但下意识中,善轩却已矛盾不已地生出这种自嘲到可笑的想法。难道说,长呆在这宫中,人真的会连本性均迷失,哪怕再亲的亲人间,亦逃不脱这高墙内有的“怨”咒……
至少,当善铬道完末句多余的那话后,善轩才欲幡醒错误的认识,确已由是怦然碎裂了一地。而善铬所有的口舌也已尽毁于一旦,及其最近所做出的全部想要挽和兄弟间正在日趋恶劣化关系的努力,亦于这瞬间,统统白费掉。
正文 第090章 以静制动
这人都不咯念叨。
且说采盈,熊人般从百孙院牛哼哼闯出来之后,待回头看看,四下并无谁人追出门时,心下不无窃喜之余,立时就撒腿开跑,直至一口气径自奔出老远,这才上气不接下气的刹住脚步,扶着竖立于宫道旁花圃中间的一块石头暂歇口气。
这一道狂奔下来,采盈的身后,压根就无半个人影追赶其。可采盈那副紧张兮兮架势,让人看着,楞是像有条饿狼正绷直着尾巴,同样呼哧哧累的呲牙咧嘴,却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在步步挥跳着利爪,不啃咬到采盈一块肉誓不罢休一样。
反观采盈,现下时分,却是无暇理睬旁人的指手画脚,只在心底寥寥自我宽慰了几句。正所谓“不知者不怪”,那些不知情的宫人,又岂能理解此时此刻其由狼窝里全身而退的那种心情,那可是九死一生……
顾不及暗生喟叹,采盈稍作停歇过后,未敢多加磨蹭,即刻又行色匆匆的拔腿继续向前疾走。时下,天色早已擦黑。之于采盈而言,先时可得以从李椒主仆三人那里“杀”出条血路来,纵然是件不易的好事,甚至值得举杯欢庆番,可惜这会儿工夫,其真正担忧的尚是江采苹。
倘非挂系江采苹安危,生怕江采苹那道号的路痴,在这到处两眼摸黑的宫中找不到回家的路,采盈岂会如此沉稳不住性子,又何须绞尽脑汁急于从百孙院及早脱身。十数年的感情摆在那,这十数年如一日的朝夕相处,采盈已对江采苹太过了解。换言之,这些年以来,自幼而今,毫不含糊的说。采盈对江采苹的了解比对其自个的了解,尚是更深三分。故,采盈也知,江采苹不是其。
江采苹纵有江采苹的大智慧,采盈则有其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别看采盈净可从百孙院走回翠华西阁去,即便是这整座皇宫,只需在其间晃上一遭儿,采盈也即可摸个路熟。但若换做是江采苹。却不见得亦能如采盈这般,轻而易举就可寻返西阁。
“阿嚏~阿嚏,阿嚏~”
既躁了吧唧又洋洋自得时刻,不晓得是迫于时下这时节,已然是深冬之时,且。当下又恰值夜幕降临的晚间,亦或是因于旁的其它关系,采盈蓦地竟接连打了仨喷嚏。
常年道。一个喷嚏有人想,两个喷嚏有人骂。揉揉差点连鼻涕牛牛均一下子哈啾入喉的鼻头,采盈不由悻悻。一时之间颇解不通,适才其这串喷嚏打的,究竟是有人在想其,还是代表,哪个臭不要脸的小人正在背地里对其下咒。倘若是前者。那这个思之念之之人,肯定为江采苹自然错不了,至于后种可能性,采盈自是亦心知肚明,躲在阴暗角旮旯里冲其使坏的人,除了百孙院的那几个小鸡肚肠的小男人之外,想必也不会是其他人。毕竟,采盈自认,在这宫中,目前其人缘还算不赖,始自混入宫门,迄今为止,尚未得罪过几个宫里头的真君子假小人。
“胡思乱想那般多作甚?又不是天上的神地上的仙,让人供着烧香拜佛的主儿。奴快些寻小娘子为妙……”片刻纠结,采盈掐断自己的神经叨叨,脚底的步调也随之越走越急切起来。
与其庸人自扰,反不如专心找寻江采苹。眼下,对于采盈来说,找见江采苹才是为最最紧要的首要事儿。
正当采盈边思忖,边迈开大步朝前走时,刚走出没几步远,却又犯开犹豫,踌躇不前。采盈的右前方,有两条交叉的石子路,一条乃是通往翠华西阁的路径,至于另一条,则可曲折延伸向那片梅花林方向,这两条路于此处虽有相交点,然而同时,亦为两条岔道,若两者择其一,再行抵达另一条时,必然须环绕着宫道兜个大圈子才能衔接上,可谓恰巧相悖而行。
也是到了这刻,采盈方忽而模棱两可,不晓得到底该选哪条路往前行。之前,其是在梅林被善轩和善铬二人劫去百孙院,照理讲,理应选向左开的这条路,但按时辰掐算,从其被劫到这时,前后已是相隔近两个时辰之久,两个时辰,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或许,江采苹早已独自返回西阁,也许,就算江采苹尚未回阁,亦极有可能早就不在那片梅林干等,这种种假设皆不可排除。
故而,采盈望着眼前的岔路口,这才心生徘徊。因为,时间不等人,一旦选错道儿,势必将耽搁不少的时辰,如此一来,白白浪费时间倒在其次,采盈只恐,会因此错失过寻人的最佳时间……
——————————————
戌时,翠华西阁。
云儿与月儿将摆盛于食案上的饭菜逐一收拾出屋后,二人即同彩儿一块侍立在阁内,以便于随时听候江采苹唤遣。
“唉~”
良久,但闻彩儿长叹息了声时,云儿及月儿暗对望眼,可也俱并未吱音搭话。
见自个唉声叹气了好半晌,竟然也无人应和只字片语,彩儿终是憋忍不住满腹的闷气,索性开口发泄道:“唉,起先足足忙活了半个多时辰,谁想,这都已快过去一个时辰,却连口热乎的饭菜亦未吃上口,甚事嘛这是!你说无端端的,采盈那贱婢究是去了哪儿了,这遛弯儿也该有个时辰限度吧?莫不是在玩失踪?”
听着彩儿的怨尤,月儿低着头瞅瞥仍在保持缄默的云儿,两弯月牙儿般的眸子闪烁了下,睨望了瞥西阁里间,这才看似唯诺的细声细语接话道:“莫道人坏话了,不然,岂不是在造口业?再者说,小娘子还在里头呢,躺下是早躺下,睡未睡却不知……”
“小娘子未睡,那又如何?还不让人说道了?其还不是仗着小娘子宠溺,才敢这般没规矩?”反观彩儿,当即翻白眼道,“实话跟你讲吧,吾见其头一眼,就不怎喜欢这人。人长的本就丑。见天里,却还穿的不男不女,唉!反正吾是真想不明白,小娘子以前怎生能让这样的一个人,伺候到现在。倘换做是吾,不被其侍候成个病秧子,必定也会被其气的少活几年!”
貌似月儿愈往下压,彩儿反倒愈怨气高涨。一派非但未会意到月儿的提示。反而越抒越觉窝囊的样子。这下,月儿见状,复又忙出声相劝了句:“别再说了。背后讲论人不是,不好……”
“怕甚?吾只不过是在实话实说,就事论事罢了,有何不可说。说不的之理?”不屑地撇撇嘴,彩儿遂冷哼道,“吾倒要拭目以待。待其回来,此次怎地自圆其说,向小娘子作何交代。吾偏就不信这邪了。看小娘子往后里还如旧惯着其不!”
看着彩儿的凶蛮相,仿乎与其口中的那人,有着深仇大恨,月儿情不自禁打了个寒噤,欲言又止:“这又是何苦?吾等同为宫婢。本该相濡以沫,与人为善才是。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彩儿眼里,月儿一贯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卑怯又懦弱,却从不曾知,原来月儿尚是个善类,竟也有如是有主见的一面:“呦,还别说,吾今儿个才发现,月儿倒是个慈悯心肠啊!”
对视见彩儿嘴角勾起的那抹嘲弄,月儿小脸顿赧然,无以作应之际,但见云儿从旁正色插接道:“有人来了。”
云儿的听察力例来灵敏,突闻云儿这响儿提醒,彩儿以及月儿于是不约而同暂止嘴仗。果不其然,云儿话音才落地,阁门口处亦已“蹬蹬蹬~”急奔进道人影来。
待仨人细一看,来人倒非他人,正是采盈时,只见彩儿即刻就率然冲上前去:
“你这人,怎回事?几时了,还知回来呀?作甚去了,弄至这般晚,难不懂的,吾等尚需为你一人留门?怎地连一点规矩也不懂呢,这儿是皇宫,非是鸡三狗四的烂糟地儿,家有家法,宫有宫规,懂不?”
采盈前脚尖才跨过西阁门槛,后脚跟尚未跟着迈入阁门着地,当头即遭彩儿啐了一长通,登时不无晕乎,懵怔住身姿。
见状不妙,月儿忙不迭跟上前,压低着嗓音轻扯了扯彩儿衣角:“姑且作罢吧,小娘子才上榻,切莫扰了小娘子休憩为是。”
闻月儿所言,彩儿尚未来得及应语,却听采盈已然抢先问道:“小娘子回来西阁了?”
采盈这一问,不止是把月儿给问的明显有点愣神,彩儿的脸色,刹那间亦变得更臭:“你还知关询下小娘子是否已回来,早作甚了?小娘子若是等着你来关心,黄瓜菜早是搁凉透!”
彩儿的火药味过重,以致月儿站在边上,楞是插不上空隙说话。既然阻不了彩儿的火爆,月儿只好及时朝采盈暗示性的点点头,继而又摇摇头,示意采盈暂且不要与彩儿计较口舌上的一时之快,退一步为益。
纵使采盈被彩儿吼得一头雾水,但当其捕捉见月儿的眼神时,心下则不免又惊又喜,当场就抬腿欲走去江采苹的卧房。却未期,竟再度遭彩儿拦截在身前,硬挡住去路。
再一再二不再三。对于彩儿的胡搅蛮缠,这次,采盈当然再难权作视而未见听而未闻:“问奴作甚,奴却想有教下你,你意欲作甚?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对人责斥,凭甚?奴可有得罪于你?莫名其妙……闹够的话,劳烦你快些闪开,好狗不挡道,奴全无这兴致听你瞎咧咧!”
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可是眼下,彩儿的蛮不让步,与采盈的忍无可忍,华丽丽交锋到一起,却是几近濒临掐架的田地。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一直旁观在侧未发言表态的云儿,立在阁内较为靠里的地方,兀自不徐不缓地笑脸迎向江采苹卧榻所置的西阁里间,随即就听其请示道:
“小娘子醒了?奴扶小娘子起身稍坐会儿可好?”
正文 第091章 情缘根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