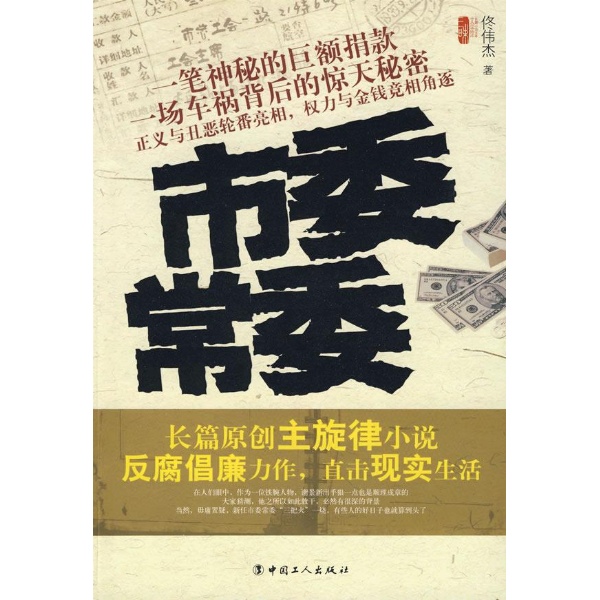市委书记的两规日子-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赞之问:“是不是布维鹰他有问题?”
石梓说:“布维鹰有没有问题现在我先不下结论,但他这个人太主观,在他的范围内你只能听他的,不论他是错还是对。”
石梓走后,杜赞之陷人沉思,他觉得石梓的分析不无道理。但这事一旦真的弄起来,麻烦将有多大!
晚上,石梓自己叫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街上兜一圈后突然停在盘家的门口。盘家大门紧闭。石梓敲了半天门,才有一扇玻璃窗轻轻地打开一点,一个男人探出半边脑袋问:“谁?”
石梓说:“我是石梓,我找盘伯。”
男人开了门,是盘小琳的父亲,石梓向他点点头,便跟着进去了。
阴暗的屋里坐了好几个人,见石梓进来,打一下招呼就出去了,只剩下盘小琳父母亲。石摔到供电公司去时曾见过盘小琳的父亲,盘小琳的父亲这时也记起来,忙说:“你是石市长。”
石梓知道不宜在这里久呆,便说:“这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盘父说:“不要紧的,家里没有其他人了。”
石梓说:“你女儿出事,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盘父说:“我不明白,她母亲也不明白,她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
“她回家里来有过反常现象吗?”石梓问。
“她不在家里住,单位里有一套房子,回来倒是常回来,但出事那几天都没有回来过。”盘父说。
石梓问:“你们清理她的遗物时有没有发现跟出事有关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盘父说,”她自己事前清理过了,什么都处理完了。“
“她有没有谈过男朋友!”石梓问。
“好像还没有。”盘父说,“她不喜欢到外面去玩,也不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
“她有手机呼机电话之类吗!”石梓间。
盘父说:“手机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呼机,有电话。”
石梓说:“给我她的电话号码和呼机号码。”
盘父说:“呼机号码我不知道,我没有呼过她,她母亲记得。”
盘母给了电话和呼机号码,石梓都记了。
“呼机呢?还在吗?”石梓问。
盘母说:“我们清理她的东西时没有发现她的呼机,估计事前她自己已经处理了。电话也不见了。”
石梓叹口气,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像个特工人员。“她是有准备的,出事前肯定有反常的迹象,只是你们不注意罢了。”他说。
“要说迹象也不是没有,出事前几天她给家里打了电话,是我接的,她只是随便问家里的情况,然后就挂电话了。”盘母说,“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说她是发神经还是怎么的,打电话回来又没有什么事,平时她可不是这样的。”
石梓问:“她生前跟谁一起玩比较多?”
盘母说:“我也不大清楚。我知道她很少跟人家出去玩。”
石梓:“现在情况很复杂,你们不要说我到过这里来,你们也不要跟任何人再提这件事,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推不知道行了。”
盘父说:“她出事后,董局长来过,也问了一些情况,他来第二次回去没几天就出事了。”
第二天,石梓去了一趟电信局,让电信局长秘密为他查盘小琳的呼机和电话,看谁跟她联系得多,什么时候联系。当结果递到石梓手上时,石梓吓了一跳,不论是呼机还是电话,都是跟市政府的一个领导联系得多。从电信局局长室下来,石梓的手一直打颤,他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将他所掌握的这一重大线索提供给谁。情况准确不准确呢?这电话呼机能不能说明问题?跟杜赞之说行不行?杜赞之处理得了吗?但不找杜赞之又能找谁呢?
三轮车将石梓送到家门口,石梓还怔怔地坐着,车夫问:“是这里吧!”
石梓下了车,后来又想叫回车夫,他考虑着是否马上去找杜赞之,但三轮车已走远了。石梓刚开了门,又折回头开信箱,几天不取信件,里面已经塞满了。他抱着一大叠报纸信件到二楼。大姐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姐说,她多次给他打电话,总没有接,是不是很忙?大姐说希望他快些出去,父母都很想念他,还是那个意思,继续读书可以到姐夫的公司也可以,姐夫会对他好的。看完大姐的信,石梓就想到身在异乡的父母,想想在汉州的种种事,他真想一走了之,必要时就动员宋白跟他一起走算了,他相信宋白会同意跟他一起出国的。他胡乱地翻着报纸,突然一个打印着他名字的封信露出来。那是一封恐吓信,内容也是打印的:多管闲事,后果自负。他有点气愤,他最看不起的是恐吓。
下午2 点,他突然记起有个会,忙呼司机。他想,等开过会之后再找杜赞之说他的重大发现,他收到恐吓信的事也要跟杜赞之说。散会后,他马上找杜赞之,但一直找不到。他问容棋,容棋说,社书记不在汉州,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找他吧。
第三十九章
“请你谈谈任在娜的情况,这次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回答我。”吕国标说。
“我这个人历来是实事求是的。”杜赞之说,看来这家伙非要在任在娜身上找缺口了,“关于任在娜的情况,我说过多次了。”
‘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了。“吕国标说,还是一副不容分辩的样子,”你是否认识任在娜?“
“认识,任在娜是市文化局副局长。”杜赞之说。
“你哪一年认识她!”吕国标问。
杜赞之想了想,说:“几年前就认识她了。”
“哪一年?”吕国标间。
“记不清了。”
‘怎么认识的?“
间那么具体干什么呢?“她当时是市歌舞团的演员。”杜赞之说,“她在市里演出,我去看,这样就认识了。”他觉得,这样说不会露什么马脚。
吕国标问:“歌舞团有多少人,你总共认得几个?”
杜赞之心有点慌,歌舞团他就认得任在娜。他想,这家伙提问题又换了一种方式,正步步逼紧。“任在娜跟其他演员不同,她是主要歌唱演员,文化局长宣传部长都很赏识她。”杜赞之说。
‘你认识她后为她办过什么事?“吕国标问。
“没有。”杜赞之说。
“是真的没有吗?”吕国标睁着眼睛看看杜赞之,杜赞之感到吕国标的眼睛里有束冷嗖嗖的光。
“真是没有。”杜赞之说。
吕国标问:“任在虎是她的什么人,你知道吗?”
杜赞之给问住了,他如果说认识任在虎,跟着下来又要回答什么问题呢,但如果说不认识,人家信不信?
吕国标望着杜赞之等待他回答。
“任在虎,任在娜,一听就知道是兄妹或者是姐弟关系。”杜赞之说。
“任在虎被分配到乡镇农业站,一直不报到上班,后来突然谁给安排到工商局?你知道吧?”吕国标问。
“不知道。”杜赞之决然地说。
“这个,我看就不是事实了。”吕国标说,没有再就这个问题问下去,也许他们已经落实的东西就不一定要他承认,到时就扣他顶“不老实”的帽子。
杜赞之有点担心,他犹豫着是不是说明一下有关任在虎工作方面的事。
“任在虎参与黑社会活动被派出所抓起来,是谁出面让放的?”吕国标面无表情,机械地问。
杜赞之想,任在虎并非因为参与黑社会被抓,吕国标你情况并不比我清楚。但这个问题毕竟也让他担心,他身上冒汗了,背部有点凉,为了不让吕国标注意到,他故意掩饰着笑起来说:“吕主任你的问题可真多,但我相信在我这里你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
吕国标沉默着望向杜赞之,杜赞之加速的心跳迟迟没有平稳下来,他突然产生一种预感,说不定问题就出在任在娜身上,谁说过,100 个腐败的男人中,有80个是因为女人,有15个因为钱,剩下5 个是糊涂蛋,难道他真是栽在女人身上了吗?“那你就说说吧。”吕国标说。
杜赞之瞬间找到了感觉,他一下子镇定下来。“这些事可以不说的吗?关于女人的事,如果跟自己没有什么瓜葛,我不想说。”他说。
吕国标冷笑一声:“一起从汉南出发飞首都,又一起从北海飞回来,这算不算瓜葛?”
杜赞之感觉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和任在娜的关系。但很快,他脑子里一个闪念,道理又有了。“两个人同机也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有这样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探讨一下,我们平时看见一对男女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我们可以说,他们也许是夫妻、恋人,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关系,但如果在公共汽车上,一男一女挤最近也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有什么,说到任在娜,同机到首都的有多少人,同机从北海回来的又有多少人,这能说明什么呢?”话虽这么说,但杜赞之毕竟心虚,他担心他们的住宿登记会落到人家的手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完了,许多领导的问题往往都在情人这个环节上被打开缺口。
“我跟她没有过超出同志间关系的事。”杜赞之说。他想,有关任在娜的事,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他们确实已经掌握了比较确切的证据,但可能性很小,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给别人抓到,即使任在娜自己说出来,他不认,案也定不下;二是他们接到举报,而这种举报多是捕风捉影,对调查最多只能提供线索,也许在飞机上碰巧有谁认识他和任在娜,但两次都同机,也实在太巧了,是不是谁查了那两趟飞机的乘客名单?
“你去广州检查身体,去的是哪间医院?”吕国标问。
杜赞之简直被当头一击,他没有想到这老家伙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他根本没有去广州,广州有几间医院他也不知道,不说肯定不行,说了就露马脚了。
吕国标望着杜赞之,脸上没有透露可供参考的信息。
“我去检查全部是朋友安排的。”杜赞之说,“说了你可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间医院。”
“将你知道的说一说,检查什么项目,有什么结果,等等。”吕国标今天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神态。
“结果也不在我手上,我只是说哪里有什么感觉,检查后医生说没事就没事了。”杜赞之说。
吕国标突然笑起来,他说:“也许天底下就你一个这样检查身体的了。”
杜赞之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哪是检查身体,是陪任在挪去玩。他心慌了,被“两规”以来心里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慌张过。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吕国标又问。提起“朋友”二字,吕国标就气愤,朋友有时候就不够朋友,儿子的朋友居然挑动儿子回家来闹事,教唆儿子说这样的父亲还算父亲?有去教唆朋友不认自己父亲的吗?真是岂有此理!
杜赞之感到自己的脸一定变色了,他广州朋友不少,但只要一说出名字,人家马上可以去调查,然后就查无此事,他那时还能自圆其说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不回答?
“说啊,谁带你去检查身体!”吕国标脸上又有了表情,那是一种嘲弄别人或者等着看好戏的表情,但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得意。
“这个,这个……”杜赞之口吃起来,“这个跟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调查我的问题,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不在调查之列吧!”
“我们也不想调查那么多,但你说去广州检查身体,我们没有这样认为,就有必要核实一下了。”
“如果不说不违反什么规定,我想还是不说的好,以免给朋友增加麻烦。”杜赞之说。
“你是市委书记,离开工作岗位近10天,你离开岗位的理由是检查身体,现在组织让你提供检查身体的有关资料,你有这个义务吧?”
“我当初想不到组织会查这个事情,没有留下资料,这点请组织谅解。”杜赞之说。
第四十章
董为一案闹得整个汉州市沸沸扬扬,抱不平的人还给杜赞之打匿名电话,不但打到家里打到办公室,还打进他的手机,说董为死得不明不白,说汉州有天没有太阳,杜赞之感到烦躁,有时甚至感到气愤,什么事都找市委书记!他连续几天休息不好。这天下午,杜赞之给任在挪打了个电话,说晚上要到她那里去。
任在娜很喜欢汉南海边那幢别墅,住进去后请了个保姆侍候她。她接到杜赞之的电话时,也在汉州上班,她马上给保姆打电话,让保姆炖汤。
7 点钟时,杜赞之的小车驶进别墅的后停车坪,任在娜已等在门口。
一个小时以前,任在娜给了保姆200 块钱,让保姆出去玩,今晚可以不回来住了。这是习惯,每次杜赞之要到这里来,她都让保姆出去玩,她要自己侍候杜赞之,和杜赞之单独在一起。杜赞之刚推门进屋,任在挪就轻声对他说:“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杜赞之苦苦一笑说:“因为董为案件的事,这段时间哪里安宁过?”任在娜说:“今晚给你炖了个好汤,让你补补吧。另外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菜,你猜是什么?”杜赞之说:“肉包两个,肉饼一个,还有……”任在娜将他的嘴巴堵住说:“你们男人真是坏!”杜赞之说:“我们也有好几天不在一起了。”任在娜说:“一个星期,也不算长,就像出趟差。”
杜赞之进到房间,顺手将门合上就忍不住抱着任在娜亲。任在娜用她那种半主动半被动的方式配合着,当她嘴有了空闲的机会,她说:“你总像个馋猫。”
“谁叫你总像刚出水的鲜鱼!”杜赞之说。他一边亲着她一边摸她。当他将她抱起来要放到地毯上时,她说:“你肚子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杜赞之说:”肚子不算得饿,其他地方倒饿了。反正先支出然后再收人总比先收人再支出好。“迫不及待地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就将她身上的衣服全部剥干净了。他们从走道开始,一点一点地移至房间,又从地毯上移至床上,再从床上下来移至卫生间,一个小时下来,他们双双泡进浴池里,让温水帮他们慢慢恢复体力。
“你的脸色红润起来了。”任在娜深情地凝视着杜赞之说,用手为杜赞之擦身子。
杜赞之说:“古人讲究阴阳平衡,取阴补阳,取阳补阴,很有道理,为什么一些老处女未老先衰,而一些风流女郎却能青春常驻,也是这个道理。”
汤是金钱龟炖吹风蛇,他们从浴池出来便喝汤吃饭,令杜赞之意外的是居然有一盘鸡屁股。杜赞之看看鸡屁股,就望着任在娜笑。
“男人没有几个不虚伪,明明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又不好意思。”任在娜说。
“当初吃你是最不好意思了,但还不是一样吃了!”杜赞之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东西?”
任在娜说:“我还知道你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杜赞之说:“就你一个,真的。”
他们吃过饭后就相拥着看电视,先胡乱看一些新闻电视剧之类,将近11点钟,杜赞之让任在娜换上影碟,开始放艳情片,很快,他们进入今晚的第二次阴阳互补。任在娜担。心壮赞之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杜赞之说:“小别胜新婚,新婚之夜还是顺其自然吧。”
杜赞之玩着任在娜的时候,任在挪突然问起她母亲那个亲戚的事怎么样了。杜赞之放慢了动作问:“是不是一个开口就要操人家娘的女人?”
任在挪说:“她病过后一直讲不了话,只会说一句粗口。”
杜赞之就跟她说故事。那天,将近下班的时候走道里来了几个人,吵吵闹闹的,其中一个女人声音像哑巴,叽哩咕嗜不知嚷着什么。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