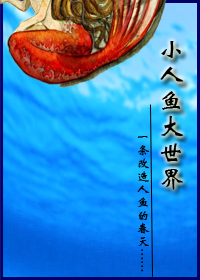第二世-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
“——但是3P什么的,不太合适吧?”
他不言语,单是拍了拍身侧的沙发,示意我过去坐。
本来我想,找个艳男来跳钢管舞似乎有点俗气,不太符合秦曙光的品味,但我又有一丝怀疑,十来年的时间,黄光裕都能从借壳上市走到锒铛入狱,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都能从强盛走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退一万步讲,市委领导班子都换了两套了,凭什么人秦曙光就不能从一个高风亮节的高知走到一个社会人都会经历的消磨时光?
想到这里,果然门外传来了青涩的敲门声——擦,我是怎么听出青涩来的——外加稚嫩的声音:“秦先生,可以进来吗?”
好吧,稚嫩也是我脑补的。
“嗯,进来。”秦曙光的声音听起来很享受,这是提前进入状态了。
灯光打得有些暗,我不太能瞧仔细来人样貌的细节,只看到了个大概:身材修长个头高挑,清爽的短发,典型的学生扮相,而他背上的小提琴则暗示了他可能还是个艺校的学生。
“秦先生,还是那支曲子吗?”他的态度像阿庆嫂一般不卑又不吭,衬托得我之前的妄加揣测倒显得不阴又不阳,十足小人。
“嗯。”秦曙光脸上显露几分倦色,我认为是刚吃过饭大脑缺氧所致?他倚在沙发上,指尖夹着烟却不点燃,就那么望着面前的少年,陷入了沉思。
少年从琴盒里拿出弓,擦松香的声音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而琴弓刚触到琴弦发出第一个音的时候,我更是差点忍不住跳起来。
门德尔松的E小协是一首欢快的曲子,甚至用青春洋溢来形容都不为过,我曾想将它选作高考特招生考试的曲目。它代表了那时候我全部的人生状态,音乐上追求精美华丽正暗示了精神上崇尚浪漫主义,对未来的憧憬对爱情的渴望消耗着我短暂的青春,最后也酿造了中年的枯槁委顿,徘徊在现实的边缘,直到如今依旧是无所善终。
而秦曙光却无可自拔地陷入这种憧憬当中,虽然他知道没有解,却仍然试图让自己相信并且依赖于这残存的、曾经有过的希望之光。
华彩响起,第一乐章已经接近尾声时,他彻底地沉浸在了乐曲之中,他的神态是放松而悠闲的,他的眼神是充满希望的,他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他的感情是有所寄托的,他凝视着面前拉琴的少年,就像在注视当年的我。
尽管那个少年,没有哪一处是和我相像的。
他一遍一遍地要求少年重复着这支三十分钟的曲子,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于是我在刹那间明白了很多事情。
可能曙光的心理的确是有问题了,他或许已经不记得我的样貌,只是沉溺于这一种怀念与感激并存的情绪里,想将一切扭回最原始的状态。
他想摆脱这一切,却挣不开那种亏欠的折磨,漫长的时间罅隙里,他早已将这一切视作最后的希望,支撑他生活的希望。
他或许本身不单纯却单纯地以为,只要在心里没有放弃对我的爱,这一切就能周而复始地走下去,哪怕我们并不在一起。
时间在消磨某一种情感的同时,相应的,也会扩大另一种,比如消磨了爱扩大了恨,消磨了希望扩大了绝望,消磨了享受扩大了亏欠,久而久之便是一个无法预知和掌控的状态。
前几天在南京见到杨浅的父亲,我其实有所顾虑,我害怕最终会将这副躯体交还给杨浅从而导致自己真正的死亡,因此才迟迟没有做出反应,而如今明白了一切,却矫情地意识到只有真正的消失才能还给秦曙光他应当有的生活。
我叫停了少年,乐曲声戛然而止在了结束部的那一声颤音之上,突然的安静使得整个包间的气氛显得十分诡异。
“换一首拉拉,这首听烦了。”我说。
他疑惑地看向秦曙光,后者则默许地点点头,意思是随我。
“吉普赛之歌会不会?”我问道。
“会,大一就在学校音乐厅独奏过。”他的回答也不含糊。
我于是抬了抬手掌:“那就来吧。”
萨拉萨蒂是个奇人,不但拉得一手好琴,还能自己作曲,最可怕的是他还能唱花腔,这种多才多艺是多么的令人羡慕嫉妒恨哪!他拉琴有个特点,就是天生速度惊人,一般人不敢跟他搞竞速赛,因此他搞出来的曲子也非常折磨人,没想到这位小帅哥技艺过人,谱架都不用支,就已经拉得神采飞扬恍如帕格尼尼转世。
对于将秦曙光的往昔悼念会转变成一场艺校学生个人炫技会,我表示十分满意,否则万一他要念出几句明媚忧伤的悼词以悼念我们逝去的青春,我隔夜饭就没消化的机会了,况且我自己都已经明媚忧伤了很久了。
时光飞逝,烟雾缭绕,我觉得这时候有警察同志路过一定会高兴地发现本省缉毒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他妈根本就是一出聚众吸毒。
抽了太多烟,我有些头疼,最后也不记得是怎么回的房间,直到第二天的阳光射过窗帘的罅隙,射在了我稚嫩又沧桑的脸庞上,我才开始计划寻找那只失落已经的琉璃盏,还有琉璃盏里杨浅失落已经的灵魂。
第三十一章
说到琉璃盏,其实我也没什么太细致的眉目,怎么找,从哪开始找,说白了还得问问淮远的意见。
然而我跟曙光和好不过三天,且距离我同淮远最近的一次床第之欢也不过才去了四天,这个时候去找淮远,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但合不合适还没来得及从我嘴里说出来,曙光先一步有了行动,反锁的门,没有窗户的房间,这一切似乎在告诉我,老子被非法拘禁了?
尤其是在我摸了口袋发现手机也被拿走了之后?
一个刑辩律师,置堂堂刑法典于不顾,在知法犯法的道路上越奔越远,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难道说,他费尽心思换车换家就是为了唱一出铜雀春深锁二乔?
好吧,我又脑补了。
白天略显漫长,于是我准备了一天的台词,到了晚上见到他的时候便熟练地脱口而出:“你锁得住老子的人,锁不住老子的心!”
曙光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坐在窗台边的沙发上抽烟。
他越是沉默,形势就越是倒不向我。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一个女的深爱着一个男的,结果那男的不守妇道,跟别的女人有了许多许多的小秘密,这个女的爱到深处李时珍,把这男的手脚都剁了当植物养在家里,每天浇浇水再顺便光合一下,成功完成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高难度转换,诺贝尔正在不远处向她招手。
“你不会是想把我种了吧?”我打了个寒战,“难度太高了,你又不是学生化的,何必呢?”
他不说话,从手里的袋子掏出便当盒:“介于你暂时还没学会光合作用,还是先用吃的吧。”
我看向他,严肃地说:“曙光,别开玩笑,你怎么了?”
他轻松地回答:“玩笑是你先开的,问我怎么了?”
“你关了我一天,没有任何的理由和解释。”我有点不耐烦,“还拿走我的电话——曙光,即使我们现在是恋人,但不代表我要完全服从于你,甚至当非法拘禁发生的时候。”
大片大片的沉默扑面而来——我沉默是在等他的回答,而他沉默大概是因为不想回答。
灯下有几只飞虫在打转,时而用它们那对纳米级的翅膀扇几下白炽灯泡,发出啪的声响,异常使人烦躁。
明明已经是初冬了。
“曙光,我以为我们可以彼此信任——”我试着和他交谈,但他似乎无动于衷。
他的目光空洞而迷茫,似乎有一万个头绪,但我猜不中任何一个。
就这样,他抽了一会烟就离开了,注意力不知集中在三维空间的哪个坐标上,也可能是四维的,因为我无法用肉眼捕捉到。
这种情况第二天仍在继续,没有任何外界接触的整个白天,我被迫看了近12个小时的电视,道貌岸然架着机顶盒的数字电视竟然只能收到一个频道——本地新闻台,并且这个频道反反复复地播放着我去世那天的新闻,不厌其烦。
我突然觉得秦曙光是想用这种方法打破我的意志,使我的精神出问题,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从这两天的沟通情况看,似乎是他的精神已经出了问题,思考问题已经同我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这种猜测令我愈加恐慌,比起生命不受控制来说,我似乎更害怕精神不受控制。
第三天的中午我在观察了窗外两只黄鹂鸣翠柳之后突然意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抗争,我的机会只有秦曙光晚上来送饭的那半个小时。因此我想到了两种方案,一是把秦曙光敲晕了逃,但不知道外面会不会有人把守,二是直接拿利器要挟他,让他主动放我走。
经过长期的理论论证,我还是觉得第二种方案比较靠谱,但是上哪去找利器呢?这真是巧妇难为那啥之炊了。我环视着房间里唯一的凶器——一次性打火机,老子总不能摁着打火机对他说“放不放?放不放?不放我就烧死你!”吧?
——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而我的计划也正在无限逼近搁置,失望无望绝望纠缠着我,心情很糟糕,情绪很低落,老子从白天的斗志昂扬走向了夜晚的茫然无措。
不过皇天真他妈不辜负有心人,四处乱转的时候竟然让我从浴室的毛巾架上卸下来一根不锈钢条,来回掂量掂量,颇有点重量也。
“曙光,千万别怪我,要怪就怪招标惹的祸,装修方案节省了,质量当然也相对下降了。”我握着钢条站在门口心中默念,“敲晕就行,我不贪心的。”介于钢条算不上利器,我还是准备实施第一套方案。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从模糊投向了清晰,暗示着声音主人的逼近,虽然我也没有做好不成功就成仁的思想准备,但还是颇有些矛盾,对曙光下手,多少有点舍不得,但此刻的他又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再不下手的话,呵呵呵,我就彻底傻逼了。
钢条是空心的,我特意往里面灌了水,以增加重量和打击力度。
苍天可鉴,我这次决心确实很大啊。
钥匙插|进钥匙孔的声音清脆而诱人,门轴转动的弧度怎么看都堪称完美,一只无辜的脚已经踏了进来,我本该犹豫却又在突然间丧失了理智,血脉贲张之下默念了一句“我会带你去看心理医生的,药钱算我头上!”一棍子就敲了下去。
对方捂着后脑勺,带着无限的不解和疑惑缓缓地转了头看我,我已经可以看到血从他指缝间渗了出来。
手中的钢条因为撞击力的反作用正在我手掌之间微微震动,而我望着面前缓缓倒下的沈疏楼,眼中迅速装上了最真挚的歉意。
“草,老子是来放你的!”这句充满英雄气概的台词成了他倒下前的最后诉愿。
唉,老子谢你也是真心的!我用腹语说了这句话,留恋地看了一眼他倒在地毯上的伟岸身躯,匆匆逃向了楼道的尽头。
既然你是来救我的,我又怎么能辜负你一片好意呢?
所以我的脚步愈发轻盈和欢快起来,完全忘记去考虑那一棍子敲的力度好像有点大,老沈那身子板到底扛不扛得住。
楼道尽头是一扇窗户,我推开半扇俯身一瞧,还好,二楼而已。
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生亦何哀死亦何苦,都他妈随风去吧!念完这句,我好像得到了能量灌注,扒着窗台边沿就往外翻,克服重力爬了出去,又借助重力跳了下去,完美着陆之后我不得不说了句感谢的话:“啊,我爱你,地心引力!”
面前的君越后座摇下车窗,一张六成熟的面孔毫无表情甚至略带鄙夷地评价道:“脑子瓦特了?”
我愣了几秒,随即回应道:“一口上海腔,您这是在做准备往中央调了?”
杭其不像秦曙光和沈疏楼,年纪一把却毫无幽默感,说了句“带走”之后,那张扑克脸就渐隐于车窗之后了。
MB的这是个什么情况?市委书记玩绑架?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手腕就已经被壮士在身后扭住,依照我灵敏的第七感估计,壮士还是成双的。
一个个都他妈怎么了?不是玩非法拘禁就是玩绑架?难道说人大常委会又要修刑法了?
我被弄上了一辆君威,不远不近地跟在那辆君越后头,身旁卡着二位壮士,整个后排座拥挤不堪,我觉得如果此刻把车座卸了,那身体绝对是悬空的。
这种考虑明显是防止我有逃跑的动作,只可惜从意识到被绑架的那一刻起我就没往逃这个字儿上想过。
“二位大哥,你们看我都给卡瘦了一圈了,这手就不用绑了吧?”我试着跟他们商量。
左边那个没反应。
我又试着征服右边那个:“这位帅哥,你看你虽然穿得一身黑,但长得实在不像黑社会啊,何必做这份没有前途的职业呢?”
他目视前方无动于衷,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我都不得不在心里夸一句训练有素教导有方,这时左边那个倒是按捺不住回了一句:“我们是公务员。”
我恍然大悟,连声道歉,都是我的错,我还以为各位是在绑架我呢,要知道您们都是公务员,那我就放心了,就是死也是为国捐躯嘛——
副驾上坐的大概是他们领导,此刻十分不满,转过来做了指示:“把他嘴也给堵上,哔哔一路烦不烦?”
右边雷厉风行,当即就开始从车座底下掏胶带,我心里一紧,当即表示了良好的认错态度:“各位爷我错了,我这一闻塑胶味儿就晕车,回头吐车里了还不好清理,要不我闭嘴,胶带就免了吧?”
我一直幻想有一天自己会被绑架,因此也知道不能跟他们来硬的,顺着他们走,反而弹性比较大,但是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幼稚——这方法可能跟讲道理的流氓行得通,但却对不讲理的市委书记办事员无法起效。
“贴!”领导总是这样言简意赅。
而执行者总是喜欢再添加点自己的想法,这让人很不爽,比如你说一个演尸体的盒饭演员不好好躺尸跳起来喊两句自己写的台词,是不是就很没职业道德?
眼前的状况就是这样,领导明明只交待封口,办事的为了献殷勤,多表现,于是把老子眼睛也蒙上了,导致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眼前这一幕感人的官场新风向。
黑暗中左拐右绕的大街穿小巷,也不知道年终奖会不会多发一点。
最后车停下来的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交谈声,好像是君越上面的人下来交待我们这辆车上的领导,等十分钟再带我上去。
上去?上哪里去?
脑子里闪过几个念头,瞬时就拼接了起来——沈疏楼来放我,我被杭其绑架,杭其是老沈他姐姐沈长枫的老公也就是他姐夫。
你要说这他妈不是事先串好的剧情,老子还真就不能信!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我被推搡着弄上了楼,当即心情就不是很好。
三年前我跟踪了一个人,一路打听到了南京才知道他是在寻找一只琉璃盏,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面相不善的杭书记,当年好像还只是市委办公室主任、人大秘书长?
杭书记这样的人,如何能一路乘风破浪挺进市委领导班子,我是不大能理解的,假使我在上位,肯定不能挑这么个人,野心大胆子大,最关键的是,此人没有下限。
一个公权力的行使者思想道德上没有下限,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日益衰减的今天更是不可想象。
然而在我还没有能构思出详细的蓝图的之前,熟悉的气息荡漾于周身各个角落,不用说是被蒙着眼睛,假使是化成灰我也知道自己正身处何方。
每一层楼有多少节台阶,每一块墙壁刷的是什么颜色的墙漆,每一层的厕所是男用还是女用,我都他妈太清楚了,还有楼道尽头的水房,似乎刚烧开了水跳进保温的状态,这一刻我竟然想的是去接一瓶开水泡一杯上个月老李带回来的祁门红茶?
黑布被摘掉的那一刹那,我刚好踏进一扇门里,杭其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对我冷笑,整间屋子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