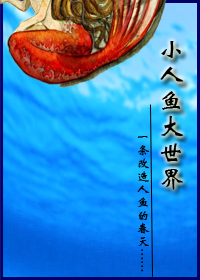第二世-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重新开始的:从手机里翻出一个室友的号码,然后约他一同吃饭,再顺理成章地一同回宿舍,熟悉并适应周围的人,渐渐步入正轨。
只是据传晚上睡觉时常常会发出古怪的哭泣声,似是被恶灵追赶,苦不得脱身。
这情况在下是知道的,只是没料到换了副躯壳,情况却没有好转,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便习惯了在白天行恶,梦中忏悔。相信我,独自入眠的黑夜里,我比任何一个同道中人都渴望脱身,甩开那挣不断的关系网,填补那永远平不完的帐,还有平反那一桩桩既得利益下的冤假错案。
不过那些源源不断排队而来的床伴,倒是很好的缓解了我这样的痛苦,因此我落下个病根,但凡一个人在家,绝不能闭眼。
我明明干着这样沥青浇铸的勾当,却比谁都痴心妄想能够洗白。
有些时候,想搭车转上一条回头路,那绝对是一票难求。就像小时候扯谎,扯完一个谎之后发现必须要用另一个谎来圆,久而久之,越走越远,你最深刻的想法便是如果一开头照实说了该多好,然而一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一条单行道,禁停禁转禁掉头。
秦曙光那张名片至今还躺在宿舍那只许久不清理的垃圾篓里,这张薄纸我一个人时揉了上百遍,揉着揉着七窍全通,我当时便振臂高呼,前世必定是个冤下诛仙台的一等大仙,今生误入歧途,玉帝实在瞧不过眼,特来助我重生,以成洗白大业。
于是我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浩瀚工程,先从人生理想说起。
我的理想,确切的说,是我替杨浅改动过的理想——惩奸除恶,扶弱锄强,还社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实际上这样决定的时候,我是存了私心的,这私心大概来源于我闭眼后的始终不死心——是不是人生轨迹不产生偏颇,就能够留在那个人身边。
是不是就可以站在他的面前,大大方方喊他一声,曙光。
第三章
我在搬出学校的同一天踏进了秦曙光的事务所,这两个动作一气呵成,占满了我整整一天的日程表。
房子实际上是我事先找好的,四楼小单居,装修简单了点,但我也不太在意,人一般都是居其位干其事,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相应的就用不着装点门面。
荤的吃多了,就想着清汤寡水。
不过想来这杨浅人缘也不是很好,搬出去的时候无人送别是一说,那围坐一团窃窃私语令人蛋疼的眼神就是另一说了。
宿舍里的东西除了书本作业其余的我都扔了,要了也没用,我认定杨小兄弟已经随着在下那躯旧壳魂归天际了,应该不至于隔天突然出现在在下床前怒指在下清理他衣物篡改他理想,就算有幸能目睹如此精彩场面,在下也会面不改色地对他说,这身子现在是我在用,你非说是你的,这让我很难办,要不你喊他一声,看看他答不答应?
流氓惯了,思路转变不过来。
躺在一米二宽的小床上睡了个午觉,跳起来一拉窗帘,今天天可真不错,挺风和日丽的,这样的天气一般适合秋决,牢里蹲了大半年的重刑犯们终于可以解脱了,而我换了身新买的衣服,出门时也是同样的心情。
赶赴刑场的心情。
民商两用小高层,七楼以下饭馆商铺健身房,七楼往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秦律师的品位一目了然。
八楼过道尽头是一扇虚掩着的铁门,门上赫然几个大字:东方律师事务所。
老子一口热血差点没喷在过道里,这已经不是品位层面上的问题了。
那扇门的虚掩处隐约透了星点的亮,而我的手正搭在门把上,迟迟用不上力,因为我当真不知道,在这扇门背后等着我的会是什么,我所自认为的重生会不会只是下一个万劫不复的开始而已。
不过这样的思想上的艰难挣扎全然完结于身后响起的声音,一刹那我的心跳略有些过速,看东西也有些不怎么分明,我定定地站着,忘记要接他的话也忘记要回头看一眼这个让我伤神伤力的秦曙光。
“来了?进去坐。”他一只手绕过我的身侧,推开了那扇搅我心绪的门,崭新的三次元覆盖了我的周身,热泪盈眶的在下十分想说,曙光你是喜欢我的对吧,否则何以连一间办公室都装修得跟我家那间两层小复式如出一辙?
但他却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抽出插在西装裤袋里的右手,走去饮水机下接了大半杯置于我面前的茶几上:“到过我这里的人,基本都要夸一夸这里的装潢。”
我接过水杯,先是坐在沙发上小口地啜,然后环顾四周,夸得真心实意:“确实不错。”
秦曙光笑了,不轻不重的一个笑,里面大概有讽刺的意味:“朋友介绍的设计师,据说替林寒川搞过装修,副检很喜欢,从此这位仁兄声名大振。”
我干笑,他讲话已经形成了套路,明褒暗贬,毒舌不减当年,只是再三于我面前损那已经过世了的倒霉鬼,究竟意欲何为?
于是我不禁脱口而出:“林寒川已经走了。”
眼神犀利扫遍我周身,曙光倚在立柜边上说:“我忘记了,副检似乎是你的……”
我当即摇头,干脆果断,不容置疑。
“不是就好。”他双眼一眯,笑里沾了安慰:“林寒川此人风流成性,且危险至极,还是不要与他扯上关系的好。”
曙光啊曙光,你叫老子说什么好?风流成性,危险至极,老子恨不能从坟里爬出来,把这两个词凿成墓志铭。
于是我放下水杯向他道:“副检身边睡过的人太多,但真正能留到第二晚的几乎没有,不过我倒听说……”
秦律师对关键词敏感,“不过”二字成功勾起了他的兴趣。
“听说什么?”
我索性实话实说,坟前那一出没唱完的接着唱:“听说他曾经有过一位恋人,年幼无知时为了此人出柜,结果落得个爹不养娘不认,秦先生,你说有没有这回事?”
秦曙光顿了两秒,终于从微笑转成大笑,先是看着我笑,而后对着立柜上那盆吊兰笑,最后倒好,拖过一张椅子坐着笑。
插句题外话,他笑起来确实好看,眉眼柔和,儒雅大方,像极了一幅水墨画,那笑意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慢慢晕开的,我喜欢看他笑。
不过绝不是眼下这个意味不明的笑。
此刻,我的太阳穴不知扯到哪根脑神经,隐隐地疼痛,不得安生。我就知道,秦曙光这人近不得,他终日与天斗与人斗与公权力斗,斗得太多心机太重。
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因此心深似海。
不过时至今日,我也没能想通,早已视我为社会毒害的秦曙光为何这十来年始终不娶不养,甚至连床伴都不曾交过一个?
我这边稍有迟疑之色,他便止了笑,极认真地与我对视:“杨浅,谣言最不可信,想做律师,就要有自己的认知,然后依据这个认知建立起属于你自身的牢不可破的逻辑体系。”
我终于回魂,想了想便问:“不问对错?”
他点头:“不问。”
我追问:“也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继续点头:“不管。”
我于是接下去问:“我记得寒川墓前,你口口声声说原要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现在怎么倒改词儿了?真相不管对错不问?”
此话一出,秦曙光脸上竟又浮上一层欣慰的笑。
我顿悟,一来一去,兄弟被他彻底套死,其结果就是我的话越来越真,而他的笑却越来越假。
只是这笑容还未冷却,西南角房间里便有人满眼血丝满嘴胡渣戳着根烟屁股走出来,路过我身边时呆滞地看了一眼,紧接着问了句:“看这位小兄弟骨骼惊奇,想必是有什么重大冤情?”
秦曙光从茶几上摸一只烟灰缸递给他:“又熬夜了?”
那人食指拇指并作一处掐了烟头,拍着秦曙光的肩语重心长道:“我说老秦啊你也悠着点儿,猥亵男青年也是能酌情定罪滴。”他一手比五一手比十,“五年上十年下,无期的例子也有……”
秦曙光毒舌,这位仁兄嘴贱,两尊佛像照得这事务所熠熠生辉。
秦曙光一仰头,朝他努嘴:“你座下两大金刚护法哪里去了?”
仁兄很是茫然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是啊,哪里去了呢?”
秦曙光于是转头向我,表情颇为无奈:“是这么个情况,我这个事务所就四个人,其中三个能办案,还有一个目前在实习,你看看,要是愿意,就留下来跟在我后面做做事。”然后又补充:“不过呢,除了我以外的那三位,基本都是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平时最好不要跟他们多讲话。”
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
秦曙光思索片刻,压低声线对我说:“因为至今我都没弄明白他们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仁兄很是惊奇,牙刷杵着牙床从大概是洗漱间的地方跳出来:“你不是不收徒弟么?”
秦曙光站起身将椅子挪回原处,一脸讳莫如深地盯着他,被盯的那位浑身不自在,换了只手捏牙刷柄:“收收收,收完这个再收俩,我再凑钱买匹马,携我那两大护法亲自送您四位去天竺行不?”
秦曙光咳了一声上楼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里同外星来客比赛眼力。
我们就这么沉默着互相对视,像江湖上两大绝顶高手的相遇,欢喜而又惆怅,孤独而又绵长。
约莫半柱香的功夫,在下赢了,因为那位仁兄实在被辣得受不了,冲进洗漱间将那满嘴的牙膏沫给吐了个干净。
出来的时候他那分裂的大脑似乎转到了正常的纬度,脸上挂着长辈般温和的笑容递来一张名片,我一眼瞟见正当中大号字体写着“沈疏楼律师”,当即为这名字折服,所于是大胆提问:“敢问您这名字是谁起的?”
仁兄抛过一个略带蔑视的眼神:“这不是我的名。”
我问那是什么,仁兄慢条斯理启唇吐气:“表字。”
于是这一刻起,沈律师骚人墨客的形象深入我心,刹那间滋生出了各种敬仰之情。
就在我感叹这地方虽小却虎踞龙盘时,秦曙光从楼上下来了,他递过一本文件夹,按着我肩膀说:“这里面是一些资料,有些是关于事务所的,有些是关于我个人的,你拿回去看看,下周一正式来报道。”说完之后大约觉得祈使句的语气太过生硬,又续上一个问句:“有问题吗?”
我抱着文件夹摇头,心里各种滋味此起彼伏。
林寒川,你与这位仁兄纠结了一世,到如今还是执迷不悟,当真是要应上那句烂大街的唱词,死了都要爱么?
第四章
曙光给的文件夹里厚厚一叠A4纸,我坐在家里耐心地翻看着,希望能在晚饭前翻出一个彩蛋来,比如限量发行的秦律师生活照什么的。
不过天色渐暗,仍不见彩蛋。
我摸摸口袋,下楼买了盒泡面,边吸溜边拜读,终于在掌灯时分读完了整本大部头。
读完之后的感觉十分不好,因为在那喜气洋洋成功案例和主要律师简介之中竟然夹杂着两宗失败的案子,秦律师在旁边御笔批注了八个大字:滥用职权,是非不辨。
这八个大字刚劲有力,力透纸背,矛头直指当今司法系统内部滋生出的腐化毒瘤。
很不幸的是,这两宗看起来板上钉钉实则内藏玄机的案子,全部出自在下之手。
不过我却实在不能明白,秦曙光将这两桩案子夹在里面,到底意欲何为。莫非是要替在下指一条明路,与他一同将后半辈子贡献给公平正义的反腐倡廉斗争?
想到此处,在下豁然开朗,玉帝老人家这戏码排得正正好,上一辈子的苦情戏断在哪了?让我好好想想,哦对,就断在了曙光在明,老子在暗,正邪势不两立,于是机缘巧合得了个重生,要我从善如流,彻底洗白。
不可谓用心不良苦。
我心满意足地扔掉泡面盒,收起大部头,脱掉外套,一脚跨进洗漱间,打算好好冲个澡。
对镜自视的过程中,我再次欣赏了这个很年轻很健康的身体,它除了在见到曙光时一些部件会出现运转失灵的情况,总体来讲比我原先那个要好出太多。
事实上,在我办公室的右手第三层抽屉里还保存着年初单位组织体检的医生报告,拿到报告的当天十分有意思,别人都是薄薄一页纸,而我那里头的加页分量相当足,简直可以装订成册直接出版。
可以料想出结果当日,各科医生从十里八乡纷沓而至,争先恐后在上面写上一大篇热情洋溢的诊断结果,总结起来就是肝脏肾脾肺无一处幸免,病重程度可以直接引进ICU。
虽然没有我形容的夸张,但那个身体的状况有多糟糕,当时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于是我终日一张死人脸,中意迁怒于人嚣张跋扈的感觉,与身体状况的日暮西山也是不无联系的。
花洒下我闭上双眼,突然自发地想起下午那位仁兄说的话。
——你不是不收徒弟的么?
一壶热酥油,从老子头顶浇下来,浇了个通通透透。
有些事情,假如不串起来想,你永远摸不着其中的逻辑,比如,非亲非故的前提下,从不纳新只身一人的秦曙光为何对这个只一面之缘的杨浅如此上心?
老子一身冷汗被冲得干干净净,有件事从头至尾被忽略的彻彻底底,即那日在下坟前,曙光根本不是冲着悼念来的,却只为演一出相遇的桥段而已,于是更为可怕的结论浮在眼前——曙光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杨浅。
在下一生致力于阴谋论,却没有哪一次用得像今天一样心寒。
原来他同我一样,一早就看了这个实实在在干干净净的小青年杨浅,枉费我一腔愁情痴心妄想还能与他邂逅再续前缘,如果他知道这身体里埋着的还是那个污浊不堪的林寒川,我又该如何收场?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原来这一出墙头马上唱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端正态度,跑了整场的龙套还愣是拿自己当个角儿。
真是操蛋的人生完全不能去解释!
有好事者嫌老子的心理动荡还不够乱,偏在我浑身泡沫的时候打来电话,惊悚的铃声在客厅里闹个不停,我胡乱裹了条浴巾跳出去接。
电话是一个名叫楚东的人打来的,听口气似乎与杨浅十分熟稔,哦?难道我还有一个叫楚东的好友吗?这个三次元还真是配备齐全啊,正好我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聊聊天也是不错的,或者这兄弟也是位明白人,专程替在下解决生理需要来了?甚好甚好。
这个不怎么善良的念头在我见到这位楚兄弟时彻底被打消了,待在下赶至约会地时,只见壮士手执半瓶喜力,面色绯红指着在下怒吼:“杨浅,你还是来了!”
该说点什么好呢?这究竟是故人还是宿敌呢?为何说得一口如此烂俗的开场白,难道说这杨浅果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吗?
壮士大概之前已经喝高了,见在下楞在当场于是忍不住上前逼问:“那天带走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黑灯瞎火想看清壮士的面容实属不易,这个上前逼问终于使我得以全面了解他的长相。怎么形容呢,大概套上两个成语比较合适,棱角分明,刚硬不屈。
这两个成语在心中滚过,立刻使我兴味全无,但凡在圈子里混过的,谁不知道我林寒川只喜欢漂亮阴柔的男人?苍天可鉴,老子实实在在是个1啊!
然后接下来的一幕让混迹官场情场名利场数十年的在下更是手足无措,壮士一把将在下搂进怀里,一边颤抖一边哽咽道:“杨浅,我有哪点比不上他,为什么我爱你爱了这么多年,你却跟那头一回见的男人跑了?我没有钱没有权,我只有这一颗心,要不要我挖出来给你看?”
我想推开他却力道不够,无奈只得维持这个姿势叹口气:“他已经死了。”
话说出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我这才明白他真是喝高了,高到接下来的对话成了他的单口相声,完全不理会我的任何回应。
“杨浅,你说啊为什么?”
“他死了,杨浅也死了。”
“杨浅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啊!”
“……”
“杨浅……”
就这状态要老子说个毛啊,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