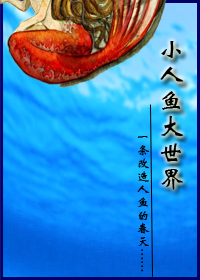第二世-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布被摘掉的那一刹那,我刚好踏进一扇门里,杭其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对我冷笑,整间屋子唯一亮着的是办公桌上一盏台灯,杭书记的冷笑幽幽地藏匿于这微弱的灯光背后,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和惊悚。
我就这么呆滞地看着他怡然自得地坐在我的办公椅上,等着他带给我惊喜。
“欢迎回来。”他最终打断了这短暂的平静,“林检。”
第三十二章
杭其还是从前那个杭其,但林寒川早已不是当年的林寒川,世间万物都在变,不变的,唯有变化。
办公室里响着杭其的声音,低沉的语调,不急不缓的语速,暗含享受的成份。
“林寒川,你不是一直想做个英雄?怎么现在躲在狗洞里不敢出来了?”
我愣了片刻,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被松了绑,正完好无缺地坐在门口会客用的沙发上,进行着一场或许是等待已久的对话。
“不过这样倒方便了我,守在洞口就能把你给逮着。”杭其直起身子,将重心转移到支撑在桌面的两只胳膊上,“我等你很久了,从中秋到现在——”
我心里好似被一桶凉水浇了个透明,然而表面上却不想让他看出明暗。
“杭书记什么意思,我不太跟得上。”
头脑里有一根筋在玩命地跳,我这也是实话。
“什么意思?”杭其的声音像是从几十公里外飘来的,充满了不真实,“林寒川,你还有什么筹码能拿得出手来跟我抗衡?”
话虽然没错,但我总不至于这么容易就顺着他的思路走,绝对是自寻死路。
“可能是我记性差,什么时候得罪了杭书记却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此刻看起来一定是满怀歉意,“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
“你没有得罪过我。”杭其倒也直截了当,“你得罪了中建。”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委屈:“杭书记,我为中建做事也有五年了,凭良心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以为退赃就能保住自己清白之身?”他冷笑,“下一步要做什么?想弄翻中建立个大功?”
我吓了一跳:“书记明察,小的实在没有退过赃啊。”
“哦?”杭其问道,“那账户里怎么会只有二百万了?不要告诉我你这几年就弄了这么点。”
我点头:“都花了啊,钓凯子泡夜店,哪样不得花钱?还都花的不是小钱——”
杭其皱了皱眉头,大概是觉得我讲话太直白?
“就算你没有退过赃,难道你敢保证心里没有这么打算过?”
“书记在上,难道有什么特异功能,能读人心了?”我又吓了一跳,“我那一片丹心照汗青,绝对生是中建人,死是中建鬼——”
杭其冷笑道:“你顶多算中建一条狗。”
“对对,一条狗。”我觉得我牛逼的地方就在于宠辱不惊的气场,随您怎么埋汰,我就是能淡定。
“你要干什么?”在我试图伸手往口袋里掏烟和打火机的时候,身边站着的两大金刚护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我的手反拧在身后,并警告以条子般的口气,“老实点!”
我无奈地看向杭其:“杭书记,来根烟?”
杭其点头默许,左护法从兜里翻出一包九五至尊,扔了一根在我两腿之间,十足厌恶的眼神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酒后失德强|暴过这位仁兄。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杭其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就算河边走,也能不湿鞋?”
我很谦虚,当即摇头否认。
“每个人都有欲|望,你想控制住,根本不可能。”他总结道,我觉得语气有点意味深长?
我苦笑道:“看您说的,我是那种禁得住欲的人吗?”
“表面上你的确不是。”杭其也跟着笑,“你自我放纵,追名逐利,有缝就钻,你根本没有原则和底线,你做足了一个恶棍,没有人比你更称职。”
我附和道:“您谬赞了。”其实我想说,年纪一把就别他妈学人文艺小青年讲话了,拿什么腔调?
“但事实上——”他转了话锋,“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压抑内心真正的欲|望,所以抛开表现看本质,你没有一刻不在苦守自己那根底线——你比谁都能把握住自己,绝不会失控。”
我默默地嘬着过滤嘴,吐着烟圈。
“一个人,看起来无所不为,恶贯满盈,但内心却高尚得像一张白纸——”杭其也开始点烟,片刻后打火机摔在桌上,清脆的声响便拔地而起,“你觉得这可能吗?”
“不太可能。”我摇摇头。
“林寒川,你一定觉得自己坚不可摧。”他说道,“因为你有着比谁都强大的内心。”
“其实杭书记您也不差。”我真诚地恭维道。
“坚不可摧……”他默念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
“还行吧。”我觉得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个人坚不可摧,我总是想看看他究竟如何能被打破。”他又重新看向我,洒给我一身寒意,“因为我想做一个无坚不摧的人。”
他笑着说:“所以我才把琉璃盏的秘密通过杨文宇透露给他那个年少无知正义感十足的儿子——说起来也好笑,杨浅一直想替他舅舅讨说法,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也在为我做事——我就这么站在外面,看你们这些人在一个又一个的圈子里打转,像一只只没有脑袋的苍蝇。”
这一切终于在我面前呈现出它真实而完整的面目,使得我一时难以消化。
虽然也想过自己经历的一切变故或许只是他人的一个念头,但从头至尾被他人计算得详详细细的感觉,此刻才真正领会。
我不知如何应对,思路仍旧是混乱的,只有潜在的意识不断释放出用以安定的情感元素,以期活得暂时的平静,从而恢复思考。
“你练书法有几年了?”就在中断的思考即将恢复之际,他突然间毫无征兆地岔开话题。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他这又是个什么思路。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叠宣纸扔在我面前:“看看这些,认不认得?”
我默默地翻着那一张张颇有些年代的宣纸,矫情而感触丰富地注视着每张纸上写得满满的草书。
虽然不想承认,但确实出自我的手笔——那些填满纸张的汉字统统指向字典里的同一页同一行。
“但凡熟悉你林寒川的,谁不知道你心里头只有一个秦曙光?”杭其的表情很像福尔摩斯正在揭晓案底,“然而你的底线却另有其人——”
“你是不是一直渴望着能有个第二世,好让你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在走过的岔路口前重新选择?”他继续道,“我好心给了你这个机会,所以想问问,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不得不承认,真他妈傻逼透了。
“是不是觉得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紧追不舍。
草,还真是。
“你爱上了那个像极了你十年前的年轻人,你穷尽所能地试图保护他,让他最大限度的远离这个社会的阴暗面而不惜身体力行地去做反面教材,甚至你做的一切只为获得他的厌恶,从而守住你的底线,控制住你的欲|望。”杭其还在滔滔不绝,“他才是你的弱点。”
“但你万万没想到即使自己费尽心思亲手炮制了这个假象,最终,他还是爱上了你。”他的语气是嘲弄的,他的表情是喜悦的,“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是种草你的心情!”我瞬间失控,思想已经不能指挥行动,直接冲着他扑了过去,然而却迅速终止在了两大护法的钳制之下。
他们牢牢地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按在地上,我只能昂着头以屈辱的姿势维持可悲的尊严:“MB你心理变态啊!”
我的语言已经失去对峙性,虽然贲张,然而无力。
“这种反应就对了。”杭其俨然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我,“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他屈起手指,抓着我的头发将我拖去了窗边,我试图挣扎,然而难敌左右护法内力强大。
“你大概还不知道。”他一只手推开窗户,另一只手强迫我探出窗台,冰冷的窗框抵在我的喉咙口,迫使我止不住地咳嗽。
“看仔细了。”他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耳廓,“温淮远就是在这里,这个窗口,跳下去的。”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
“自杀是官方说法——反贪局侦查处处长因患忧郁症而跳楼身亡——”他阴测测地笑着,“实际是被我扔下去的。”
“三天前。”他最后补充道。
望着下面那漆黑的虚无,我感觉自己悄无声息地落下了一滴眼泪,深夜的沉寂已经凝固在周围,无言以对。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那片虚空中扎了根,然后像藤蔓植物,爬在我的胸口猛烈地生长。
“我一直很有兴趣,怎么才能把打破你这样一个坚不可摧的人。”
冰冷的声音染上了夜色中无边的黑暗,就这样浮在我的耳边,使我艰于思考,艰于呼吸。
第三十三章
“从失去自由那一刻开始,你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相对姿势没有改变,杭其的声音依旧漂浮在我的周围。
身体本能地在做着徒劳的反抗与挣扎,思想却回应以沉默。
就像突然一脚踩空,茫然与无措接踵而来,从前与过往被撕得粉碎,散落四处。
“现在又在想什么?”他不知疲倦,兴致盎然。
发根连着头皮被更大的力量拖向前,我被迫又探出窗外十来公分,相当狼狈。
晚风呼啸着擦过我的耳朵,我的脸颊,我每一根毛孔,我的每一根神经。
“想不想死?”
离黑暗又近了几公分,双手虽然扔被拧在背后,半个身体却已经处于悬空的状态,唯一的承重寄托在那五根拽着我头发的冰冷的手指。
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似乎都近在咫尺,虽然看不清楚,却无所畏惧。
死过一次的经历都远不及此刻的真实,死亡这种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概念正在我眼前、身侧、脑后不断地具实化,逐渐成型。
“你是不是在想,跳下去——”声音邪恶而充满诱惑,“——跳下去就解脱了?”
思绪被拉得细长几乎断裂,绷在上面的,是最后的理智。
“不——”声音像是不经过大脑就从喉咙口冲了出去,近乎本能的呼喊击碎了所有虚构出的伪装,“不想死——”
“很好。”
毫无预感的力量将我拖了进去,继而摔在地上,昏黄的台灯落在我面前的地砖上,画出一条不十分分明的光与影的界限。
“我希望你活着。”他站在我面前,快乐地说道,“活着,像一个不会思考的动物,像一堆行尸走肉——”
我茫然地抬起眼皮,想读懂他话中的意思。
“温淮远跳下去之前,向我提了个要求——”他蹲在我面前,不动声色地搂着我的肩膀,“——我满足了他。”
“什么?”
“他要我把琉璃盏给他。”
我在身后握紧了拳头。
“然后当着我的面摔碎了——”他眯起眼睛,异常兴奋,“这就是爱啊!感受到了没有?哈哈哈——你说你还有资格去死吗?你有脸去死吗?你看你连死都不行了——”
“你MB的!”我的拳头已经撞击在他的颧骨上,发出不重不轻的声响,而他被手捂着的脸颊仍旧绽放出不可思议的笑容。
“——哈哈,你还有大半辈子的时间,打算怎么过?我们讨论讨论?”
左右护法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半边脸贴着地砖,被挤压得变了形状。
不可名状的情绪,不能言说的痛苦,从来没有一刻像如今一般,发作得肆无忌惮。
我的脑子里盘旋着杭其的话,明知都是放屁,却思考得格外认真。
大概思想不能指挥行动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能控制思想。
不过幸好,我还能思考。
拳头像雨点一般落在我的身上,疼痛的感觉异常实在,我想了很多——之前总是不理解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为什么会遭到意志上的瓦解,现在总算知道这一切皆因你心中仍然有欲|望,而这种欲|望通常被称作希望。
“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了解你心中的那种想摆脱却永远无法摆脱的欲|望,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你身处哪个世代,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杭其站在边上,观众一般欣赏我被殴打的整个过程,“无论多少世——”
他最终没有弄死我,虽然我觉得被弄死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没有发生变故,中建也不会让我活得太久,袁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于是发自内心的,我开始理解杭其。
总有个人会代替中建扮演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或者他也是身不由己。
然而他却放过了我,可能是觉得我会进入一个生不如死的状态,因此也不必再添一条人命,也可能是出于怜悯,给我一个暗示,给我一条生路。
我艰难而缓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其间踉踉跄跄尝试了很多次,最终还是坐实在了椅子上。
浑身都痛的厉害,一波一波地延迟到现在才集体迸发。
我就这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四周熟悉的物件,回忆着过去的丝丝毫毫,那种程度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了绝望,呈现出一种麻木的平静。
不知道谁将填补这个位置,我也再没有兴趣去想这个问题。
突然间竟然有点羡慕温淮远。
人生有太多的选择,假使知道每一种都是痛苦,是不是早点离开才是最万全的方式?
坐了一阵子,感觉差不多能走了,便扶着桌边慢慢起了身,不知道该去哪里,只知道急需离开这里。
走出检察院大楼的时候,杭其的车正停在路边。
他摇下车窗对我说:“你应该谢我。”
我无力地点头:“是啊,是该谢你。”
街灯淡淡地照在君越的屁股上,杭其的轮廓是半明半暗的,一半敞在灯光下,一半隐在黑暗里,呈现出一种亦正亦邪的状态。
他看了我一会儿,表情难以捉摸,眼睛是看不清的黑色,像黑洞一样吸收着所有的光线,我读不懂他想传达给我的信息。
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懂了。
尾气喷在面前,君越载着我人生的审判者呼啸而去,我抬起头,看见天边一轮明月,圆得令人发指。
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过去,犬儒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在这十几年里不断寻找着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位置,到头来,仍旧飘无定所。
我将不能实现的理想化作深埋心底的欲|望,将对未来的期待化作终日的放荡,我什么都交待不了,因此做梦都想有个第二世,好让我重新读档重头再来。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夜已经深了,车辆和行人都在递减,他们都形色匆忙,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存在。
我想发泄,却异常的平静,甚至再挤不出一滴眼泪。
我撒了谎,你们或许已经发现了。
实际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淮远,他的相片就一直塞在我钱包的夹层里面,怎么可能认不出。
我拼了命地告诉自己,真的爱他,就不要毁了他。
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克制过自己,却没成想到头来,还是同样的结局。
那轮明月依旧执着地圆在天边,我站在公交站台的边上,瞧着它出了神。
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我喜欢这句话,然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我们也总是习惯说,如果有来世。来世就会变得更好吗?没有人知道。
一辆救护车闪着顶灯呼啸而过,我沿着它驶去的方向走进了一座小区。既然我已经不知道该去处何方?
穿过一片健身场地,绕过几栋寂静矗立的小高层,我终于看见了那辆救护车停靠的地方。
漆黑的夜承托着楼道里的灯光,遗世而独立的光芒,我顺着那道光的指向沿着楼梯慢慢地往上爬。
扶着楼梯的手虚弱且颤抖。
但却无法停下脚步。
不出一会儿,便有人躺在担架上,在他的周围布满了毫无表情的脸庞。救护人员的脚步是匆忙的,于是我便看清了担架后面那张脸上与我相似的茫然。
他扒着门框,泣不成声,然而却满是虚情假意。
一道雷轰在我头顶。
后知后觉中我方才明白,那日门外不协调的脚步声,既不是温淮远也不是楚东更不是秦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