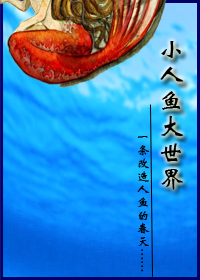第二世-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知道。”他用胳膊环着我的脖子,就这么仰着头与我对视。
他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让人上瘾,欲罢不能,我就这么看着他,像是少看一秒就会忘记。
从前我尚且能用一副刻意制造的伪装来隔开我与他,克制心底的念想,而如今就仿佛最彻底地裸|露在他面前,没有退路,也没有遮挡。
我深知跨出这一步自己将无法克制,或者会万劫不复,但没有一条是回头的路。
我低下头,慢慢地照着他的唇形印了下去,脑子里只剩下最简单最原始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我们通常叫它做——爱。
“你钱包里那张照片,我很早以前就看到过。”他问道,“为什么你一直不敢承认?”
“我怕你看上我,进而不可自拔,直到酿成人间惨剧——这实在是司法系统的一大损失。”我又说了句大实话,“况且倒追我的小帅哥目前还有一个加强连。”
“你会不会压力很大?”我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问道。
“我爱你。”
就在此刻,我听到了全世界最沉重的字眼。
第三十六章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家里的牙刷就变成了两根,拖鞋变成了两双,毛巾变成了两条,迫于他老人家的淫威,我不得不含泪接受了同居这个事实,这也使得老子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又一页。
在细枝末节中体会生活的乐趣,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爱情的喜悦,老子像个心思活络的吟游诗人,不,是像文艺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之中。
大千世界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浓缩成油灯里的一根棉芯,在死亡到来前缓慢燃烧,虽然结局大同小异,期间发光放热的过程却只有自己能体会。
“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搬去我那里住。”针对我的反抗,处长他老人家是这样回答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到底是谁他妈官大一级?
“我们反贪局就是为了办你而存在的。”在我提出了以上疑问之后,他又是这样威胁我的。
在他说完这一句之后,我竟然微妙的萌了。
然而萌完之后我就忧心忡忡,玩笑虽然开着能怡情,但有些实际的东西摆在那里,就算现在不去碰,也早晚有一天要面对。
比如,爱情的伟大也不能改变我被中建当枪使了五年的事实。
当初这一步可以说我走得义无反顾,也实在没有什么后路,同流合污到了这个地步,想全身而退几乎已经不可能,唯有撞个鱼死网破。
不过决心虽下的容易,实行起来却颇为艰难,曾经我着了魔障看透人生整天发些白日梦实际的确了无牵挂,然如今又跌回红尘俗世里,更被一个情字绑得牢靠,于是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放,完全乱了主张。
我方才意识到,如果你想打破一个强大的人,那么就给他以爱,他便会从内部瓦解,毫无招架之力。
曾经我以为自己像堵城墙坚不可摧,最后还是被撞得只剩断壁残垣,片瓦残砖。
于是我改变了思路,既然不能搞Plan A,总得备着个Plan B,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打算一直计划到Plan Z。
我偷偷地做了很多事情,虽然不甚光彩,但总是在为将来扫清障碍。
比如退赃。
退赃这种事情,光胆大心细还不够,最主要你得干的偷偷摸摸,因为这他妈是坏事啊,假如你一脸正气地去找人退赃,势必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于是我乘着夜深人静接连走访了好几个曾向我行过贿的同志,并婉转的表达了“办事可以,钱拿回去”的中心思想之后,大家竟然一致认为我这是要遁入空门了,于是也都大方的表示既然老林你都一心向善看破红尘了,那些凡尘俗事也就别费心了,搞得我都觉得自己很不厚道。
所以在给每位同志都做了一次暗地里的录音之后,我就乘着上班时间溜了号,把钱都给几位打账户里去了,并果断地注销了自己的账户。
至此,这事就勉勉强强告了一个段落,万一将来东窗事发,我这也算是积极退赃了,最起码死缓问题不大了。草,瞧我这点人生追求,真他妈磕碜。
这一整天老子心情都很好,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内线电话打到淮远那里去,结果被告知已经走了,我当时就暗自感叹:一直以为只有我这种人喜欢迟到早退,没想到你堂堂温淮远也好上这一口了?这不是个好现象啊。
就在我的拇指搁在拨出键上犹豫是不是要给他挂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呼叫倒适时地接了进来。
“是我。”他说。
“去哪了?”我问。
“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我说:“哦,那我一个人随便弄点。”
他那边沉默了片刻:“不问我去哪?”
我说:“你去哪?”
他答:“市委领导请吃饭,电话直接打到内线不好意思推。”
“哦。”我觉得自己似乎大概是没有不高兴的感觉?“这时候吃午饭好像有点晚啊?”
“别这样。”他叹气,“我尽量早点回去。”
我爽快地答应:“没事,我给你留门。”正要收线的时候听见他急切地说了声“等等”,便又将听筒放在耳边:“怎么了?”
“我会早点回来的。”他又说了句。
“我知道。”
“我说的是真的。”他的话里好像有点别的意思?
“你怎么了,有什么话直说行不?”
“所以等我行不?别去找……”
“找什么?”我觉得莫名其妙。
“这几天夜里你都去哪了?”他好像问得很忐忑。
草,该不会他以为我这几天晚上都去找一夜情了吧?我盯着桌上的台历,有点百口莫辩,怎么解释?难道说我退赃去了?
“你不是都睡着了?”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完便顿觉实在是太傻比了。
“浅睡眠。”他平静的陈述道,仿佛他的平静就是用来折磨我的。
“我真不是去找……那啥的。”我无力地解释道,“只是办点事而已。”
那边又是声叹息,叹得我肝疼:“下回让我陪你去办行不行?”
“行行行。”我讪讪地答应,暗自庆幸好在没下回了,“少喝点酒,我等你。”
“嗯。”他说。
“给你准备蜂蜜水醒酒。”我讨好他。
“嗯。”他好像不是很领情。
实际上我和他同居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为掩人耳目我不得不让驾驶员早上不要来接,而选择自己开车上班,他一般会坐在后排,然后在快到单位的地方提前下车,极具地下工作者的潜力。
但这也不是长远之计,早晚会被人撞见,回头以讹传讹再这么一加工,我的名声事小,回头要连累了他便有些不过意,特别是他老子正在我头顶上坐着,得罪不起。
于是我总说给他买台车,但他也总说不想学,让我给他当司机挺有面子,这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回家的路上,我完全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思辨当中,明明这家伙一直睡得很深,怎么就浅睡眠了?
这种思考来的太过热烈,导致我完全机械地握着方向盘直到眼前一道闪光才回过神来——闯红灯了。
这是我这个月被扣掉的第四分了,上一回是被某人从后面亲了一口,当时就油门当刹车给踩过线了,搞得我一直耿耿于怀,你说人这一生有多少个十二分能让你这么肆意挥霍?
于是我的心情很不好,想到回家要一个人对着残羹冷炙就更加高兴不起来,方向盘一打就奔延安路去了。
我打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杯啤酒,打发打发时间,然而就在我拿了停车牌正准备倒车进位的时候,右前方一辆银灰色的帕萨特也打了倒车灯,很明显在向我挑衅。
我这个人向来低调,不像那些傻逼官员一样在外头公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就让了,况且那个印着我生日号码的车牌就是他妈烧成铁水我也不会不认得。
所以,人生在世,走为上计,于是我推了前进挡,打算另辟蹊径。
世事不遂人愿者居多,倒车进位的帕萨特直接横在了老子面前,似乎昭示着一场明显的正面碰撞是免不了了。
“好久不见啊林检。”车主愉快地站在我半摇下的车窗边。
“是啊,挺久了。”我硬着头皮回应。
在这漫长的十年里,除去今天,实际我与他只有一次正面对话的经历,那回大概是发生在我升副检那天各方溜须拍马的好手给我摆酒席的那间饭店里。
当时我喝了半斤白开水换的酒,尿意甚浓,站在厕所里正享受开闸放水的快感,骤然身边有人开口,且话里明显扎了刺,那人说,林副检,尿得挺顺畅么。
我干笑一声,说何止顺畅,简直是一泻千里。
然后他冷笑着扔了句话走了,他说希望您的仕途不要也是一样,一泻千里。
实际我在白日发梦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设想过与他见面的情形,我要如何贴切的自我表达,要如何向他展现生活的美好以及分手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的态度,然而没有一种会是之前的那种情形。
“一个人?”他探头进来假意张望着。
“嗯。”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还没吃饭吧?一起?”他的笑容毫不生分,“我也一个人。”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话里有些许暗示的成份?
就在我还没有确定是不是应该开始这场会面的时候,身体却已经处于一家餐厅的临窗位置上。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装修十分考究,且以杭帮菜为主,口味比较清淡,是个吃喝腐败的好去处,除了包厢以外,大厅里也有一些位置,大多提供给情侣用餐。
“最近怎么样?”我决定掌握主动。
“不想搞刑辩了。”他给我斟上一杯啤酒,“来钱太慢。”
我点点头:“搞民辩也好,离婚遗产之类的,钱好挣。”
“也安全。”想了想又补上一句。
“是啊,也安全。”他重复着我的话,“每次开庭我一想到又要跟你们检察院作对,就总是有一种把脑袋拴在裤带上读辩词的感觉。”
气氛很轻松,我便也将语气尽量往轻松里调整:“是啊,现在一提到你的名字全院上下都恨得牙痒。”
“还是一个人?”他突然问得我毫无防备。
就在他转移话题的同时,我转移了视线,盯着左前方的包厢门:“不是了。”
“你呢?”问完这一句我突然很怕听到答案,不管是肯定的答案还是否定的,它们都一样会令我感到沉重。
“正在发展中。”他端起酒杯,象征性的要与我碰杯,“回头带给你见见。”
“一个系统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会追问下去,明明到此为止就已经很好了。
“算是吧。”他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之后我便岔开了这个话题和他聊了些别的,其间淮远来了一条短信问我在干吗,我回复说在家上网。
就在这条寻常的短信刚发出去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左前方那扇包厢的门出乎意料地被打开了,紧接着我便看见短信的主人站在门口,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之后定格在了秦曙光的身上,而后者并没有察觉到。
第三十七章
从来只在电视里看到这种狗血白烂的剧情,没想到自己也得了个巧给碰上了,感觉十分荣幸,而当温淮远已经走到桌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站起身说了句:“二位慢聊,我先走一步。”
秦曙光轻轻咳了一声,我听的很清楚,但他也只是咳了这么一声,而并没有阻止,或者主动说些什么。
温淮远大方地点了点头,填进了我让出的那个身位,继而更加大方地坐在了我让出的那张椅子上。
我愣在当场,进退不能,只听见秦曙光用一种平静地难以形容地语调漫不经心地问道:“林检花了多长时间把你追到手的?他又是怎么能把你给追到手的?”
草,原来他已经知道了,不过老子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怎么就被说得跟滞销货一样呢?当时我就感到很不受用,脚底下也顺理成章地迈不动了,站在原地等着听温淮远的回答。
相对论告诉我们相对时间像一根皮筋,时长时短,这回大概就算是扯得挺长了,因为温淮远他迟迟不开口,进退不是的感觉就让我觉得越来越难熬。
这当口,秦曙光又补问了一句:“不会是拿什么不正当理由潜规则你的吧?”
“去你的,说什么呢,老子像那种人吗?”我忍不住质问道。
秦曙光还真他妈思考了一会儿,继而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像。”
“你告诉他,是不是老子强大的个人魅力使你无法自拔?”我觉得自己的语气已经相当循循善诱了。
温淮远夹了一块杭椒,嚼得活色生香,全然不顾老子的尴尬,虽然我知道这个当口他的愤怒或许要远远超过我的尴尬。
“被强|奸得太久以至于产生了爱情。”然后他平静地回答道。
草,这是什么话,老子堂堂副检察长,随说不上风流倜傥万人景仰,但能长得那么像强|奸犯吗?
秦曙光脸上的表情我很难形容,大概有十分之三的难以置信加上十分之三的景仰崇敬再加上十分之三的兴会淋漓。什么,你问我还有十分之一是什么?我绝对不会告诉你那是意犹未尽的。
行,老子就当你是心情不好,不跟你计较。我也同样平静地打算平静地回家再平静地看几部平静的小电影平静平静。
蓦然间,手腕被人轻松而用力地捉住,在我诧异地回头看向肇事者时他又将桌上一杯啤酒推进我掌心。
“杭书记在里面,不去敬杯酒?”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并没有与我达成交汇,这比知道他和杭其有往来还要令我不爽。
“去个毛,要老子陪酒?他请不动。”我把陪酒两个字咬得很重,“就当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家,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幻觉,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他看见你了。”他很轻松地打断了我的文艺情结,“他跟我说你在大厅里,叫我出来打个招呼。”
这么一搞我真就没法走了,虽然从行政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他要高出半级,但是他接管了中建,所以我必须屈从于他,就像传销里的蓝宝石级的要受红宝石级的领导,当孙子当到我这个高度的,难免会有些高处不胜寒,至于到底有多寒,这种感觉你们是不会懂的。
“草。”我低声咒骂,怀着一种逼良为娼的心情拿了只空酒杯准备上战场,啤酒顶球用,跟这帮人喝酒,不喝到胃出血你别指望能爬出包厢门。
什么你问杭其酒量是不是很好?他不会亲自跟我喝的,他会用各种各样令人作呕的理由教唆那帮陪酒的下级跟我喝,虽然表面上全是恭维话,然而真相却只有一个——酒桌上级别最高的那个是永远不会“被喝酒”的——只要你的头上还有人,你就会无休止的“被喝酒”“被受贿”“被贪污”一直到“被自杀”。
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快要走到最后一步了?
就在我酝酿到差不多的时候,杭其却一手握瓶梦之蓝,一手夹两只高脚杯相当高调的亲自出了包厢门。
他向我露出了领导特有的招牌式的微笑,似乎是故意透露出的亲民气氛完全掩饰不了浓郁的官僚做派:“林检,现在请想你吃饭基本上是请不动了啊。”
“哪里的话。”我客气地迎上两步,挤出一脸歉意:“不知道书记在里面,罚酒罚酒。”
温淮远也站了起来,主动接过杭其手里的酒瓶和高脚杯,摆在桌上,动作很熟练,且发自内心。
实话说,我很不受用。
秦曙光则显得十分反常,他依然好整以暇地坐在原处,间或用一种玩味地表情看我两眼,似乎根本不买市委书记的账。
从情形上看,秦律师打算置身事外,但是老道如杭其这样的官场老手怎么可能会给对方这种机会呢,只见他主动斟了半杯酒挪到秦曙光面前,用一种极为熟稔的口气说道:“曙光,最近忙什么呢?”
秦曙光斜他一眼,只持续了大概0。5秒左右,口气冷淡:“忙着反腐倡廉。”
杭其面不改色,笑着接道:“那不是林检该忙的事嘛!”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不那么简单?
“哪里哪里,主要还是得靠社会监督。”我看了一眼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