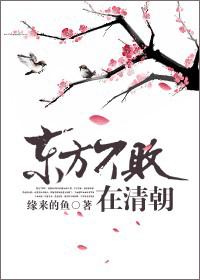穿到清朝当戏子-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别说是少爷,就是我,晚上做梦也常……”
“也常什么?”
见商承德面色忽然严肃起来,陆青缩缩脖子不再说话。
平日里,商承德这时候总要往春沁园走一遭,不为别的,只是这两个月来已成了习惯,今日府中设宴,没能去春沁园,令他觉得焦躁难安,于是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陆青被绕的眼花,央求道,“少爷,您再转下去,我可就晕了。”
商承德却是不理他,陆青苦着脸站着,忽而灵机一动,“哎,对了少爷,我听说城外北城百顺胡同那儿明日新开一家戏园子,那戏园子老板据说可是个美男子,咱要不也去瞧瞧?”
商承德没好气地瞪他一眼,“你要去便自己去。”
陆青顿时哭丧了脸,“我的少爷,再这样下去,您没什么,我非先疯了不可。”
韩家谭一带便是那八大胡同的风月街,与韩家谭隔了几条街的百顺胡同如今新开张一家戏园子,名为“西祠楼”。
这西祠楼原是一家清茶馆,半个多月前转手给了别人,经过一番装修整改修葺,如今已俨然成了一座戏楼。歇山卷棚顶,轻巧飞檐,蓝色琉璃瓦,啐金剪边儿,整座建筑无处不画栋,无处不雕梁,便是屋脊、栏杆处都有极为精细的雕花卷纹。
戏园临街一间宽敞门面,进去之后有一前院,内设小摊几处,再往里便是戏厅。戏厅一楼分池座和廊座,池座平地,廊座地面稍高,倒八字整齐摆放数十套长条桌凳,除此之外,沿墙设有一排高凳,俗称“靠大墙”。二楼为包厢雅座儿,桌椅均为实木雕花,喝茶的杯子,盛点心的碟子,也都是成套的。
锣鼓铮铮,劈哩啪啦一阵鞭炮乱响,这西祠楼正式开张了。
原先是茶馆儿的时候,这里冷情得不见几个人影儿,如今开了戏园子,前来捧场的人却挤满了整座大堂。池座、廊座、包厢,就连一楼那排靠大墙,如今也挤得满满当当,从上望去,黑压压一片。
铜锣铛地一声响儿,方才还喧声鼎沸的戏厅忽而鸦雀无声。
只见那绣有“出将”字样的五彩门帘掀起一道缝儿,随后锵锵锵锵,踩着锣鼓碎步出来一位身披大红锦缎开氅之女子,柔荑纤手,扶柳细腰,水袖一抛,眼波才动被人猜。
谁道不是女娇娥?
台下足足静了半盏茶,随即轰鸣掌声,轰堂喝彩,生生掩盖了锣管弦音。
连天叫好声一波盛似一波,这等热闹喧天,简直空前绝后。
戏罢,红氅女子入了帘子,随即一只手便伸过来捏住了“她”的下巴,“啧啧,苏老板这般倾姿绝色,实在让人欲罢不能。”
苏倾池懒得理他,拍开男子的手,“花老板,下一场可轮到您了。”
“啧,还真冷淡。”男子倒是不急,靠在墙头看着正在卸妆的苏倾池,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苏老板,在下这般精神抖擞,怎上的了场?”
苏倾池眼角斜过去,掸掸袍子,起身缓缓上前,“花老板想怎样?”
男子俊挺的眉毛微微一挑,俯身在苏倾池耳垂上一咬,“不若倾池这张小嘴替为夫……”
随即一声闷哼。
苏倾池笑道,“替你如何?”
男子一脸惋惜无奈,“唉,倾池,你若是当真下了狠手,以后可得守寡了。”
苏倾池手上一紧,“花老板这孽根趁早断了的好,不如苏某现在就替花老板解决它,以绝后患。”
“哎哎哎,我求饶我求饶。”男子两手举起,作投向状。
苏倾池这才松了手,那男子瞅准机会,忽而凑前,偷得一个香吻,随后风一般溜得没了影儿。
帘子外头铿锵再起,掌声轰鸣。
这人竟当真顶着个……
也亏得那戏袍子宽大。
苏倾池一脸无奈,又有谁能相信,这没节|操之人竟是名动京城的小生花景昭。
雨中凝眸
一小碟酱瓜,一碟豆豉,一碗白粥,一根鬼腿(炸油条),三人围坐在院中央凉棚之下吃早点。
这些酱瓜豆豉,都是自家腌晒的,晾干之后拌上茴香、紫苏等调料小炒,味道清脆,开胃爽口,配上一碗白粥,在这季节吃着倒也爽快。
苏宝儿咯曾咯曾嚼着酱瓜,低头喝了口白粥,两只眼睛在他哥和他对面的男人身上来回地转,最后停在他对面那个男人的脸上。
“怎么?小宝儿别是迷上我了吧。”花景昭放了筷子,唰地一声展开扇子,动作潇洒。
苏宝儿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我是瞧你脸上的鞋印子,你昨晚又翻进我哥屋里了?”
苏倾池面上一派无情无欲。
花景昭讪笑一下,摇着扇子,“最近采花贼张狂,我这不是怕你哥遭了贼手么?”
苏宝儿撇撇嘴,低头喝粥。
花景昭收了扇子,摸了苏倾池的手,“倾池,你放心,师哥一定护你周全。”
苏宝儿一口粥险些喷出来,咳嗽两声,拍着胸脯,“花大哥,你啥时候成我哥的师哥了?”
“哎~”花景昭一皱眉,“小宝儿怎么这样说,我当初也在王家村学戏,只不过在你们去的时候我转去了别的班子,这样说来,我可不就是你哥的师哥,倾池,你说是也不是?”
见花景昭这样恬不知耻地摸苏倾池的手,苏宝儿只能翻白眼。
苏倾池抽了手掸掸袍子,起身,“我去西祠楼瞧瞧。”
花景昭跟条软蛇一样缠上来,搂着苏倾池的腰,尖细的下巴抵在他肩上,“我同你一道去。”
西祠楼自开张那日就场场满座,先不说别的,单是每天冲着苏倾池和花景昭来的人,就能把这西祠楼塞得满满当当。
苏倾池既是这西祠楼的房东又是铺东,另外还是专属西祠楼的小戏班儿的班主,身份不可谓不重要。
西祠楼的戏班儿除了名下的粹锦班,其余的班子并不固定,平日里只作为各家戏班儿唱戏的场所,每日只要在西祠楼门前挂一张牌子,注明今日请了哪家的班子,唱哪几出云云,剩下的事儿便是坐着等数银子。
这西祠楼只算个消遣的场所,里边楼上楼下,池座雅座儿,各个地眼儿都配了几个跑堂的,每日提着茶壶四处添茶添点心,西祠楼场面虽算不得最大,但是这里茶水点心的名堂可不少。
茶水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碗茶到千金难买的精贵名茶,只要你叫得出名儿,它就有。
点心的名目更是遍及天南地北,有京城的特色糕点,也有江南特色的汤水小吃,便是冲着这点心,每天也能吸引不少顾客。
两人到西祠楼里溜了一圈儿,出来的时候已经近午时了。
花景昭方才与人搭戏唱了一出,出来的时候口干舌燥,便拖着苏倾池进了路边的摊子,点了两碗桂圆汤。
路边的摊子自然比不得西祠楼,木条桌长条凳,一不留神就能蹭一袖子油腻。
这里做的桂圆汤作料虽然粗糙,不过却也有股独特的味道,比那些大酒楼里的可有滋味多了,苏倾池平日里无事,便在这胡同里四处闲逛,早把这百顺胡同里的特色小吃给吃了个遍。
花景昭素来闲不住,才吃了两口,便不老实,“哎,倾池,左右无事,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苏倾池头也不抬,“你能有什么好地方。”
花景昭往四周瞧了瞧,凑到苏倾池耳边说,“销魂儿的地方,去不?”
花景昭指的消魂地儿,不是别的,而是那韩家谭一带的相公堂子。
那相公堂子之内,多半是清俊之伶人。
清朝禁娼不禁戏,导致贵族子弟、风流名士纷纷痴迷于扮相俊美的伶人,甚至有人因亵玩伶人过度,致使精尽血出,脱|阳而死,当时人们对于伶人之痴狂可见一斑。
许多戏班为了应和世人喜好,择选学戏幼童之时,常挑选那些相貌清秀者,令其每日晨间以肉汤洗面,入夜以秘制药膏敷体,三四月之后,那些幼童肌肤白皙,眉目清透,婉若女子。
那些个相公堂子,门外挂着小木牌,书以某某堂,门内悬挂灯笼,其内的相公年龄大致在十三至二十之间,均通过上述法子培养。
清朝最出名的伶人与相公有三,分别是乾隆时期的李桂官和方俊官,以及道光时的陈长春,这三人共有一个称谓——状元夫人,这皆是因为与他们相好的老斗(嫖|客)考中状元,其中方俊官的相好庄本淳病逝后,方俊官为他守孝一年,极尽妻妾之道。
这等与伶人的断袖之交,狎弄亵玩有之,真情实意有之,实在不好辨其是非好坏。
苏倾池懒得同他说,扭头看向外头嬉戏耍闹的总角小儿。
那三小儿一个扎着朝天冲,一个辫着狗拉车,另一个剃了个鬼见愁,模样憨厚喜人。
花景昭摇着扇子,笑得偷了腥一般,伸手在桌下摸上苏倾池的大腿,“倾池这般,莫不是吃醋了?”
“你要是嫌活长了,尽管把手再往里边伸。”苏倾池淡淡地道。
花景昭满脸遗憾地把手收回来,“唉,倾池啊,早晚有一天我会被你逼的爆阳而死,嗷嗷嗷,我求饶,娘子莫怪,娘子莫怪。”
花景昭皱巴着一张脸,说是疼,还不如说是作怪。
嘿嘿一笑,抬头却见苏倾池望着外头,花景昭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倾池在看什么?”
门外三个小儿两个站在一边,一个坐在地上,面前还站着一个锦衣的男子,看样子是嬉闹之间撞上路人了。
花景昭瞧着那男子,那人模样长得倒是端正清俊,一派儒雅之气。
“少爷,您这衣裳……”一旁的小厮道。
男子低头看了眼袍子上的糖渍,面上含笑,俯身扶了地上的孩童,“没事,起来吧。”
替小儿掸了身上的灰尘,瞧那孩子一脸要哭的模样,男子捡起地上沾了一层灰的糖葫芦,笑道,“可惜了这糖葫芦,陆青,你去买几串来。”
陆青无奈,应了声哎,跑到一边买了几串糖葫芦来分给三个小孩。
“下次玩闹可得当心了。”男人伸手摸摸那孩子的脑袋,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
陆青在一旁塌着肩膀,“我的少爷诶,您这样怎么去见邓老板?”
男子扫他一眼,“不过一套衣裳,你也能计较成这般。”
“好好好,我不说。”陆青耸着肩膀,“除了苏老板,谁能说动您呀。”
“嘀嘀咕咕什么呢。”
“没~”陆青耷拉着脑袋,跟上前去。
花景昭摇着扇子,戏谑地瞧着苏倾池。
“看什么?”苏倾池瞥他一眼。
“啧啧啧,倾池啊……”
“倾什么池,还不付账。”苏倾池丢下一句,撩起袍子走人。
“哎,得,谁让我就您苏老板一钱袋子呢。”花景昭摇着头,付了钱,钻出铺子。
两人回了宅院,苏宝儿已经烧好了水。
院子一角用木板搭了一个露天的浴室棚子,三面一人高的木板,一面带门,底下铺着石板铺地,浴室里边放了一只半人高的大木桶,外边放着一个大水缸。
这浴室素来为苏倾池专用,平日里苏宝儿只站在浴室旁,舀水缸里的水洗澡。
便是花景昭住进来,也只能站在外头冲澡。
花景昭如何住进苏倾池的宅院,这要说来,还有一段故事。
苏倾池当日与春沁园解了契约,带着苏宝儿住进了北城早些时候置好的宅子,住进来的第二日便大刀阔斧地办了两件事,一件便是找关系让苏宝儿进了官办书院,另一件便是寻了块好地界,盘下一间临街的铺面开办一家戏楼。
这戏楼子是开起来了,但只靠一个人,总撑不得门面,于是每日苏宝儿去书院之后,苏倾池便四处走动,留意京城里有名气的角儿,盘算着挖别的班子的墙角,也正是这个时候,花景昭找上了苏倾池。
这花景昭在北京城可不是一般二般的小角儿,早在苏倾池在京城落脚之前,这人就已经是京城红得发紫的名小生了,这样的人,便是苏倾池,也没敢轻易考虑过。
若是换做别人,兴许不敢要花景昭这尊大佛,可苏倾池是谁?这兔子都撞到树桩上来了,哪有不捡的道理,当下就立了契约。
按着花景昭的话来说,苏倾池就是个苍蝇腿上也能刮二两肉的主儿,不过当初确实不怪苏倾池吝啬,实在是置办完一切之后,苏倾池身边银钱所剩无几。
但花景昭却没要苏倾池一文钱,他的要求很简单,给他一个接近京城人人追捧的名旦苏老板的机会,并且供他吃住,这就足够了。
当初花景昭说这番话之时,摇着金丝扇,恰如临风玉树,是何等的潇洒风流。
苏倾池勾了下唇角,“成交。”
苏倾池每日与苏宝儿清粥小菜,便是有一两样荤菜,也绝对是花景昭掏腰包。
花景昭使银子使得义无反顾,苏倾池便吃得心安理得,苏宝儿跟着他哥自然讨了不少便宜,三人这般相处,其乐也融融。
此时,花景昭裸着身子,只腰间裹了一块巾子,手里举着瓢,舀水冲澡。
苏倾池在浴室之内,两人隔着一块木板。
苏宝儿趴在一旁的凳子上习字,就瞧着花景昭一刻不停地摸索着木板上的缝隙,一个澡尽绕着他哥的浴室棚子转,实在无耻得令人费解。
“小心我哥打你。”苏宝儿用口型说。
花景昭摇摇手指,咧嘴露出一口白牙,“不会,你哥舍不得。”
正说着,一块湿热的巾子就从天而降,啪地甩在他脸上。
随后浴室的门开了,苏倾池换了衣裳出来,白皙的肌肤清透如脂,身上温柔的湿气夹着一股似有似无的暗香,阵阵袭来,实在诱人得紧。
花景昭的□立刻顶起一块,无声地叫嚣。
“下流。”苏宝儿嘀咕,脸上红了一片。
早些时候,天色就有些阴沉,此时更是阴得厉害,看样子怕是要下雨。
果然,不出多久,一道惊雷炸过,冷风紧凑地一卷,便扑扑扑下了雨,雨势不小。
苏宝儿趴在窗上,看着屋檐上倾泻下来的雨水,“哎,白天还好好的。”忽而想起什么似的,一拍脑门,“糟啦。”
赶紧冒着雨跑到院子另一头的架子上把酱坛子捧下来。
这雨下得又急又紧,纵是苏宝儿动作快,那一坛子的酱菜也都遭了殃,苏宝儿哀声叹气,可惜了这坛子好菜,不知道他哥知道之后,会不会臭骂他一顿。
想着,苏宝儿拍了拍身上的雨水,拿了东西把坛子里的水给撇赶紧,不晓得天晴再多晒几次,这坛子菜还能不能吃。
正忙活着,就听院外有人敲门,咚咚咚,铁环扣着木门,发出沉闷的响声。
若不是苏宝儿的房间离院门近,那声音早被淹没在这瓢泼大雨之中了。
苏宝儿寻思着是避雨的人,一时没找着蓑衣,便顶了个木盆,踩着满园的雨水,啪嗒啪嗒跑去开门。
“谁呀。”
“不好意思,这雨下得太急,实在找不着地方躲雨,小哥儿能不能行个方便,我同少爷……”
“小宝儿?!”
“商……商少爷?”
头顶的木盆哐啷一声掉在地上,发出不小的动响。
“怎么回事?”
正房的雕花房门打开,一个身着白色亵衣,肩头披了一件外褂的男子走了出来。
身后穿着同样丝绸亵衣的英俊男子单手环着他的腰。
一夜难眠
正厅之内,镂空透雕的香几之上燃着香炉,香炉之上彩绘着含苞吞吐的牡丹,枝叶缠绕扭曲。熏香袅袅,门外渗进一缕凉风,香气立刻如祥云一般缠绵缭绕于雅室之内。
说是雅室并不为过,苏倾池素来讲究,这正厅之内的每一物件都由他亲自挑选,无一不精巧雅致。
厅堂与内室之间以彩绘绣雕的花罩相隔,这花罩虽只起了门框的作用,却也耐人赏看。
内室与正厅的布置有所不同,没有那许多繁琐的物件,只在屋子中央摆了一张圆桌,四周围着四张圆杌子,一边摆放着一架花屏,里边是一张软塌。墙边挂着褐色竹制书架,小巧精致,还有镂空小门,书架旁边是一个几案,摆着一个白底粉彩的花瓶。另一边的墙壁之上则悬挂着一把胡琴。
窗外的雨噼噼啪啪击打着院中的石板地面,窗内却安静的很。
苏倾池、花景昭和商承德,三人坐在圆杌上,陆青和小宝儿坐在另一边的小凳上,两人围着一座小青炉,一边烤火一边烧水。
三人没一个开口的,苏倾池看着墙壁之上的胡琴,商承德望着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