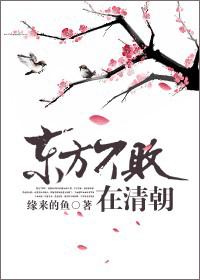穿到清朝当戏子-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沿着鼻梁滑下来,在鼻尖凝成一粒粒汗珠,滴落到地上,虽如此,他却笑得爽朗,伸手在那汉子粗实的胳膊上一拍,说下次定要将这仇讨回来,那汉子也哈哈大笑。書 香 門 第
商承恩在一旁看着,直到管队举旗喊停,方暗自松了一口气。
晚上,两人照例一个吃饭,一个洗澡,中间隔着一块羊皮地图。
苏倾池泡在热水之中,低头看了眼胸前臂上的淤青,不免抽了几口气,浑身就跟散了架似的,先去并不觉得,现在经热水一泡,这才觉得浑身都疼,有些地方破了皮,沾了热水,更是剌剌地疼。
商承恩在羊皮地图另一边只能听见几声隐隐的低吟。
起身穿衣服的时候,苏倾池险些一头栽倒,两条腿软绵绵地使不上力,胳膊也是,举起手来,手指尖还在颤抖,看来,今日是真的累坏了。
两人的床铺分别在营帐的对角,苏倾池累极了,今日也忘了替商承恩换药,听得营帐外吹了号角,便睡下了。
夜半时分,营帐之外的风更大了,整个营帐被刮得哗啦作响,动静不小,然而营帐之内却安静之极。入夜,苏倾池翻身,无意识地发出几声痛吟,过不多久,那气息渐稳,浅浅的,像一缕细软的风。
商承恩望着头顶的帐篷,思绪万千。
他还记得当日府里请戏班子唱堂会,这人一身霞帔在台上唱戏,体态风流,媚色妖娆,那一颦一笑究竟勾动了多少人的心弦?便是女子,怕也比不得他。
陌久说他是春沁园的苏老板,京城有名的骚旦,身后有无数人追捧,挥金撒银,只为博他一笑。
丫鬟说那人和他大哥关系暧昧不清。
下人说他三弟是那人的房中客,入幕之宾。
外头传言那人允了珍宝楼花老板一夜风流,花景昭才为他抛了一切。
他一直当他水|性杨花,之所以会名动京城,不过是因为他雌伏那些男人身下,以后|庭之淫取乐他们罢了,这样一个“一条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尝”,不知廉耻为何物的男人,让他看一眼都嫌脏。
原先那般厌他,如今却同他住在一个营帐之内,吃同一锅饭菜,甚至喝过同一个水囊里的水。
这人……
却再叫他厌恶不起来。
银丝
营中近日无事,兼之众士兵抱怨伙食不好,缺油水,上头便下了命令,今日抽一个营的士兵去营地东边的河里摸鱼,今晚全体开荤,此令一出,全体士兵顿时欢呼如雷。
营地东边的那条河本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却因淤泥沉积,形成了一个孤立的河滩,河滩两岸岸坡平坦,河滩有没膝的淤泥堆积,整条河河床平缓,水面宽阔,河水微绿且浑浊,除却水中有淡淡的腥味,偶尔还能瞧见跃出水面的鱼。
入营几个月,几个月不知肉味,早把一帮汉子馋得口舌发干,见到活鱼,一个个早脱了干净,一个猛子便扎进河里。
如今入夏,天气愈发炎热,众人待河里一边摸鱼一边解暑,正是爽快,葛冰也脱了个光|溜溜,在河跟条白泥鳅似的,四处扑腾,大约是他太闹了,吓跑了不少肥鱼,一个汉子一把掐住他的腰,把他整个儿举过头顶,一个使劲,粗沉地嘿了一声,将他丢出了老远。
“哇……”只听得噗通一声响,水花四溅,众人哄然大笑。
烈日炎炎,四周蝉鸣聒噪,光景十分惬意,宽阔的河滩里边一通混战,搅得河水更加浑浊,只衬得黄浊的河水里白花花一片,好不扎眼。粗犷的大汉,年轻的少年,飞跃的肥鱼,风景独好。
河水很深,成年汉子若站在河中央,恰能露出一个脑袋,胆儿大的能水的士兵纷纷跑河中央待着,水性差的则靠着岸边摸鱼,不会枭水的,就如苏倾池,便在河岸上帮着看鱼。
装鱼的竹筐如今正插在河岸的淤泥上,一半没在水里,免得那些鱼缺水而死,苏倾池就坐在岸边一块大石头上,就着树荫正好乘凉
河里的众人早忘了捉鱼的任务,一个个游水的游水,混闹的混闹,唱山歌的唱山歌。 葛冰露出半个黑脑袋,在河水里四处游动,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所经之处水纹浅动,没有丝毫声响,后来竟在嘴里含了根芦苇杆,整个人没进水里,只能隐隐瞧见河中央一截芦苇杆牵着两条细细的水纹。
苏倾池见他许久不见动静,正担心出事,那头河中央突然冒出个人来,葛冰举着手里的一条大鱼,大喊,“赵大哥,鱼,好大一条鱼。”
半游半划靠近河岸,举着那条鱼就往河岸上丢,两手叉腰,甚是得意。
果然是条大鱼,苏倾池卷了衣袖裤脚,脱了鞋袜,踩着淤泥走到河滩边将那条鱼拣来装进竹筐里,起身对葛冰挥手,“干的不错,今儿有鱼汤喝了。”
众人一听鱼汤,顿时欢呼,士气大振,一个汉子挥着黑毛的粗膀子大喝,“兄弟们,跟老子逮鱼,把鱼当杀我们兄弟的狗贼抓了,炖他|娘的几大锅。”
“好————!”众人热血沸腾。
苏倾池走到岸边,靠着石头坐下,竟是忘了两脚齐小腿的淤泥,微暖的风带着一点腥味吹过来,叫人浑身舒畅,看着河中央那帮汉子,苏倾池不由得弯了嘴角。
“怎么不下去?”身边忽而有人开口。
苏倾池转头,面上的笑容敛了两分,将视线重新转到河面上,没有说话。
商承恩方从营地后的武场练过骑射回来,马匹如今正系在一旁的树上,发出“咴咴”的声响。大约是练得时间久了,身上有些粘腻,商承恩拉了拉衣领,视线停在河中央。苏倾池靠坐在石头上,俨然已经忘记了身旁的男子,目视前方,嘴边含笑。
商承恩低头,正瞧见对方细白的手臂,以及卷到膝盖的裤腿下那双修匀的小腿,小腿上黑白分明,白的是肌肤,黑的是淤泥。
天气炎热,这片树荫斑斑驳驳,阴凉并不多少,苏倾池的衣襟微微敞了一分,从商承恩这个角度,恰瞧见里边两道细长的锁骨,浅浅的勾勒的线条,流畅之极。
商承恩别过眼去,面上不见丝毫表情。
天上正是一轮圆日,鲜红似火,照得河面都起了一层水雾,树底的阴凉下,一个倚树站着,一个靠石坐着,一个英容俊貌,一个白净清俊,虽是一身戎装,却是难得的和谐。瞧见葛冰被几个军汉玩笑地丢来丢去,苏倾池不禁低笑出声。
声音清婉,竟是难得的动听,商承恩不由微愣。
河岸上纷纷有人丢鱼过来,苏倾池起身,弯腰将裤腿卷的更高些,赤脚踩着泥沙踏入淤泥之中,恰如肌白入墨。
“可别把鱼都捉完了。”那人大笑,洗了手将袍角系在腰间,双腿修长匀称,腰身纵是有衣袍裹着,却也纤细不若男子。
天色渐晚,霞光满天,天上的蔚蓝也淡却了,被橘色染了半边天,淡妆的蓝,浓抹的橘,清风习习,一众人沿着山路哼着山野调子,抬着竹筐满载而归。
回营之后,火头军架起大铁锅,忙得热火朝天,十几条鱼下锅,热汤足料儿,大铁锅下火烧得噼啪直响,锅里浓汤烧的咕嘟嘟,滚滚地冒着热泡,勾得满营兵将的馋虫骚动,一个个没命地使劲嗅。
晚上,营帐外生了几个火盆子,众人围坐几团,中间支着铁锅,给人分了一碗鲜鱼汤,总兵又拿出了几坛烈酒,众人满上,胡吃海喝一通,整个军营又唱又笑轰轰烈烈热闹了好一阵子。
苏倾池只要了一壶酒,斟了满满一陶琬,举起对周围人道,“来,为了绿营,为了前线浴血杀敌、顶天立地的铁血汉子,是爷们儿的就跟我干了这碗。”
“说得好!干!”众人爽快地举碗,仰头灌下。
众人气血高涨,过了今夜,日后就是战死沙场,也死而无憾。
熊熊的篝火映在苏倾池的脸颊上,衬得他面色红艳,双唇因为饮酒的缘故,变得水漾红润,一双纤长的凤眸此时流光浮动,竟莫名地多了几分魅惑。
苏倾池被高涨近乎沸腾的热烈气氛感染,心中热血翻涌,白皙的双颊酡红,他舔了舔双唇,跟着众人又干了几大碗酒,末了哈哈大笑,直呼痛快。
酒是陈年的烈酒,苏倾池同众人碰碗豪饮了几碗,还没觉得什么,此时酒劲上涌,便觉燥热难耐,呼吸亦变得粗沉,吐息炽热,身体微歪,靠在身旁的男子身上,眼神微微有些涣散。
苏倾池根本不知道身旁的男人是谁,只是觉得脑子晕眩得厉害,虽如此,却依旧满腔热□薄欲出,他从没像今日这样淋漓尽致地痛快过。
面对生死未卜的战场,过去的种种纠葛,如今又算得了什么?男儿就该在马蹄炮火中抛头颅、洒热血,这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后,再回头忘一眼曾经束缚自己的重重枷锁,不过几根茧丝。
什么忘不了,什么舍不掉,等在铁血征场中热血一回,什么都忘得了,什么也都舍得了。
苏倾池仰天大笑,靠着身旁男子的肩头,举着身边的酒壶,仰头灌下,辛辣的烈酒填满咽喉,呛得他双眼泛红,砸了酒壶,望着苍墨的天际,笑着闭上眼。
商承恩一动未动,手臂上有什么湿热的东西透过绵甲渗入他的皮肤,炽热,滚烫,有一丝涩涩的滋味。
苏倾池醉了,靠着他的肩膀歪倒在他怀里,大约真的醉迷糊了,仰头枕在他腿上看着他,竟会对他笑。
那双迷人的眼眸中闪动的是什么,狂热,痛苦,迷茫。
到底怎样一个笑容,才会凄美到让人心痛。
商承恩来不及追问,怀中那人已沉沉睡去,眼角一道银丝,晶莹,清透,在火光中愈发耀眼。
粗糙的拇指贴着细腻的肌肤,缓缓将湿润抹去。
行军
方形的矮木几,不大,仅有一臂长宽,桌上摆了一碟大白菜豆腐,一盘油焖茄子,全无荤腥,这样的菜色并非一两天,近日一日两餐,除却早上的窝窝头和稀粥,竟是素菜。
这些素味菜颇合苏倾池的口味,每日将自己碗中的饭吃完,还会多添上半碗。
饭桌上,两人面对而食,没有只字片语。
苏倾池伸手夹一块茄子,要巧不巧,筷子和对面那人的默契地碰在一起,两人皆没有动作,末了,商承恩将筷子移开,苏倾池夹了茄子,将最后一口饭吃完,放下碗筷,起身取了箭囊便出了帐子。
营帐外头风声、马蹄声、脚步声井然有秩。
咻地一声,伴随着“铮”地声响,一枚枪头箭扎进箭靶,箭杆微颤,有短促细微的嗡响。弓是好弓,桦木黑漆的弓身,韧鹿皮的弦,一旁的树枝上挂着箭囊,红片金里,石青衬缎,银线革边。
苏倾池吁出一口气,伸手抹了把额上的汗,走上前去,看了眼那肩头扎进的位置,不免叹气,要说他练剑也有两月之久,百步穿杨不说,总该离靶心近些,可如今竟是毫无进步。
憋了口气,又射了几箭,只有一次命中靶心,其余全偏得不像话,大约射中的那一次也只是巧合,苏倾池皱皱眉,偏不信邪,虽然双手酸软无力,依旧举起了那把实沉的弓。“嘿!”
箭头破风而出,在空中打了个颤,险险地擦着箭靶而过。
苏倾池长长叹了口气,走过去伸手将箭从地上□,神色之间竟带了几分气恼。
“赵大哥……”
苏倾池转身,身后向他跑来的正是葛冰,待跑到他跟前,葛冰扶着膝盖喘了几口气,伸手把歪到一边的虎帽扶正,鼻尖上的汗在太阳下亮晶晶的,“赵大哥,上头有令,全营向前行进三十公里。”
“这么突然?”苏倾池动了下眉毛。
“上头讨论临时决定的。”葛冰神袖子擦了把脖子底下的汗,“看样子我们离上战场的日子不远了,赵大哥,赶紧准备准备,总兵说明儿一早就出发。”
事情说突然也不突然,金川从三十七年至今,东征西调,动用了近十万大军,花了一年多竟还没将几个小小部落的联盟攻下,这无疑是伸手在清王朝的脸上打了一巴掌,乾隆是无论如何丢不起这个脸面,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挥兵铁骑踏平这块弹丸之地。
苏倾池回到营帐,恰逢商承恩从营帐之内出来,两人抬头看了一眼,苏倾池便低头进了帐篷。
当晚全营天一黑便熄灯就寝了,苏倾池在榻上辗转反侧,大约是惦记着明日一早整装进发的事儿,睡得并不踏实,索性披衣起身下床倒水喝,摸黑找到墙上挂的水囊,取了囊袋扒了塞子,仰头刚喝了一口,冷不防耳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漆黑不见五指的营帐里,身旁神不知鬼不觉站了个人,苏倾池被吓了一跳,冷水进肺,顿时呛得直咳嗽。
商承恩大约也没料到自己一出声便把苏倾池呛成这样,一时有些愣神。
苏倾池擦了嘴,甩手就唇枪舌炮,“你当这是乱坟堆子吗,大半夜没声没息就钻出来!”商承恩被当头骂了个语塞,半日才道,“……我起来喝水。”
苏倾池借着营帐外微弱的火光瞪了这张面无表情的脸一眼,转过身去。
身后久久没有动静,等苏倾池走到床边的时候,那人忽然说了一句,“你以前就挺能说的。”
苏倾池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皱了皱眉,翻身睡觉。
天还未亮,整个川北镇标左营已经出发了。
除却本营的七百余名兵丁,另有两百匹马骡、百余挑夫、百辆民车,粮草辎重、枪箭大炮,浩浩汤汤竟是一个大队伍。
营内外委和马兵自有官马可骑乘,步兵守兵每五人配给一辆螺车,车上既装载了行装行李,自然容不得每个人都坐,只能轮流坐上去歇歇脚,其余时间便只能步行跟上大军。
人马众多,行军便不免困难,因为车上还有辎重,挑夫还抬着大炮,沿途又多是陡险山路,更是难行。
一众人马行了一整日,人疲马乏,再行不动了,上头才发话,众人在附近的树林子里搭了帐篷,就地野宿,待天亮再继续前进。
待一切妥当,已是月明星稀了,众士兵甚至没力气爬进帐篷,直接仰地就睡得横七竖八,林子里哀声遍地,只剩篝火烧得噼噼啪啪。
苏倾池也累得够呛,浑身酸痛难忍,双腿早失去知觉了,脚底原先还一阵阵刺痛,现在也感觉不到了,脱了鞋,脚底心和净袜已经粘在一块儿了,起了血泡。
讨了些热水,就着泡了脚,这才觉得身子有了些知觉,浅浅吸了口气,又长长吐出,转头正瞧见篝火边坐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挑着火里的木柴,火光熠熠,照在那人脸上,衬得对方侧脸的线条愈发刚毅,对方看着火堆不知道在想什么,眉心习惯性地拧着,这大约是他唯一的表情。
察觉到另一方向而来的视线,他微微转头,正对上苏倾池的视线。
两人对视片刻,各自转回头。
苏倾池擦了脚,觉得身上舒服了些,低头看了脱下的净袜,早已被磨破的血泡弄得污糟不堪,实在不能再穿,便从自己的军装里找了双干净的。
耳边传来渐近的声响,是靴子踩在草屑树枝上的声音。
苏倾池抬头,一个白瓷的药膏盒递到他眼前,那人沉默,没有音调的嗓音响起,“涂上,别耽误明日行军。”
说完,将药膏放在草地上,人已经转身走了。
次日天未亮,全营再次整队出发,只是这次的山路愈发陡峭,许多地方不得不砍了树木,辟出一条道来,螺车是不能再用了,只能弃了车,一切军装或由雇来的民夫挑着,或由马骡驮着,众步兵守兵只能一路徒步。
葛冰走得歪歪倒倒,好几次屁股沾到路边的石头就差点粘上去不起来了,被苏倾池拖着这才又跟上部队。
葛冰舔舔干燥的嘴唇,“怎么还不歇歇呀,我两条腿马上就断了。”
“才半天就嫌累了?”这样说,苏倾池也长喘了一口气。
葛冰哭丧着脸,眼红地盯着前边的马兵,“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马兵呀。”
“多立两次军功,你也就有马了。”苏倾池望了眼远处的山路,弯弯曲曲,有些地方狭窄难行,也不知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葛冰叹了口气,“我们没马想骑马,人家有马的反而不骑。”
苏倾池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又收了视线,没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