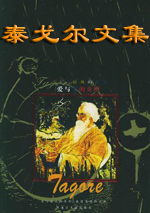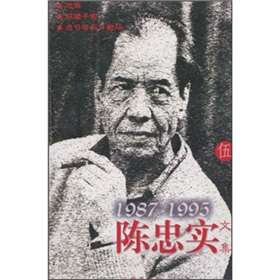石康文集-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躺下,这里背阴,地上干燥凉爽,我跟刘佳斗了句嘴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是阿莱把我推醒的,退场的时间到了,我们四个分别往更衣室走,然后在大门口集合,一同坐车回学校,我们迈着软绵绵的脚步走进校门,我和华杨不禁心情沮丧,越往前走越后悔,想想后天的考试,心急如焚,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宿舍,背起书包直奔自习室。
自习室人满为患,连座位都找不到,一些学得不错的男生在给女生讲题,趁机谈感情,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平时自习室是公认的嗅蜜场所之一,但得手的大都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学生,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那些原来在他们身边愁眉苦脸的大笨蛋这会儿会扬眉吐气。自习室门前站着几个抽烟的学生,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晃动着。我走出去时正碰上其中的一个认识我,冲我点点头,我对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向教室走去,在教室门口遇到正匆匆往外走的华杨,他说教室太乱,什么也干不了,正要奔自习室,我告诉他自习室连他妈位子都没有,我们俩只好奔图书馆而去,图书馆里也是爆满,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从哪里变出来的,一个个的占住自己的那个坑纹丝不动,像从地里钻出来的根茎植物,呆头呆脑地埋头书本,一片叫人感动的学习景象。我们拎着书包,经过这么一通折腾,都泄了气,身上粘乎乎的,
尽是些不争气的虚汗,正是下午3点多钟,视力所及,到处是白晃晃的一片,头昏沉沉的,脚下却轻飘飘的一点根也没有,从图书馆往宿舍走的路上,我们俩脚步迟缓,没精打采,手里的书包加倍沉重,里面装满了这个夏天里所有的绝望,回到宿舍,我们各自跃上自己的床,分别以自己恶梦中最难看的姿势睡去,真的睡去了。
105
我还是讲讲我和华杨是怎么混过考试的吧,这源于焦凡的一句话。晚饭前,这个傻逼从外面进来,不小心踢了地上的脸盆一脚,于是我被吵醒了,华杨也应声而起,弄清情况后不禁破口大骂:〃你丫干嘛呢!〃
焦凡对这种粗暴态度早已习以为常,因此不慌不忙地收拾他的饭盆儿,出去时对华杨笑着说:〃真他妈的难,就是有卷子都不一定过的去。〃
说完,他故作摇动饭盆儿,让里面的破铝勺儿发出阵阵怪响,那个铝勺儿我见过几次,被他的利齿几乎咬成小铲儿,勺把儿七拐八拐,勺前端几个细小的死角上沾着牙垢,连当掏耳勺都不够格,他却不当回事,这家伙明知道华杨什么都不会,所以故意摆出一副轻松样,以为能叫我们心里不好过,他说完那句危言耸听的话后,得意扬扬地出门而去,叮叮当当地消失在楼道中,这时我头脑中灵光一闪,把头抬起来,对华杨叫道:〃谁说有卷子不一定过的去!〃
华杨起初没有听懂,片刻反应过来,冲我一笑,接口道:〃要是有卷子,就一定能过去!〃
106
半夜12点,教师楼的最后一盏灯灭了,几个青年教师从楼门口出来,不久,一个校工过来锁上楼门,然后沿着花园边上的一条柏油马路向另一座楼的值班室走去,这个过程刚好能被躲在学校花园里的我看到、花园里静悄悄的,我和华杨弓着身后退几步,长出一口气,依次躺在学校花园的草地上,虽然出来时抹了防蚊油,我的脸上还是被蚊子咬了一个包,头上是映在夜空里的树冠的黑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叶子缝隙中有时会透过几点星光,倏尔就被摆动的树叶湮没了。暑热被风搅动着,缓缓飘上天空,草地就如同一个被太阳练了一天的婊子一样酣然睡去,体温渐渐消散,皮肤重又变得光滑凉爽。贴近地皮,似乎能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一股湿湿的甜味在草尖上凝结,化解了土地里的腥味儿。
华杨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的瞬间,我看到他脸的轮廓,什么表情却看不清楚,我已经抽了半盒烟了,喉咙里直发干,校园里还留有那么几声零星的声音,脚步声,说话声,关窗子声,自行车的轧轧声,这些声音不时传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越来越小,突然,在那么一刹那,一切都中断了,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风擦过高高低低的植物所带来的自然的音籁,这种寂静从某一刻起就一直持续着,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也听得见华杨的心跳声,夜里,我们俩的双眼闪闪发亮。
〃像什么?〃华杨问我。
〃什么像什么?〃
〃我们俩现在。〃
〃电影里的两个中国侦察兵。〃
黑暗中华杨笑出声来。
〃走吗?〃他对我摆摆下巴。
〃再等会儿,还早呢,我想再渗会儿。〃
〃怎么了?〃
〃没怎么。〃
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口香糖,撕开上面的锡纸,放进嘴里吃了起来,华杨捅捅我。
〃什么?〃我问他。
〃别吃了,听着不舒服。〃
〃真的?〃
〃真的。〃
我吐出口香糖,他长出了一口气,仰面朝天,双手垫在脑后。
〃别紧张。〃
〃没紧张。〃他小声说。
我随即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摸索,不久,掏出一张垫板来,那是我下午从家里火速取来的,是一张天蓝色的垫板,即使隔着几万重的夜色我也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是天蓝色,为了买这块垫板,我曾和父亲大吵一顿,原因是父亲买了一个红色的,可当时我就是喜欢天蓝色,父亲实在拗不过我,于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找这块垫板,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是个人人称道的懂事孩子,但也有极其固执的时候,虽然那种情况很少发生,可发生一次就能把全家弄得团团转,
我8岁时已经学会各种狡猾伎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让父母最头疼的办法,比如,我会故意装做去上学,实际上,我只是走到学校门口,然后直接折回家,在我们家楼下转悠一天,直到父母下班,才装做若无其事的放学回来,这种事我知道不会持久,果真,老师来家访,这时父亲就会问我到哪儿去了,我就死也不会说,叫他们胡乱猜疑,终于,在父母快撑不住的那一刻,我才告诉他们我的要求,这样要求便会立即得到满足,于是我又变成原来的好孩子,一切正常。这块垫板就是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我记得它是在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买到的,我在几块颜色和式样都相同的垫板中间挑了很久,一直挑得售货员和父亲都不耐烦了才算挑中这块我认为颜色最正的,很久以后,我对自己那一时期如此偏重于蓝色这个问题大惑不解,现在,无论是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白色在我眼中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我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情感,无法想象当时父亲买错垫板颜色这一事情如何叫我愤怒和难过,一切成了过眼云烟,无从追忆,无从理解。这块垫板很长时间内成了我喜欢的一个玩艺儿,我甚至用它来代替尺子,也当做扇子用过,考试时把记不住的东西用削得尖尖的铅笔抄在垫板的一面,当然,如果老师发现,我只需用袖子顺手一抹证据便荡然无存。上初中以后,很少有人再用垫板了,可我用,垫板垫在纸下,钢笔在上面轻轻滑过,字写的又小又快,这个习惯直到改用圆珠笔时才被丢掉,但是垫板一直留在我的抽屉里。
那天夜里我差点给华杨讲那块垫板,但我最后还是忍住没讲,我还决定了不对任何人讲这块垫板,我用手把它重又装回我那个大得要命的上衣口袋,华杨忽然坐起身来,我伸了一个懒腰,也跟着坐起来,华杨对我说:〃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老是在想保罗西蒙那首《寂静的声音》,咱们看《毕业生》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刚才这首歌的旋律就是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一遍遍地回响,我真想回宿舍去听一遍这首歌。〃
〃弄到卷子咱们去我那儿听,可以听一夜。现在,咱们还是走吧,一点了。〃
我们站起来,一人嘴里叼一支烟,从小花园边上的柏树墙上跳出来,拐上柏油路,一直走到教师楼的后面的空地上,这里平时没人来,杂草丛生,草丛里积着厚厚的从教师楼窗户里扔出来的垃圾,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傍晚时我们来过一趟,所以也没费多大力气就走到从左边数第三个窗下,那是一楼的男厕所,窗子的插销已经被华杨弄开,我踮起脚尖,用手一拉窗子外面的把手,窗子吱地一声开了。我立刻翻了进去,身上蹭了不少窗台上的土,我蹲在窗台上,把华杨拉上来,我们依次跳到地上,厕所的门半开着,可以听到走廊里的动静,我们先站在门边,侧耳细听,楼道里安静得出奇,我们又等了一会儿,见无异常,于是从容地从厕所内闪身而出,贴着墙壁向前悄无声息地前进,等上到二楼时我们已经走得大摇大摆了,眼睛也适应了楼道内的黑暗,我们上到四楼,沿着楼道一直走到顶头,在一扇上面标明打印室的门前停住,华杨拧亮手电,我把垫板插进门缝,顶在正对着撞锁舌头的部位,再用力向前顶住,华杨把门向前一推,再往回一拉,啪地一声,门开了,我和华杨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用力一握,然后走了进去,我走到窗前,把窗帘一个个拉上,华杨把碍手碍脚的椅子搬到一旁,然后再次拧亮手电,但见桌子上和地下到处是一摞摞的卷子,有的已经卷成一卷儿,包好,靠墙立着一个保险柜,我过去抓住把手轻轻一拧,竟是开的,华杨已经开始在卷子中找了,我因为没有手电,只好静静地坐在一张写字桌边,看着华杨在那里东翻西找,不时小声说一句:〃又一门!〃
我问他:〃几门了?〃
〃咱们班的还差一门,就是后天那一门,你找吧,就差那个保险柜了。但你媳妇儿她们班的都齐了。〃
我从他手里接过手电,在保险柜里一摞摞卷子看去,终于在第二格找到了,我把最上面一份拿出来,把保险柜关好,交到正在桌边整理的华杨手里,华杨把它们摞起来折好,然后我们一同把现场恢复原样,关上门,化成两股黑烟儿溜出了教师楼,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大学考试带
142
6月中旬,我突然收到陆然的来信。
陆然的一摞信是通过他父亲转给我的,夹在一个大包裹里从海南寄过来,包裹里还有一些书和生活用品,信用一个大牛皮纸口袋包着,上面写着〃请转交周文,电话是4261359〃
,字迹零乱不堪,据他父亲说,他已经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他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取那个牛皮纸口袋,他并没有拆开,只是叮嘱我,如果里面有什么陆然的消息请及时转告他,他们一家都很惦记他,他父亲为了找陆然曾经去过一趟海南,查遍那里的所有旅馆也没找到他。
143
下面是陆然的信。
周文:你好。
〃告诉我,幸福的开端在哪里?〃我这么问自己,那是我走在一条田埂上所做的胡思乱想,两旁是刚刚收割的秋天的稻田,目光的尽头都是金黄金黄的颜色,田里有一些拾麦穗的农家小孩,他们远远地用好奇而羞涩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衣服裤子不管原来是什么颜色,现在看上去一律呈土色,田里还有成群结队的麻雀,它们时而远远地飞去,一会儿又飞回来。但距离我和孩子们都很远,刚一走近,它们就一轰而起冲向天空,我还看到一只田鼠,它长着灰溜溜的皮毛,但跑动起来迅捷无比,一闪就从一条田埂间溜得不见了踪影。田里东一堆西一堆地摆放着许多稻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土地和谐地接触着,仿佛它们不是人工堆放的,而是天然就长在那里的。现在是上午,阳光把我从一堆稻草中叫醒了,我的表早就停了,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时间,昨天夜里,我就把自己陷在稻草里,彻夜未眠,我望着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注视着那一颗颗神秘莫测的星星,星星多得无法计数,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只要你盯住一个地方仔细看,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星星,直到你眩晕,眨一下眼,立刻,它们都消失了,是的,你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星星,我知道,我看到的都是几百万光年前的幻影,至于它们现在怎样了,我说不上来,但有一阵儿,我确实眨着贪婪的双眼在吞噬它们,这些不可琢磨的幻影,这些可望不可及的光芒,它们像我们一样在宇宙里飘荡,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因由和结果,我想着它们,看着它们,直到觉出稻草里的潮湿,忽而,我又想到美丽的村姑,我把头钻出草堆,希望她们之中的谁会来和我约会,后来我觉得有些饿了,终于朦胧睡去,清晨我曾醒过一回,但四周太静了,我很快又睡去了。
我设法靠近那些小孩,向他们问路,并试图让他们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吃的,他们起初默不作声,像是不懂我的意思,但轮到他们说话时,我又糊涂了,因为我一句也没听懂,不过,没用多久,一切都解决了,我被领进村子,现在我写这封信就多亏了其中的一个小孩,他把我领到他们家,我吃了东西,于是,我又想到那个奇怪的问题:〃幸福是从哪里开始的?〃我想我现在就有了一个答案。因为我寻找了很久,走了很多地方,但我知道,我的答案不久就要改变,从我现在过的流浪生活所提供的经验告诉我,我已经找不到确定的东西了。
记得吗?我们曾经疯狂地主张毁灭一切,毁灭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一切,现在我懂得了,我们什么也毁灭不了,除了我们自己,你要是像我一样在旷野里呆过你就会懂得,这山、这水、这大地,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你会有这种感觉,它们永远长存、实实在在,分量沉重,不可改变。
以前,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包括那些曾经的我们、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是一些怀着梦想,扇动着破烂的翅膀妄想飞到云端的傻瓜,是一些特别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们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几个,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就在刚才,我吃了饱饱的一顿,两碗米饭,一盘咸菜,现在我想睡觉了,虽然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但是,我还是睡吧,因为油灯已经快用完了。
144
这是另一封信。
周文:
我无法收到你的消息,我没有地址,我在奔波,在寻找,毫无目的,以前我以为自己是在找生活的秘密,我在观察别人的生活,我在天空和土地间制造我的幻想,但是我错了,我发现了很多东西,每一次都令我兴奋,但不久,我感到我发现得越多我反而越痛苦,因为世界的秘密随着每次发现反而距我越来越远,也许它就埋藏在我身边,而我却无法触摸。
刚刚我写了一首诗,讲的是关于一只死在沙丘之巅的美人鱼,我写到它神秘的死,写到了泥土之中的爱情,那些在岩浆之中紧紧拥抱的情人以及他们石化了的接吻和深沉广阔的激情,我写了泥沙之中留下的泪痕和开在泥沙深处的花朵,那些年代久远却和我们并存的灵魂……写到这里我不禁想,也许我真是个疯狂而过时的浪漫主义者?
这片树林就坐落在村庄旁,不久以后我就要到达那里,并从那里接近城市,我就在这树边给你写信。
到处都很潮湿,露水把一切都弄得生机勃勃,美丽清新,这露水要到下午才能完全褪尽,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处在一种亢奋而疲惫的状态中,一直十几天了,我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