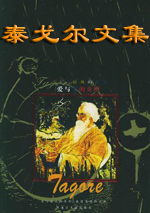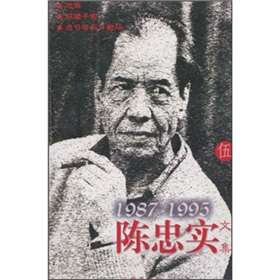石康文集-第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时期,也门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无疑也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和文化接触,但实际上,犹太人定居阿拉伯南部的数百年以前,在埃及已经建立了几个人数相当众多的犹太人定居群落了。因此,考虑到法拉沙人的宗教还带有浓厚的《旧约》宗教特点,我们便可以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了:犹太教必定是通过一种〃文化融合〃的渐进过程,从埃及向东南而传入埃塞俄比亚的。
确切地说,没有任何绝对不容置疑的史实能把法拉沙人和埃勒法坦岛连在一起。然而,我的确发现了大量引人入胜的线索,而我认为它们已经强烈地暗示出了这个联系。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其中没有一个能够证实我的理论,即约柜先在埃勒法坦岛的犹太神庙放置了200年,后来在公元前5世纪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不过,综合考虑了我(在以色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了解到的所有背景资料以后,我的最新发现却显示出了一种更令人信服的不同面貌。
以下是我得出的主要结论及其证据根据:
1.埃勒法坦岛的犹太居民实行燔祭,并且在约西亚国王推行改革后依然长期坚持,这个情况的确非常有意义。犹太教在埃塞俄比亚很古老,其证据之一就是法拉沙人的宗教具有极其古老的特征,而埃勒法坦实行的燔祭则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证据使一个假说更有分量,即法拉沙人是来自埃勒法坦的犹太移民的〃文化后裔〃,因此它也有力地支持了一个命题:约柜可能就是从那个岛被带入埃塞俄比亚的。
2.在埃勒法坦犹太神庙的黄金时代,它具有自己的一套祭司体系。在那种没有无音的纸草书语言当中,这些祭司被称为〃khn〃;将元音a和e加进这个字以后,它当然就成了〃kahen〃这个字。法拉沙人的祭司也叫〃kahen〃。
3.埃勒法坦的犹太神庙有个名字,叫作〃msgd〃,意思是〃跪伏之地'。今天,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既没有犹太教堂,也没有神庙;不过,他们还是把他们那种简单的圣所称为〃Mesgid〃(这是在msgd中插入元音e和a之后构成的)。在这个背景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所罗门王当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祷告的时候,确实是〃屈膝跪着〃的(见《旧约·列王纪上》第8章第54节)。
4.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在耶路撒冷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说,一个〃外国国王〃在大规模拆毁埃及人神庙时,留下了他的祖先〃在阿斯旺〃建造的那座犹太神庙:
他却没有拆毁我们的神庙。埃及人看见只有犹太人的神
庙没有被毁,就怀疑我们和入侵者站在一边。正因为这个理
由,埃及人就开始反对我们,毁掉了我们的神庙,而我们不
得不逃亡。
公元前525年,一位外国国王的确入侵过埃及,也的确拆毁了许多神庙。他的名字叫坎彼塞斯(Cambyses),是扩张成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波斯帝国是他的父亲居鲁士大帝建立的。埃勒法坦纸草书上有关于坎彼塞斯的记载:
坎彼塞斯侵入埃及之后,他发现了这座(犹太)神庙。
他们(波斯人)拆毁了埃及的所有神庙,但谁都不曾损坏这
一座。
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在这个时期里,埃勒法坦的犹太人和波斯人密切合作。波斯人的保护被彻底驱除之后,岛上的犹太神庙才被拆毁。因此,拉斐尔·哈达尼讲述的这个民间传说具有确凿的历史依据。
5.哈达尼还说,法拉沙人特别崇拜塔纳·奇克斯岛。我听说,公元前5世纪时约柜曾被送到这同一个岛上。不仅如此,我在这个岛采访过的基督教神甫梅米尔·菲塞哈还告诉我:约柜被藏在岛上的〃一个帐篷里〃,藏了800年,然后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塔纳·奇克斯岛上用帐篷(或叫会幕)掩藏约柜,我对此毫不吃惊。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把约柜带到该岛的那些犹太人,其在埃勒法坦岛的神庙想必刚被破坏不久,他们也应当知道所罗门圣殿当年被尼布甲尼撒烧毁的历史。他们很可能做出了决定:从此永远放弃正式的神庙,回到荒野流浪的纯粹传统上,那时的约柜就被放在帐篷里。
6.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拉斐尔·哈达尼告诉我,法拉沙人的祖先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前,不仅路过了阿斯旺(即埃勒法坦),也路过了莫罗,〃在那里住了一段不长的时期〃。1990年1月,我在安波博尔村采访法拉沙祭司所罗门·阿莱姆时,他也提到了这两个地方的名字。莫罗的废墟被湮没在历史中1500多年以后,终于又在1772年重见天日了。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发现莫罗废墟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参见他的《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1790年爱丁堡版,卷4,538…539页)。
逃亡者之地
我感到,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发现古代莫罗遗迹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布鲁斯,这一点更激起了我加快考察进程的的热情。
我可以断定,当年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史诗般的埃塞俄比亚之旅,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约柜的下落(参见本书第七章)。因此,他找到了传说里莫罗城的遗址,这太合情合理了。当年,约柜在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途中,就曾经路过了莫罗城。
可是,约柜当年果真路过了莫罗吗?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当年离开该岛后,为什么要带着约柜向南方迁移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例如去以色列)呢?
我发现对这个问题大概有几种答案,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没有约柜的生活。所罗门圣殿早已不存在,一座新圣殿(即第二圣殿)已经建了起来。何况还有一批戒备心很强的祭司们管理着第二圣殿,他们自然不会欢迎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竞争者。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提供的那种神学思想氛围中,埃勒法坦的犹太人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宗教思想已经向前发展,人们不再认为上帝是半带肉身的神,因而也不再认为上帝住在〃二基路伯之间〃;那种约柜占据核心位置的崇拜形式,也已经大都被放弃了。
因此,约柜的回归将会引发许多潜在的灾难性难题。埃勒法坦的犹太教祭司们很清楚:为了避免这些难题,他们应当远离耶路撒冷。但又到何处去呢?他们显然不能继续留在埃及,因为埃及人已经在处处和他们作对,还拆毁了他们的神庙。同样,从埃及北方离开埃及,这条路也很不安全。所以,合理的出路只能是向南走。
阿斯旺和埃勒法坦的总督又被称为〃南部诸国大门的总督〃,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把约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只需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直接进入〃南部诸国〃就可以了,而南部诸国又被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当时指深色皮肤的人所居住的所有地区。
这些犹太逃亡者去埃塞俄比亚,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到一片可怕的〃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上冒险。相反,有直接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群体的一些成员就已经到南部诸国参与军事冒险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几个有据可查的先例,说明历史上外邦人曾向埃塞俄比亚迁移,那些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但他们数量众多,都来自阿斯旺地区,并在〃南部诸国〃定居。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说,乘船沿着尼罗河经过埃勒法坦岛再向前走四天,河中便不能通航了:
因此你必须上岸,沿着河岸走40天,因为尼罗河中有尖利的岩石,还有许许多多的暗礁,船只根本无法通过。在这个国家里跋涉见天之后,你会再度登船,在河上再走上12天,然后你便会到达一个大城,其名为莫罗。据说,此城乃是全埃塞俄比亚之母……从该城再乘船向前走同样长的一段路(即从埃勒法坦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母亲之城的距离),你便到了〃逃亡者之地〃……所谓〃逃亡者〃,乃是撒关提库司国王(Psammetichus)时期的24万埃及士兵,他们反叛埃及人,站到了埃塞俄比亚人一边。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人当中定居后,埃塞俄比亚人便逐渐被文明化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埃及人的举止。因此,尼罗河出了埃及之后,沿水陆及陆路走四个月路程所流经的土地,便是个已知的国度。若加在一起计算,你将发现:自埃勒法坦沿尼罗河旅行四个月,便可到达我方才提到的那个〃逃亡者之地〃了。(希罗多德:《历史》,D·格林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我前面已经说过,来自埃勒法坦的大量〃逃亡者〃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我没有找到相反的证据。但是,希罗多德说得很清楚,那场大逃亡发生在撒美提库司二世法老时代(公元前595…589年)。因此,我从一份无可挑剔的资料上看到〃犹太人被派去充当撒美提库司军队的援军,当时这位法老正和埃塞俄比亚国王作战〃(B·波腾在他的《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一书中引用的〃阿里斯蒂司书信〃,见该书第8页)时,便感到格外高兴了。根据这个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史实,说〃那些逃亡者里可能有一些犹太人〃,这似乎井不算不合理。
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一个方面使我兴味盎然,那就是它特别提到了莫罗。按照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的说法,法拉沙人的祖先当年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曾经路过莫罗城。不仅如此,希罗多德还相当详细地描述说:要从莫罗再乘船航行足足56天,才能到达那些〃逃亡者〃居住的地方。如果沿着阿特巴拉河航行,那么,当年那些旅行者便一直可以到达现代埃塞俄比亚的边境,甚至可能越过边境。阿特巴拉河在莫罗城以北汇入尼罗河,而特克泽河则汇入阿特巴拉河。
希罗多德的记述写于公元前5世纪,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如果有一群抬着约柜的犹太人打算从埃勒法坦岛逃往南方,那么,他们便可能路经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一直抵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不仅如此,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还可以知道:阿比西尼亚高原很可能就是吸引着他们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气候凉爽,雨量丰沛,而在他们眼里,与苏丹的荒漠相比,那里的苍翠群山想必如同一个伊甸乐园。
在古实河外
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逃亡者,是否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荒野那边的花园〃呢?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向南方逃亡时,不仅穿过了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且曾向一块特殊的土地前进,因为那里住着他们的亲族,住着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同的人?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找到了证据,它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而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犹太人就可能已经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这个证据的一部分来自《圣经》。我虽然知道《圣经》里使用〃埃塞俄比亚〃时并不一定就是指现在叫这个名字的国家,但我也知道:《圣经》中使用这个字时,有时的确指的可能就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前面已经说过,〃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在一些最早的希腊文《圣经》版本里,希伯来文里〃古实〃(Cush)这个字被翻译成〃埃塞俄比亚〃,并且(像一位杰出的权威指出的那样)用来指〃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E·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与(圣经>》,第6页)。这就是说,《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也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也许不是。同样,《圣经》的一些英译本上恢复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其含义也是如此:它或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或许不是。
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一提:《民数记》的一个可靠的古代版本上说,摩西娶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子〃为妻(参见《旧约·民数记》第12章第1节,中文神版《圣经》上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译者注)。此外还有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的一则奇特证言(它和一些犹太传说一致),它强调说:先知摩西在他40岁到80岁之间曾在〃埃塞俄比亚〃居住过一段时间(见卜约瑟福斯:《犹太古迹》,1978年伦敦版,卷4,第269…275页)。
《圣经》里还有一些段落提到了〃埃塞俄比亚l古实〃,但其中许多和我的考察没有关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相当引人入胜,并使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圣经》作者们的头脑里想到的并不是努比亚或者苏丹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非洲之角的那片山区国土,我们今天称它为〃埃塞俄比亚〃。
我对其中的一段经文已经能很熟悉,它在《创世记》第2章里,其中提到了从伊甸园流出的那些河流:〃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参见第13节,中文《圣经》将〃埃塞俄比亚〃译为〃古实〃——译者注)看一下地图,我立即知道了青尼罗河很像这条基训河(Gihon):它从塔纳湖奔流而下,河道形成了一个大环,的确〃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不仅如此,我此前还知道:被看作这条大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把它们称为〃基雍河〃(Giyon)。
另一段有趣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的第68篇里,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希伯来圣经》副教授J·D·莱文森认为〃它是以色列诗歌最古老的篇什之一〃。这篇赞美诗包括了对约柜的神秘暗示,还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预言:〃埃塞俄比亚不久将向神伸出她的双手。〃(参见第31节,中文《圣经》译为〃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译者注)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被如此看重、被说成皈依以色列宗教的潜在人选者呢?
遗憾的是,这首赞美诗里没有任何词句能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先知阿摩司(Amos,他的传教期是公元前783…743年)后来写的一段经文里,却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l古实曾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它使这个遥远国家的居民被与以色列人一起并列为〃上帝的选民〃。同一段经文(即《旧约·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有3种英文翻译,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意思: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
(中文种版《圣经》译文)
Are ye not as children of Ethiopians unto me,O children of Israel?saith the Lord.(《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Are no you and the Cushites all the same to me,son of Is…rael?…it is Yahweh whospeak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Are not you Israelites like Cushites to me? says the Lord.(《新英语圣经》译文)
我知道,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这句经文,那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已经没有资格让耶和华继续对他们特殊看待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句经文,其含义便显豁得多,但仍然需要仔细斟酌。
在公元前8世纪阿摩司宣讲预言的时期,是否可能已经有一批希伯来移民向南穿过埃及,进入了阿比西尼亚高原呢?我承认:这个推测极为大胆,而且没有证据。但是,阿摩司说到〃埃塞俄比亚(古实)〃的时候,在它可能所指的那一大片版图中,只有一个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