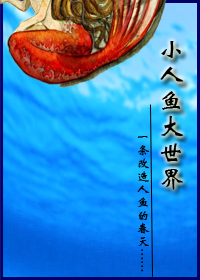世界主宰-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您支票。”
“谢谢您。”
“又来了!您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当主人呀?”
埃尔莎走出办公室,把支票递给戈特利布。
“给您20万的支票……”
奥斯卡尔·戈特利布激动不已,哆哆嗦嗦地接过支票,千恩万谢不说,还连连致歉。
“别这么客气啦,”埃尔莎不好意思地答道,“您还是跟我说说您到底出了什么事吧,庭审之后您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又坐下来。
“我害病了……得了一场病,是的,得了一种非常古怪的病。我从法庭里出来,突然感到又羞又愧,不敢见人……怕在人前露面……您是知道的,庭审进行当中,许多报纸上都登了当事人的照片。所以我觉得,每个过路人,每个过路的车夫,甚至连那些小孩都对我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瞧瞧那个人,就是他被哥哥剥夺了继承权,因为他干了不体面的事!’由于谁都不知道这件不体面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想怎么猜就怎么猜:或许我犯了伪造罪,在票据上伪造我哥哥的签名;或许我想毒死自己的兄长。我只好溜之大吉啦……”老头儿叹了一口气,“是啊,小姐,我这段时间里吃了不少苦……我其实并没逃远。人们满世界找我,可我就躲在这个城市里。我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住在一个老朋友,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如果您泄露我的行藏,哪怕只告诉一个人,我就自杀。’我当时这么对他说道。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说这个,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卖我的。”
“对不起,可我想问一声,”埃尔莎笑道,“您就不羞于见这位朋友么?”
“不!还有件奇事,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地址,却凭着一种难以解释的灵感找到了他家……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就到了……更为奇怪的是,我和那位朋友已经多年不见,连音讯都不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工夫去找他,看他,而这回他竟像我们事先说好似的那样接待我。‘啊,你来啦,’他只随口说了这么一句。我就在他那儿住下了。但我却一直有一种又羞又怕的感觉。到了晚上,我有时似乎觉得自己恢复了正常,甚至想第二天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是一到深夜,我又感到极度的恐惧,羞愧难当,我吓得连头发根儿都立了起来……就像中了一种什么魔法似的!我紧紧地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蒙起来,一动都不敢再动。到了第二天早晨,连到餐室吃饭都不敢去,只好推说头疼。我把我住的房间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
“这可真奇怪……”埃尔莎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天天看报,手脚冰凉地注意着人们究竟到哪儿去找我的消息,以防万一。令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都找错了方向。这些日子里我只笑过一次:那就是我在报上看到,有人在阿根廷——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找到了‘我’!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了。那个‘我’也是个农场主,也到城里去办事。从报上登的照片来看,他长得还真像我。”
“您这种状况持续了有多久?”
“恰好到终审法院做出对您有利而不可更改的最后判决为止。那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于是我就回到家里,一直安安稳稳地住到收到拍卖通知那天。我当时认定,只有一个人能够救我……”
他没能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绍尔和埃玛·菲特两人进屋来了。戈特利布急忙起身告辞。
绍尔和埃玛的盛装叫埃尔莎吃了一惊。绍尔穿着燕尾服,埃玛是一身雪白的衣裙,胸前别着一束白花。两个人都是喜气洋洋。
绍尔挽着埃玛的手臂走过来。
“格柳克小姐,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埃玛·绍尔。祝贺我们吧,我们结婚啦!”
埃尔莎脸色发白,站起身来。
埃玛想扑过去亲吻她,但一见埃尔莎的窘态,就犹豫不决地站住了。埃尔莎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冷冷地吻吻埃玛,便向绍尔伸出手去。
埃玛陶醉在幸福里,根本没注意到埃尔莎冷冷的神情。她像个孩子似地把双手在胸前一叉,絮叨开了:“这个奥托呀,”她的眼睛亮闪闪地瞥了丈夫一眼,“可真好笑,昨天我跟他在剧院里看着看着戏,突然之间他说什么:‘现在我该跟您结婚啦。咱们走!’”
“于是你马上就答应啦?”埃尔莎问道。
埃玛做了个可笑的怪样,那意思再清楚不过:“谁能拒绝好事儿呢?”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没等到戏演完,虽说那出戏挺有趣……天哪,我竟忘了它叫什么啦!……不过反正一样,爱叫什么叫什么呗……我们坐上车去找牧师。奥托简直就是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的!那个老头儿好玩极啦,睡得稀里糊涂的!他不知叨咕了些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完事大吉!您不生我气吧,埃尔莎?”她突然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埃尔莎见她还像个孩子般的稚气,脸上不由掠过一丝笑意。这时,她已经是诚心诚意地拥抱着女友,亲吻她表示祝贺了。
“难道能生洋娃娃的气吗?你不是感到幸福吗?”
“幸福死啦!”埃玛应道,连眉尖儿都耸了起来。
可是,当埃尔莎把目光转向绍尔,脸上不由笑意全消。她看见绍尔正含情脉脉地凝视埃玛。
“不,这桩婚事根本不是绍尔对我的报复。”她暗自想道,“绍尔对埃玛是一片真心……中了魔啦。中了魔法!这话是谁说过的?对了,是奥斯卡尔·戈特利布……是他说的:中了魔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觉得我的思路又乱起来了呢……”
“啊哈,好一对新婚佳偶!”施蒂纳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路,他正站在办公室门口。
“他已经知道啦?”埃尔莎暗暗吃惊。
她不想再看一次道喜的场面,尤其是当着施蒂纳的面,就悄悄走了出去。
“恭喜,恭喜。”施蒂纳乐呵呵地说道。
绍尔也欣喜异常地同施蒂纳紧紧握手。往日的敌意已经踪影皆无。
“我们打算今晚出发去旅行结婚,”埃玛说,“您和埃尔莎不会反对吧?”
施蒂纳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马上亲切地朝埃玛笑笑。
“当然不会,这还用说吗,漂亮的洋娃娃,你们想去哪儿呢?”
“去尼斯或者去挪威,还没定呢。奥托想去挪威,可我想去尼斯……”
“这么说,你们是想各自单独进行旅行结婚啦,”施蒂纳笑着说道,“现在在挪威能把您的小鼻子给冻掉!”他接着说,“您得疼她呀,绍尔。你们当然要去尼斯!”
“好啦,再见吧,我们该收拾上路啦!”埃玛一把抓住丈夫的手,把他向门口拖去。“快点儿嘛,快点儿嘛,奥托,你总是这么磨磨蹭蹭!我敢肯定,同你一块儿坐火车,准是走到哪儿误到哪儿!”
绍尔住在旁楼,那儿有他一套面积不大,但十分舒适的住宅。
两个年轻人嘻嘻哈哈跑进门来,开始急急忙忙地收拾行李,而且嘴里一直没住声。
“说定了,到尼斯去?”
“这有什么,去尼斯就去尼斯。”
“我的天哪,这一切太快了,像赶着去救火似的!……这箱子可真沉!……”
“我们也可以不去……得把箱子里的书拿出来……你把梳妆盒递给我……”
“不去?你是不是疯啦?我们当然得去!可路上的衣服呢?……”
“半路再买吧。你先穿那件灰的,也挺漂亮。”
他们坐在地板上的大箱子前,开始从里面往外挑书。
突然, 他俩都呆住了,就这样过了有1分钟,仿佛在凝神谛听某种思绪,接着就惊奇地互相瞧了一眼。
“我们像中国泥人儿一样坐在地上干什么?”埃玛终于问道,“你干吗把这个箱子拖出来?要出差吗?”
“我根本没打算去什么地方呀,”绍尔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干吗把箱子拖出来。也许,是你想看看这些书?”
“看书?看这些无聊的书?我们真蠢!我们这是幸福得发昏了呀!”
她清脆地发出一串笑声,一骨碌爬起来,跳过箱子,开始亲吻绍尔。
绍尔皱起了眉头。莫名其妙地把箱子拽出来这件事儿使他十分纳闷。
“怎么,生气啦?对我不满意?”说完,她故意使劲把脑袋一耷拉,绍尔不由笑了。
“当然不满意,”他笑着说道,“你还没搬到我这儿,就已经把一切给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发誓, 这不是我弄的! 是它自己跑出来的!”埃玛翘起脚踢了踢箱子。“躺着别动!别乱动啦,乖乖!你倒是来帮一把呀,等着看笑话呀!”
埃玛和绍尔把箱子塞到了床底下。他俩谁也没再想起旅行的事来……
第十二章 傍晚6点
“别忘了, 埃尔莎,明天就是星期天啦。傍晚6点我就要听到您的答复。这会儿我出城去办件急事。不是夜里就是明天一早回来。再见吧!”
施蒂纳走出冬园。
只剩下了埃尔莎独自一人。但她并没有考虑答复的事:她的心思全在另一件事上。绍尔同埃玛·菲特突然结婚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她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她感到自己从来没这么孤独过。
金鱼缓缓地在鱼缸里游来游去,一转身鳞片就熠熠闪光,柔软的尾鳍平稳地摆动着。
埃尔莎羡慕它们。这些金鱼同她一样,都被囚禁在玻璃箱子里。然而它们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却有自己的玩伴,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疑虑重重,会让人不得安宁。她此刻觉得自己比往日干活糊口时更加不幸。财富到底给了她些什么呢?
一场颇为可疑的诉讼案和亿万财富,从此就使她脱离了芸芸众生,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高兴逛街就出门,高兴看电影就上电影院。可是,她每次出门都会招人眼目,有成千的人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于是她再不出门。她若是想开开心,有什么能办不到呢?可偏偏她就失去了普通人的一切欢乐。只有一层透明的玻璃墙把她和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隔开,然而对她来说,这竟然是一道不可克服的障碍。她痛苦地低声叹息:“我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
这时,时钟开始打点,沉闷的钟声同昨天,同前天,同好多天以前一样,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楼下什么地方传来轿车马达的声音,这是施蒂纳走了……
施蒂纳!明天得给他答复。她意识到这就是最后的期限。
“为什么非得给他答复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奇怪,施蒂纳走后她的思路便开始愈来愈清晰。
如同拨云见日一般,往事出现在她的眼前。奥斯卡尔·戈特利布,他害的那场酷似“中魔”的病;绍尔对埃玛的爱是那样的古怪和突如其来,也像是中了什么魔法……
自从卡尔,戈特利布去世之后,她周围的人的举止全都变得那么荒唐,既不合逻辑,又自相矛盾,如果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不就像是中了魔么?对呀,“中魔”这个字眼就是揭开神秘之谜的钥匙!可这个魔法是打哪儿来的呢?谁能抵御它?施蒂纳!就他一个人不受影响。
施蒂纳!……
会不会就是他造成的这一切?他在小船上的奇谈怪论,他曾暗示过一种强大的武器,有了这种武器他就能征服全世界。难道这并非吹吹牛而已?难道他真像猫儿戏弄半死不活的老鼠一样,有摆布别人的本事?他的这种力量来自何处?它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什么人?一个魔法师?一个新的卡利奥斯特罗?斯文加利?……
埃尔莎忽然感到身上冷得发抖。
施蒂纳在她心目中成了一头在草原上空追捕小鸟的秃鸢,而那只鸟儿就是她。她走投无路,不,她摆脱不了这个人。他决不会松开利爪放走她。
埃尔莎气喘吁吁地站起身来来,紧跟着又一屁股坐回沙发上。
她吓坏了。
“不!不!不!”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吓得枝头的几只乌儿直扑腾。
大厅里清晰地响起她叫喊的回声。说来也怪,这突然响起的回声竟然使她振作起来,就好象有人在给她壮胆,好象一位看不见的朋友在给她打气:“当然不!”决不能这么束手就擒,决不能给别人当一个身不由己的玩物,委身于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
她走进大厅,想定定神。
“怎么办?怎么办?”她在大厅里徘徊着想道。一幅画偶然落入她的眼帘:一个贝都英族骑士骑着一匹阿拉伯马在荒原上疾驰,带风帽的白斗篷随风飘起,他在拼命逃脱一群追捕者。
“危急关头就得这样!也许他最终会惨遭毒手,但他毕竟尽力而为了……逃走吧!无论如何也得逃!”
埃尔莎走到钢琴前,在凳子上坐下。眼前突然闪过不久前的一幕:施蒂纳倚琴而立,听她弹琴。他那张面带讥笑的苍白长脸,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令她感到恐惧和憎恶。
立刻就逃!可怎么逃呢?她身边甚至连钱都没有!
“百万富翁!”她苦涩地叹道,“我这个百万富翁——简直就是个叫化婆……”
昨天她还送给戈特利布20万,可她自己从来没向施蒂纳要过一分钱。也许,是一种清高的傲气阻止了她干这种事。
再说,她要钱干什么用?她几乎从不进城。如果她要买东西,商店自会送货上门,施蒂纳会付账。
她猛地想起,她的钱包里可能还放着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她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心急火燎地打开钱包。
钱在钱包里。虽说不多,可出走还是足够。以后呢?任何一个城市的随便哪家银行都会让她任意透支,不过,要求付款的票据会送到她的银行里,那时施蒂纳自然就会得知她的行踪。
埃尔莎沉吟片刻。
“哼,豁出去了!就是做个乞丐也比留在这儿任人宰割强……”
她草草穿好衣服,下到了二楼。门口卧着一条花斑短毛大猛犬。狗见了她,亲热地摆了摆尾巴。埃尔莎抚摸了它一下,想把它推到一边儿去,但那狗却纹丝不动。她想绕过它去开门。不料猛犬一跃而起,立了起来,随即把两只前爪往她肩上一搭,恶狠狠地咆哮着把她朝后推去。
她被狗的意外举动吓了一大跳,赶忙倒退几步。
“布采法尔!你这是怎么啦?”她温和地问道。狗又摇了摇尾巴,可一见埃尔莎又想去开门,就更凶猛地咆哮起来。这是施蒂纳留下的忠实看守!叫人来帮忙吗?她可不想打草惊蛇。突然,她想到了个主意。她匆匆朝戈特利布的办公室走去,门正好开着。她坐进电梯里的圈椅,把电钮一按,转眼就到了银行的营业部,不由心中暗喜。
“我赢了您啦,施蒂纳!”
她这不寻常的出现使警卫十分惊奇,可他们还是恭恭敬敬给她让开了路。而她还担心施蒂纳会给他们下过命令不准任何人出去呢。
埃尔莎只觉得心口怦怦乱跳,她跨过了那条令她深恶痛绝的门坎,深深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便钻进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真走运!她自由了。她拐了个弯,拦住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最近的火车站去。得尽快离开这儿,越远越好!……
在车站上,当一个脚夫问她要买去哪儿的票时,她的回答叫他吃了一惊。
“哪儿都行……用这些钱能坐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