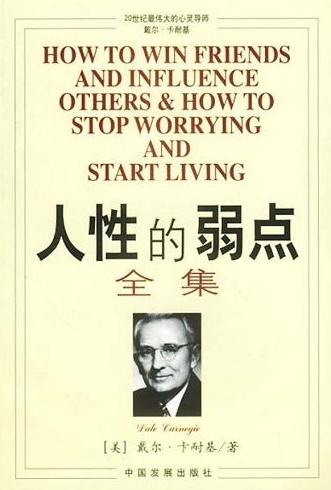人性禁岛-第1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与阿鼻废僧快要接近时,胸口下已无附着物,这几块儿连在一起近乎两米长的木片,被阿鼻废僧和凋魂门螺刚才的打斗毁坏了。
我如同一只泥鳅,滋溜一下钻到了索道的定下,抱着如大海波涛般起伏的连排木板,一点点地往阿鼻废僧的脚底下靠去。
凋魂门螺很是吃力,她在与阿鼻废僧厮杀的同时,眼角余光必须时刻提防着播月拔出手枪。
如果播月真敢拔枪,凋魂门螺定会将手中的一把棱刀,甚至两把棱刀向播月掷去,宁可再给阿鼻废僧打上一鞭,也不能让子弹打中自己。
播月在等的机会,其实就是想在凋魂门螺招架不住时,与、观察能力跟不上时,一个冷不丁出手。
我趴在索道底下,周围浓烈的白色水雾,令我感觉像泡在牛奶中。这样也好,对手更难发现我的存在。
阿鼻废僧的牛皮靴子,踩得索道木板腐屑飞落,我眯缝着眼睛,像骆驼那样用睫毛保护视力,不被小固体迷伤了。但脖子里面,掉的尽是潮湿的木渣滓。
瞅准机会,我抽出肩头一把锋利的匕首,悄无声息地翻上了索道,对准阿鼻废僧的右脚后筋,咬着牙下了死手,狠狠将刀刃抹了上去。
“啊呀呀呀啊……”耳旁虽然雨声唰唰,可连我自己都能清楚地听到,利刃割断活人脚筋时,金属薄片上发出“噌”地一声。
第四卷 斗岛 第三百五十九章 … 悬桥上的坠血僧
阿鼻废僧惨叫的同时,他心中已经明白,自己一条右腿被废掉了。这家伙因吃疼而迸发出的躁狂,一下飚升到了极限。他愤恨地嘶吼一声,猛挥手中的挂肉罪鞭,朝我翻扒在索道底下的头部抽来。
那条尽是细碎倒刃的钢鞭,来势劲道巨大,倘若横着抡在我鼻梁骨上,别说脸上的皮肉给它剜拽下去,恐怕两只眼球都给连带着挂出眼眶。
凋魂门螺两肩多伤,本就与阿鼻废僧厮杀的极度艰难,可突然之间,见对手歇斯底里地大喝一声,那条再度打向自己伤处的挂肉罪鞭,竟然中途一抖变向,朝索道下面抽去。
她立刻明白,自己不再是孤军反战,我这个一直被她被视为低等佣兵而刻薄待见的男人,已经如幽灵一般,隐伏在缭绕迷雾中出手了。
凋魂门螺从阿鼻废僧的嚎叫中,听得出对手伤得不轻,她岂肯放过这等机会,两把锋利獠长的棱刀,更是削中带刺、刺中变削,宛如久旱之后爆发出来的雨点,密集地攻击阿鼻废僧的咽喉、心窝和双目。
那条宛如一股疾风抽打下来的钢鞭,在我右臂快速蜷缩收起护挡头部后,却没如料想的那样打下来。
“苍啷啷……”一声棱刀和钢鞭的激烈撞击,再次从索道上面传来。凋魂门螺知道,我翻扒在索道下,偷袭阿鼻废僧,实则相当冒险。
悬挂在索道底下的我,不仅躲闪不便,更会一不小心坠断索道,让四个人一齐摔进树世底下。
凋魂门螺和阿鼻废僧,彼此已是厮打得伤痕累累,而播月这名悍将杀手,仍处在优良的格斗状态,仍在等待最佳的以逸待劳的时机。
不难看出,播月与凋魂门螺之前那短暂的交手,使她对这个出身缅甸的杀手极为提防。
播月一直没对凋魂门螺冒然出手,是因为这个北欧洋妞心里清楚,这场海盗大战,不知何时休止,假如过早地使自己负伤,就等于减小了自己活到最后的机率。
正如猎豹捕食水牛那样,它宁可暂时饿着肚子,放弃一顿美餐,也不会为了把肉吃进嘴巴而使自己在狩猎中受伤。
因为,瘸脚的猎豹吃得再饱,也不能规避生物链上的契约,等到它再度饥饿,估计连旱鸭都追不到。所以,狡黠的猎手不会让猎物成为自己最后的晚餐。
大自然的法则是威严的,它凌驾于人类社会的法则,不容许任何亵渎。现在,这片幽隐在浩然雨雾中的查戈斯群岛,已经将我们每个人,纳入了地狱的法则。
在这场猎杀与反猎杀的盛宴中,任何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仅靠缺失阴险和诡计的残酷手腕,是远远不够的,势必处在猎杀链条的低端。
到了这个时候,凋魂门螺也不得不做周全考虑,她宁可自己再吃阿鼻废僧一鞭子,也不想让我负伤。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清楚,播月迟迟不肯出手,正是想要至凋魂门螺于死地。而我,必须调动一切可能,成为播月的压轴对抗。
见阿鼻废僧那凶猛异常的一鞭子,没能成功地打下来,我乘机快速后撤,想再度消失进迷幻的水雾中。
现在的凋魂门螺,总算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阿鼻废僧得一边忍着巨疼,一边提防着脚下,防止左腿的脚筋再给从白色水雾下悄悄伸上来的匕首割断。
而且,阿鼻废僧也已无法再用右腿袭击凋魂门螺,那是一条在汩汩冒血却没时间包扎的腿,只要凋魂门螺脱耗时间,阿鼻废僧很快就会像断油的机器,动作越来越迟钝,直至完全停止,摔下索道死亡。
我从树冠里跃出,奇袭搂锁住播月时,咬得这个女人发出近乎绝望的凄惨尖叫,那声音一传入阿鼻废僧耳朵里,阿鼻废僧便再度爆发潜能,一面抗住凋魂门螺的攻击,一面腾出手来帮播月解围。
阿鼻废僧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对播月有什么关怀之心,而是他不想让自己落单,处于一对二的被动局势。
播月飞荡在钩山绳上的时候,与我有过近身接触,她已经略略清楚,我究竟是个怎样的对手。她见阿鼻废僧突然被我偷袭成重伤,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两把白闪闪的月牙割刀,像蹿跳起来的刀螂前爪,直奔凋魂门螺的一条大腿后侧削去。
播月心里清楚,这种直白的攻击,很难伤害到凋魂门螺,但她还得这么做,以此分担掉阿鼻废僧的压力,让他有一丝歇缓和调整。
可能播月还不知道,阿鼻废僧的脚筋已经给我割断,这种伤害,不是坐下来喘口气而就能恢复了的。
凋魂门螺也早早料到,播月该被迫向自己出手了。她攥在右手的那把锋利棱刀,随身体一个变速侧转,当地一声,拨开了播月剪削来的利器,同时右腿跟上,低位侧踹播月的小腹。
播月身体快速收缩,以单膝跪地的姿势,保护腹部不受伤害,同时右臂乘势下压,格挡在凋魂门螺的脚弓外侧。
凋魂门螺闪动着阴森可怖的眼睛,死死盯住播月的脑袋,而她急速扭转的腰肢,已经像上足劲儿的发条,致使左腿像松开挡栓的轮棍,再度攻击跟上。
“啪”!一记响亮的低边腿,重重抽在播月跪蹲时直立的小腿上。凋魂门螺的招数,大多柔和了泰式格斗,我在东南亚将近二十年,也深谙此种刚猛的攻击。
凋魂门螺那两条腿,硬入铁棒快如风,一看便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艰苦特训,先练就出腿的速度,再去踢打粗糙坚固的大树。直到将一棵一米维度的老树踢死,再一棵类似的老树接着踢。
在磨练膝击和肘击时,这些被当作杀人工具培养的格斗者,大多肉身上被抹了特殊植物的麻油,迫使神经不敏感肉体的疼痛。
可想而知,这种残酷方式培养起来的厮杀者,自然出手便是杀招,可顷刻结果普通肉身的性命。
第四卷 斗岛 第三百六十章 … 阴雨下的赶潮人
不过,但凡这样的杀手,由于身体超负追求一种极限,他们的寿命不长,很多只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
凋魂门螺那一记重重的低边腿,虽然结结实实打在了播月身上,但播月那白皙冷艳的面孔下,包裹骨骼的却尽是击打和抗击打能力超强的红肌和白肌。
由于播月预先有了意识,知道已经躲不开,势必要吃上一击,所以身体全部神经和肌肉紧张起来,大大降低了受损伤的程度。
即便如此,播月俊秀地眼角,还是微微颤了颤。我知道,那是真得疼。
凋魂门螺的每一次攻击,都非常坚决和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所以,她释放出攻击之后,身体回缩的速度很快,简直和出招一样。
播月右手腕儿一翻,月牙割刀去追抽踢在自己身上的腿,可对方回收速度太快,割刀只得落空。
任何一个人,回击用偷袭伎俩割断自己一根脚筋的对手,那种愤恨和怒火的激烈程度,已是可想而知,更不用说阿鼻废僧这种家伙了。
他对我愤恨到了极点,握在他右手里的那把笔直利刃,隔着铺垫在索道底下的潮朽木板的空隙,疯了似的往下乱戳乱扎。
此时翻扒在索道下面的我,就感觉自己抓在一头巨牛的尾巴上,随着它的狂奔而起伏颠荡。
无数碎木渣滓,混合土腥怪味儿,稀里哗啦往我身上和身下散落。我不仅要注意保护眼睛,还得时刻提防夹在木屑中戳下来的尖刀。
我此时的手指,一丝一毫也不敢扒在一个地方多停留上小半秒,更不敢张开胳膊去抓索道两侧的麻绳网。
阿鼻废僧那个家伙,不断隔着木板戳扎我的胸腔和腹部,他的真实意图,是想逼我在索道底下快爬,一不留神漏出手指和脚掌。
我五个指头,若挂在索道两侧的麻绳网上显露出来,阿鼻废僧会毫不犹豫地一刀削落掉;若给他抓到我的一只脚,这个暴躁到快要燃烧起来的家伙,势必要将我整只脚掌给活活剁下去解恨。
我依靠两只粗糙的手,悬吊着身体往后速撤,希望快掉靠近那棵靠近索道一旁望天树旁,然后跃起身子,扑抱上去逃开。
“咵啦啦,咵啦啦……”不断有木板被阿鼻废僧握刀的手砸碎,那家伙追得很猛很凶。我已经将后撤速度提到了极限,此时心中甚至有点后悔,不该采取这招偷袭,使自己给人逼到这步田地。
阿鼻废僧唯一的优势,在于他处在索道上面,不用控制自己的重力。但他也得趴下身子追我,一是站起来够不到我,二是他有一条腿已经残了。
我和阿鼻废僧的心里,都有去掏手枪的念头,意图隔着索道木板穿射死对方。可是,双方一追一撤,彼此都没有机会。
依靠双腿的弹动,双臂轮番后扒,带动身体回撤的速度,本来就到了极限,若再腾出一只手去摸枪,恐怕食指不等勾在扳机上,令一只手就给对方斩去五指,变成一只不具备抓力和控狙能力的血鸭蹼了。
而阿鼻废僧,左手握着挂肉罪鞭,右手攥着断剑式匕首,也很难将一手更换成枪械,虽然这仅是一点点的停顿时间,但也足够我腾出一只手,抽出挂在屁股上的FN57手枪。
这个时刻,就是拼速度,拼谁的枪械质量好,落后了就得死。但他不想与我同归于尽,那样的话,他会认为自己亏本,认为自己堂堂八大传世杀手,不该与我这种在大环境下无名份的低等佣兵玉石俱焚。
我快速地抽身,恨不能生出翅膀,飞进浓重的水雾中。一旦我消失在水雾之后,倒底是翻上了索道,还是故意做了一个假动作,依旧挂在索道底下,用手枪顶着木板对他过来,阿鼻废僧可就不清楚了。
这种情况我以前遭遇过,只不过那是在黑夜之中,如果;两人距离特别近,且又看不清对方的准确位置,只有想自杀或找死的一方,才会打出一声不可能击中对方却会暴露自己确切位置的枪响。
凋魂门螺虽然阴森森地令人恐怖,但她却是个很智慧的女人,她知道我拼命后撤中要经过一段底板空白的索道,便也牙关一咬,跳跃回来再次袭击阿鼻废僧。
可是,就在如此一瞬间,这一截不知经历多少风雨的破旧索道,再也容忍不得我们四人,在它苍老的身体上折腾,最后低沉闷重地发出啪啦啦一串崩响,索道从中间断开了。
只听得呼啦一声,耳畔再度生风,眼前就像突然掀起了热蒸屉,白烟似的水雾,瞬间充斥遮盖住了视线。
我心里清楚,这半截儿先后急速坠荡的索道,不会撞在周围的树干上,但若是荡到尽头,挂在残断索道上面不肯松手的活人,势必要拍砸在支撑索道的大树干上,喷出一口浓血。
先前看中的那棵索道旁的望天树,瞬间被我估算好时间和惯性距离,较接近望天树干时,我快速松手挺腰,跃起身子扑挂过去。
随着“啪”地一声,整个胸腔重重撞了一下,里面的笼骨差点没发出嘎巴嘎巴地断裂。此时的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疼痛,急速搂住树干往下滑溜。
只要出了水雾层,落入树界底下,便有看到轮廓的视野,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像赶潮人一般,看看播月和阿鼻废僧哪个掉在地上摔蒙了,然后抬去狙击步枪,对准让们的脑壳,令其永远安睡在这片参天的大树下,直到成为尘埃,被植物吸食上树冠顶端,再度展望到蓝天。
第四卷 斗岛 第三百六十一章 … 三道夺命的伪装
双脚一接触到潮湿绵软的树界底层,我便快速趴伏下来,匍匐着往后面退爬。
凋魂门螺和播月,已经被断裂的索道荡到了那边,只有阿鼻废僧,距离我很近,虽然那个家伙残废了一条腿,但他未必掉下来就摔死了。
向后爬了大概一百米,我才躲在一棵粗大的望天树后面,倚靠着树干慢慢蹲坐起身,开始通过狙击步枪的镜孔搜索。
由于气压的变化,望天树中层的水雾开始飘升,导致下面的光线,逐渐有了星星点点的亮度。
但从狙击镜孔中窥望,看到的依旧是那种黄昏即将进入黑夜前的光景。每棵树干之间,大概有十多米的距离,黑乎乎的四周,不断坠落下水点,使人感觉不出是下雨,仿佛植物王国的天蓬在漏水。
T型准线对着阿鼻废僧可能摔落的位置,仔仔细细地扫描着,除了一些四散零落的残枝朽木,散发着苍古阴森的气息,丝毫没有看到活着的在移动的模糊轮廓。
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又往前爬进一段距离,现在的阿鼻废僧,逃跑的动机会很大,关于这场争斗,万不能让活人的嘴巴传入命中水的耳朵。
但我此时,必须得谨记一点,这些八大之列中高级杀手的意图,大多出乎传统思维的意料,我必须得防着阿鼻废僧点,不让这家伙给我来一招“回马枪”。
双手扒在泛着潮腐闷热的枯叶层上,那种黏黏糊糊的触觉,使人说不出的难受。人在活着的时候,是绝对不愿意死在这种仿佛无法超生的阴暗世界的。
浓烈的土腥和植物腐烂味道,充斥着我的鼻腔,我的匍匐动作,比一只苍老的海龟也快不了多少。
当我靠近一截朽空了木心的树桩,便抽出匕首底端藏着的鱼线,绑住了这截儿长满菌类的朽木,再小心着脱下身上的伪装网,一点点的披挂到朽木上面,之后便释放着鱼线,悄悄爬开。
距离那截儿被鱼线绑牢的朽木大概六十米时,我便在一处地势稍高点的落叶积层上停下,让身子像孵卵一般,凹陷下去隐蔽。
长长的巴特雷狙击步枪的枪管儿,从厚厚的叶片下桶了出去,我再次往前面呈扇形侦查了一会儿,并仰望一下树界上空,那厚厚的水雾又升高不少。我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便开始收缩鱼线。
那段披盖着伪装网的朽木,像一只正用鼻子拱着落叶翻嗅食物的野猪,时急时缓地向我两点钟的位置靠去。
面对阿鼻废僧这种高手,即使自己已经割断他一条腿上的脚筋,我丝毫不敢大意,只要稍稍骄傲疏忽,死在对方抢下的惨剧随时都会发生。
凭借此时极其昏暗的光线,那截儿朽木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在伪装移动的狙击手。我不敢直接牵引那截儿朽木,便在右前方五十米远的一个树干上绕了一下。
一旦对方识破了这种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