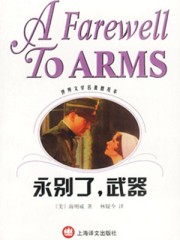永别了,武器-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岸朝北走。”
“也许风会转向的。”
“不会,”他说。“这风将这样连刮三天。是从马特龙峰1直接刮下来的。船上有只罐子可以舀水。”
1亨利·巴比塞(1873—1935)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战壕中写成本书,揭『露』战争的罪恶。该书于1916 年出版。
2 这是英国作家威尔斯发表于1916 年的优秀反战小说。
1 卢易诺是马焦莱湖畔的工业城镇。
“我现在付一点船钱给你吧。”“不,我还是冒个险吧。倘若你平安到了那边,你就照你的能力付给我好了。”
“好的。”
“依我看,你们不至于淹死的。”
“这倒是个安慰。”
“顺着风从湖上朝北走。”
“好的。”我跨进船去。
“旅馆的房钱你留下没有?”
“留下了。放在房中的一只信封里。”
“好吧。祝你运气好,中尉。”
“祝你运气好。我们俩多多感谢你。”
“如果淹死就不会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说运气好。”
“好运气,”凯瑟琳说。“非常感谢你。”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他弯arw(〃#gu}i0〃; ark1); 下身把船推离岸边。我把双桨往水里一划,随即抬起一只手来招招。酒保摇摇手表示不赞许。我看见旅馆的灯光,赶快把船直划出去,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湖上波涛汹涌,不过我们正是顺风。
第一卷 第三十七章
我在黑暗中划船,使风一直刮着我的脸,以免划错方向。雨已停止了,只是偶尔一阵阵地洒下来。天很黑,风又冷。我看得见坐在船尾的凯瑟琳,但是看不见桨身入水的地方。桨很长,把柄上没有皮套,时常滑出手去。我往后一扳,一提,往前一靠,碰到了水面,于是一划,往后一扳,尽量轻松地划着。我并不摆平桨面2,因为我们顺风。我知道我手上会起泡,不过我希望尽可能慢点起泡。船身很轻,划来不吃力。我在黑暗的湖面上划船。我看不见什么,只希望早一点到达巴兰萨的对面。
我们始终没看到巴兰萨。风在湖面上刮着,我们在黑暗中错过了遮蔽巴兰萨的小岬,所以根本没看见巴兰萨的灯火。等我们最后在湖上更朝北而近岸的地方看到灯光时,已是印特拉了。但是未到印特拉以前,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既不见灯光又不见岸,只好在黑暗中顺风破浪,不断划桨。有时我的桨碰不到水面,因为有个浪头把船抬高了。湖上浪很大;浪打在上面,激得很高,又退回来。我连忙用力扳右桨,拿左桨倒划,退到湖面上;小岬看不见了,我们继续朝北划。
“我们过了湖了,”我对凯瑟琳说。 google_protectandrun(〃render_ads。js::google_render_ad〃; google_handleerror; google_render_ad);
“我们不是要先看见巴兰萨吗?”
“我们错过了。”
“你好吧,亲爱的?”
“我好。”
“我来划一会儿吧。”
“不,我能行。”
“可怜的弗格逊,”凯瑟琳说。“今天早晨她上旅馆来,可找不到我们了。”
“这我倒不大『操』心,”我说。“怕的是在天亮前进入瑞士国境内的湖面时被税警撞见。”
“还远吗?”
“离这儿有三十来公里。”
我整夜划船。到后来我的手疼极了,几乎在桨柄上合不拢来。我们好几次差一点在岸边把船撞破。我让船相当挨近岸走,因为害怕在湖中『迷』失方向,耽误时间。有时我们那么挨近岸,竟看得见一溜树木、湖滨的公路和后边的高山。雨停了,风赶开云儿,月亮溜了出来;我回头一望,望得见那黑黑的长岬卡斯达诺拉、那白浪翻腾的湖面和湖后边雪峰上的月『色』。后来云又把月亮遮住,山峰和湖又消失了,不过现在天已比从前亮得多,我们看得见湖岸。岸上的景物看得太清楚了,我连忙又往外扳桨,因为巴兰萨公路上可能有税警,免得他们看到。月亮再出来时,我们看得见湖滨山坡上白『色』的别墅和一排排树木间所透『露』出来的白『色』公路。我时时都在划船。湖面越来越宽了,对湖山脚下有些灯光,那地方该是卢易诺。我望得见湖对岸高山间有个楔形的峡谷,我想那地方准是卢易诺无疑了。倘若猜想得对,那我们的船算划得快的了。我收起桨来,在座位上往后一靠。我划得非常非常疲乏了。我的胳膊、肩膀和背部都发痛,我的手也疼痛。“我可以打着伞,”凯瑟琳说。“我们拿它当帆使吧。”
2 巴兰萨在马焦莱湖上,对着巴罗米岛,是春秋二季游客游玩的地方。
“你会把舵吗?”
“大概行的。”
“你拿这根桨放在胁下,紧挨着船边把舵,我来撑伞。”我走到船尾,教她怎样拿着桨。我提起门房给我的那把大伞,面对船头坐下,把伞撑开。雨伞拍拉一声张开了。伞柄勾住了座位,我双手拉住伞的两边,横跨伞柄坐下。满伞是风,我感觉到船猛然挺进了,便尽力地抓紧伞的两边。风把伞扯得很紧。船冲得好快。
“我们驶得太好了,”凯瑟琳说。我只看得见雨伞的伞骨。雨伞被风绷得紧紧的,直往前拖,我只觉得我们正跟着雨伞在前进。我用两脚死命撑住,拖住了它,猛不防伞被吹弯了;我觉得一条伞骨折断了,打在我的前额上,当我伸手去抓那被风刮歪的伞顶时,它一捩,整个儿翻转过去,本来我是满帆而行的,现在弄得骑着一把完全翻转的破伞的柄了。我把勾在座位下的伞柄解下来,把伞撂在船头上,回到船尾凯瑟琳那儿去拿桨。她正在大笑。她抓住我的手,笑个不停。
“什么事啊?”我接过桨来。
“你抓住那东西太滑稽了。”
“大概是吧。”
“别生气,亲爱的。真滑稽。你看样子有二十英尺宽,非常亲密地抓住了伞的两边——”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来划船。”
“休息一下,喝一口酒。这真是个良宵,我们已经赶了不少路啦。”“我得不让船陷进大浪间的波谷。”
“我给你倒杯酒来。然后休息一下,亲爱的。”
我举起双桨,我们靠划船前进。凯瑟琳在打开小提包。她把白兰地瓶递给我。我用怀刀挑开瓶塞,喝了一大口。酒味醇厚,热辣辣的,热气透过全身,叫我觉得温暖愉快。“这是很好的白兰地,”我说。月亮又躲在云后边,但是我看得见湖岸。前头好像又有个小岬,深深伸入湖面。“你身体够暖和吗,凯特?”
“我挺好。只是稍为有一点僵硬。”
“把水舀出去,这样你的脚就可以往下伸了。”
随后我再划船,听着桨架声、划水声和船尾座位上白铁罐子的舀水声。
“罐子递给我好吗?”我说。“我想喝口水。”
“罐子脏得很呢。”
“没关系。我来洗一洗。”
我听见凯瑟琳在船边洗罐子的声音。随后她汲满了一罐子水递给我。我喝了白兰地后,口很渴,可是湖水像冰一样冷,冷得叫我牙齿酸痛。我望望岸上。我们离那长岬更近了。前面湖湾上有灯光。
“谢谢,”我说,把白铁罐子递回去。
“何必客气,”凯瑟琳说。“你要这里多的是。”
“你不想吃点东西吗?”
“不。我要等一会儿才会觉得饿。我们到那时候再吃吧。”“好的。”前头那个看起来像是小岬的地方,原来是个又长又高的地岬。我把船朝湖心划得远远才绕了过去。现在湖面狭窄多了。月亮又出来了,倘若湖上税警真在守望的话,一定看得见水面上我们这一条黑糊糊的船。“你好吧,凯特?”我问。
“我很好。我们到哪儿了?”
“照我想,顶多还有八英里路了。”
“划起来路可不少啊,可怜的宝贝。你累死了吧?”
“不。我还行。只是手痛罢了。”
我们继续在湖上朝北划。右岸高山间有一个缺口,成为一条低下去的湖岸线,那地方大概就是坎诺比奥吧。我把船划得离岸远远的,因为从现在起最有碰上税警的危险了。前头对岸有座圆顶的高峰。我疲乏了。划起来距离其实不远,但是人一虚弱就显得远了。我知道我必须过了那座高山,再朝北划五英里才能进入瑞士水域。现在月亮快要下去了,但在落下之前,阴云又遮住了天,成为一片黑暗。我把船划得离岸远远的,划一会,歇一会,抬起双桨,让风刮着桨身。
“我来划一会儿吧,”凯瑟琳说。“我想你不该划。”
“胡说。这对我有好处。划划可以使我的身体不至于太僵硬。”“你不该划,凯特。”
“胡说。适度的划船对于怀孕的『妇』人很有好处。”
“好,你就适度地划一会儿吧。我先回船尾,你再过来。你过来时双手抓牢船舷。”
我坐在船尾,披上大衣,翻起衣领,看凯瑟琳划船。她划得很好,只是双桨太长,很不顺手。我打开小提包,吃了两块三明治,喝一口白兰地。这一来精神为之一振,我又喝了一口酒。
“你累了就说一声,”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当心桨,别撞在肚子上。”
“倘若撞上了,”——凯瑟琳在划桨的间歇间说——“人生就可能简单多了。”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
“你划得怎么样?”
“很好。”
“你要歇时说一声。”
“好。”
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抓住两边的船舷,走向前去。
“不。我正划得挺好。”
“回到船尾去。我好好休息过了。”
借着白兰地的力量,我轻松而稳定地划了一会儿。随后我开始『乱』了章法,不是划桨入水过深,便是未入水中,不久我只是『乱』划一阵,口里涌起淡淡的褐『色』胆汁味,因为喝了白兰地后划船划得太用力了。
“给我点水喝,行吗?”我说。
“这太方便了,”凯瑟琳说。
天亮前下起『毛』『毛』雨来。风不晓得是停了呢,还是因为被弯曲的湖岸边的高山遮住了。我一发觉天快要亮了,就认真地划起船来。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只求进入瑞士水域。天开始亮时,我们相当贴近湖岸。我望得见多岩石的湖岸和树木。
“那是什么?”凯瑟琳说。我歇桨倾听。原来是一艘小汽艇在湖上开的咋咋声。我赶忙划船近岸,静悄悄地伏在那儿。咋咋声越来越近了;我们随即看见那汽艇在雨中行驶着,离我们的船尾不远。汽艇尾部有四名税警,阿尔卑斯山式的帽子拉得低低的,披肩的领头往上翻,背上斜挂着卡宾枪。在这样的大清早,他们看上去都还昏昏欲睡。我看得见他们帽子上的黄『色』和他们披肩领子上的黄『色』徽号。汽艇咋咋地开过去,在雨中隐没了。我把船朝湖中划。如果我们离边境很近了,我就不愿让湖滨公路上的哨兵来喝住我们。我把船划到刚刚望得见岸的地方,在雨中划了三刻钟。我们又听见汽艇声,我连忙把船歇下来,一直等到引擎声在湖的那一边消失。
“我们大概已在瑞士了,”凯瑟琳说。
“真的?”
“这也难说,除非我们看到了瑞士的陆军部队。”
“或者瑞士的海军。”
“瑞士海军对我们倒不是好玩的。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的汽艇声,可能就是瑞士海军。”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瑞士,就来好好地吃一顿早餐吧。瑞士有非常好的面包卷、黄油和果子酱。”
现在天『色』大亮了,又在下着纷纷细雨。湖的北部还刮着风,我们望得见滔滔白浪正打我们这边翻腾地朝北往湖上卷去。现在我有把握的确到达瑞士了。湖滨树木后边有许多房屋,离岸不远还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些石头房屋,小山上有些别墅,还有一座教堂。我细心张望绕着湖滨的公路,看看有没有卫兵,但没有看到。公路现在离湖很近,我看到一名士兵从路边一家咖啡店走出来。他身穿灰绿『色』的军装,帽盔像是德国兵的。他长着一张看来很健康的脸,留着一簇牙刷般的小胡子。他望望我们。“对他招招手,”我对凯瑟琳说。她招招手,那士兵怪不好意思地笑笑,也招招手。我放慢了划船的速度。我们正经过村前的滨水地带。“我们一定已深入瑞士境内了,”我说。
“我们得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亲爱的。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从边境线上押回去。”
“边境线早已过了。这大概是个设有海关的小城。我相信这就是勃里萨哥。”
“会不会同时也驻有意大利军警?在有海关的边城,通常驻有两国的军警。”
“战时可不同。照我想,他们不会让意大利人过边境来的。”那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城。沿着码头泊着许多渔船,鱼网摊在架子上。虽则下着十一月的细雨,小城看起来还是很愉快干净。
“那我们上岸去吃早点吧?”
“好。”
我用力划左桨,贴近湖岸,当船挨近码头时,我把船打横,靠上码头。我收起桨来,抓住码头上的一个铁圈,脚往湿淋淋的石码头上一踏,算是踏上了瑞士的国土。我绑好船,伸手下去拉凯瑟琳。
“上来吧,凯特。这太愉快了。”
“行李呢?”
“留在船上好啦。”
凯瑟琳走了上来,我们两人都在瑞士了。
“一个多么可爱的国家啊,”她说。
“岂不是挺好吗?”
“我们走,吃早点去!”
“这不是个非常好的国家吗?我脚底下踩的泥土都给我快感。”“我人太僵硬了,脚底下感觉不大灵。但是我觉得这正是个很不错的国家。亲爱的,你是不是体会到我们到了这儿,已经离开了那该死的地方了?”
“我体会到了。我真的体会到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体会。”“瞧瞧那些房屋。这岂不是个很好的广场?那边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吃早点。”
“你不觉得这雨下得真好吗?意大利从来没有这种雨。这是一种愉快的雨。”
“而我们到这儿了,亲爱的!你可体会到我们到达这儿了?”我们走进咖啡店,在一张干净的木桌边坐下来。我们兴奋得如醉如痴。一位神气十足、模样干净、围着围裙的『妇』人前来问我们要吃什么。“面包卷、果酱和咖啡,”凯瑟琳说。
“对不起,我们战时没有面包卷。”
“那么面包吧。”
“我可以给你们烤面包。”
“好。”
“我还要几个煎蛋。”
“先生要多少煎蛋?”
“三个。”
“四个吧,亲爱的。”
“四个。”
那『妇』人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