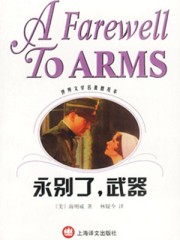永别了,武器-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顺利了。俘获的战俘差不多有一千名。公报上登载过。你没见过吗?”
“没有。”
“我捎一份来给你。这是一次顺利的奇袭。”
“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大家都好极了。人人都夸赞你。把经过的情形切实告诉我。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搞到银质勋章。说啊。把一切都告诉我。”他歇一歇,想了一想。“也许你还可以得到一枚英国勋章。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可以想个法子的。你吃了很多苦吧?喝杯酒。护理员,拿个开塞钻来。哦,你该看我怎样给人拿掉三公尺小肠,我的功夫比从前更精了。正是投稿给《刺血针》1的材料。你替我译成英文后我就寄去。我现在日日有进步。可怜的好乖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妈的,开塞钻怎么还没拿来?你是这样勇敢沉静,我忘记你在吃苦了。”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开塞钻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开酒瓶。拿个杯子来。喝这个,乖乖。你那可怜的头怎么样?我看过你的病历卡。你哪里有什么骨折。急救站那个少校根本就是个杀猪的。要是我来动手的话,担保你不吃苦头。我从来不叫任何人吃苦。这窍门我学会了。我天天学习,越来越顺手,功夫越来越精。原谅我说了这么多话,乖乖。我是因为看见你受了重伤,心中未免激动。喂,喝这个。酒是好的。花了我十五个里拉呢。一定不错。五颗星的。我从这里出去,就去找那英国人,他会给你弄枚英国勋章的。”
“人家可不会这么随便给的。”
“你在谦虚了。我找那位联络官去。由他去对付那个英国人。”“你见过巴克莱小姐没有?”
“我给你带来。我现在就去带她来。”
“别急,”我说。“先讲一些关于哥里察的情形。姐儿们怎么样?”“还有什么姐儿。两星期来始终没有调换过。我现在再也不去了。太丢人了。她们不是姑娘,简直是老战友了。”
“你真的不去了?”
“有时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来的。顺路歇一歇脚。她们都问候你。她们呆得这么长久,已经变成朋友,这件事太丢人啦。”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哪里的话。有的是姑娘。无非是行政管理太差罢了。人家把她们留在后方,让那些躲防空洞的玩个痛快。”
“可怜的雷那蒂,”我说。“孤零零一人作战,没有新来的姐儿。”雷那蒂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我想这对你没有害处,乖乖。你喝吧。”
我喝了科涅克白兰地,觉得一团火直往下冲。雷那蒂又倒了一杯。现在他安静一点了。他把酒杯擎得高高的。“向你的英勇挂彩致敬。预祝你得银质勋章。告诉我,乖乖,这样炎热的天气,你老是躺在这儿,你不冲动吗?”
“有时会的。”
“这样躺法,我简直不能想象。要我早就发疯了。”
“你本来就是疯疯癫癫的。”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探险回来。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血肉兄弟,没有arw(〃)8x*ee〃; ark2); 同房间的伴侣。你究竟为什么要受伤呢?”
“你可以找教士开玩笑呀。”
“那个教士。也不是我跟他开玩笑。是上尉。我倒喜欢他。假如非有教士不可,那个教士也就行了。他要来看你。正在大作准备呢。”“我喜欢他。”
“哦,我早就知道的。有时我想你们俩有点那个,好比阿内奥纳旅第一团的番号,紧紧挤在一起。1”“哼,活见鬼。”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1 《刺血针》是英国著名的医科杂志。
1 也许暗指同『性』恋。
“哦,我真喜欢取笑你,乖乖。你尽管有什么教士,什么英国姑娘,骨子里你我还不是一式一样。”
“不,不一样的。”
“我们是一样的。你其实是个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你不过是假装做美国人罢了。你我是兄弟,彼此相爱。”“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设法把巴克莱小姐弄来吧。你还是跟她在一起,不要有我在一起的好。你比较纯洁一点,甜蜜一点。”
“哼,见你的鬼。”
“我把她弄来。你那位冷冰冰的美丽的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男人碰上这种女人,除了对她叩头膜拜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派什么旁的用场呢?”
“你真是个愚昧无知而嘴巴龌龊的意大利佬。”
“是个什么?”
“是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鬼子。”
“鬼子。你才是冰冷冷的。。鬼子。”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发觉他对这些字眼最受不了,因此便继续说下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有经验而笨头笨脑。”“真的?我告诉你一点关于你们那些好女人的事吧。你们的那些女神。和一个一向贞节的姑娘或一个『妇』人搞起来只有一点不同。姑娘会痛。我只知道这一点。”他用手套拍打了一下床沿。“至于姑娘本身是否果真喜欢,你就无从知道啦。”
“别上火。”
“我并没有上火。我说这些话,乖乖,无非是为你着想。可以免掉你许多麻烦。”
“唯一不同点就在这儿?”
“是的。不过许许多多你这样的傻瓜还不晓得哩。”
“谢谢你开导我。”
“别拌嘴吧,乖乖。我太爱你了。但是你可别当傻瓜。”
“好吧。我一定学你的鬼聪明。”
“别上火,乖乖。笑一笑。喝一杯。我果真得走了。”
“你是个知心的老朋友。”
“现在你明白了。你我骨子里岂不就是一式一样的。我们是战友。接吻作别吧。”
“你感情太脆弱了。”
“不。我不过是比你感情丰富一点罢了。”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逼』近来。“再会。回头我再来看你。”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喜欢,我就不吻你。我把那英国姑娘给你弄来。再会,乖乖。
科涅克白兰地就在床底下。希望你早点复原。”
他走了。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薄暮时教士来了。医院里开过饭,并且已把碗盘收拾走了,我躺在床上,望着一排排的病床,望着窗外在晚风中微微摇晃的树梢。微风从窗口吹进来,夜晚凉爽了一点。苍蝇现在歇在天花板上和吊在电线上的灯泡上。电灯只在夜间有人给送进来,或者有什么事要做时才开。薄暮以后病房里一片黑暗,而且一直黑暗下去,叫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仿佛当年做孩子时,早早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护理员从病床间走来,走到床前停住了脚。有人跟着他来。原来是教士。他站在那儿,小小的个子,黄褐『色』的脸,怪不好意思的。
“你好?”他问。他把手里的几包东西放在床边地板上。
“好,神父。”
google_protectandrun(〃render_ads。js::google_render_ad〃; google_handleerror; google_render_ad);
他就在当天下午给雷那蒂端来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了,不好意思地望着窗外。我注意到他的脸,显然很疲乏。
“我只能呆一会儿,”他说。“时候不早啦。”
“还不算晚。饭堂里怎么样?”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人家的大笑柄,”他的声调也显得疲乏。“感谢天主,大家都平安无事。”
“你好,我很高兴,”他说。“希望你不疼得难受吧。”他好像很疲倦,我很少见到他这样疲乏过。
“现在不疼了。”
“饭堂里没有你,怪没意思。”
“我也盼望回去。跟你谈谈总是挺有趣。”
“我给你带了点小东西,”他说。他捡起那些包裹。“这是蚊帐。这是一瓶味美思。你喜欢味美思吗?这是些英文报纸。”
“请打开给我看看。”
他欢欢喜喜地解开那些包裹。我双手捧着蚊帐。他端起味美思给我看了看,然后放在床边地板上。我拿起一捆英文报纸中的一张。我借着窗外『射』进来的暗光,看得清报上的大字标题。原来是《世界新闻报》。“其余的是有图片的,”他说。
“看起来一定挺有趣。你哪儿搞来的?”
“我托人家从美斯特列1买来的。以后还有呢。”“谢谢你来看我,神父。
喝杯味美思吧?”
“谢谢你。你留着自己喝吧。特地为你带来的。”
“你也喝一杯。”
“好的。以后我再捎一些来。”
护理员送上杯子来,打开酒瓶。他把瓶塞搞碎了,只得把瓶塞的下端推进酒瓶里去。我看出教士失望的模样,但是他还说:“没关系。不要紧。”
“祝你健康,神父。”
“祝你早日康复。”
敬酒以后,他还拿着酒杯,我们彼此对看着。过去有时候我们谈话谈得很融洽,但今天夜里有点拘束。
1 美斯特列是意大利大陆接连威尼斯岛处的一个海滨城市。
“什么事啊,神父?你好像很疲乏。”
“我是疲乏的,但是我不应当这样子。”
“是天气太热吧。”
“不是。现在不过是春天。我觉得沮丧极了。”
“也许是厌恶战争。”
“倒不是。不过我对战争本来是憎恨的。”
“我也不喜欢它,”我说。他摇摇头,望着窗外。
“你满不在乎。你不明白。原谅我。我知道你是受了伤。”“那是偶然受伤的。”
“你就是受了伤,还是不明白。这我知道。我本人也不大明白,只是稍微感觉到了一点。”
“我受伤时,我们正在谈论这问题。帕西尼正在发挥议论。”教士放下酒杯。他在想着旁的事。
“我了解他们,因为我自己就像他们一样,”他说。
“你可是不相同的。”
“其实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军官们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有的是明白的。有的非常敏感,比我们哪一个都更难受哩。”“大部分还是不明白的。”
“这不是教育或金钱的问题。另外有个原因。像帕西尼这种人,就是有教育有金钱,也不会想当军官。我自己就不想当军官。”“你可是列入了军官级。我也是个军官。”
“其实我不算。你甚至还不是意大利人。你是个外国人。但是与其说你接近士兵,不如说你接近军官。”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我不大说得清楚。有一种人企图制造战争。在这个国度里,这种人有的是。还有一种人可不愿制造战争。”
“但是第一种人强迫他们作战。”
“是的。”
“而我帮助了第一种人。”
“你是外国人。你是个爱国人士。”
“还有那些不愿制造战争的第二种人呢?他们有没有法子停止战争?”
“我不知道。”
他又望着窗外。我注视着他的脸。
“自有历史以来,他们可有法子停止过战争?”
“他们本没有组织,没有法子停止战争,一旦有了组织,却又给领袖出卖了。”
“那么是没有希望了?”
“倒也不是永远没有希望。只是有时候,我觉得没法子再存希望。我总是竭力希望着,不过有时不行。”
“也许战事就要结束了。”
“我也这样盼望着。”
“战事一完,你打算做什么呢?”
“倘若可能的话,我要回故乡阿布鲁息去。”
他那张褐『色』的脸上忽然显得很快乐。
“你爱阿布鲁息!”
“是的,我很爱它。”
“那么你该回乡去。”
“那一定太幸福了。但愿我能够在那儿生活,爱天主并侍奉天主。”“而且受人尊重,”我说。
“是的,受人尊重。为什么不呢?”
“当然没有理由不啦。你本应该受到人家尊重的。”
“那也没关系。但是在我们那地方,人人知道一个人可以爱天主。不至于给人家当作一种龌龊的笑话。”
“我明白。”
他望着我笑了一笑。
“你明白,但是你并不爱天主。”
“是不爱的。”
“你完全不爱天主吗?”他问。
“夜里我有时怕他。”
“你应当爱他。”
“我本来没有多大爱心。”
“有的,”他说。“你是有爱心的。你告诉过我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
“我不爱。”
“你会爱的。我知道你会的。到那时候你就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向是快快活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