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ʵ����˵�������д��桷������ർ�������Ҫ��һ�������21�㡷����һЩ�����ӱ����ַ�Ҳ�Ƚ϶ࡣ������Ŀ������ͬ��һ���칫�ң��ҵ����γ������š�21�㡷���ε������ң���Ϊʲô��ÿ�ζ�Ҫд��ô��ʶ���ÿ�ζ�дʮ��ҳ��ʲô�������ӣ�Ҫ����ͬ�����������������Ҳ��ұ�⣬����˵�����úúã���ȥ�ġ���ÿ����ʱ����21�㡷���������Ǹ��ҵ�����˵������֪��ɣ����DZߵ��˾��Dz���д���ӣ����Ӵ���û������д������ҳ�����ǰ��˶����˵�ʱ���ӡ�����ռ䡷��Ӱ�죬���ó���ͷ����������ͬ������һ��Ƭ��д��������ʶ����о��ؼ�ʵ�����������֡��������룺���������Ž�Ŀ���Ҳ������ձർ������һ����
һ�žŰ����Ͼ�����һ����ѩ��Ҳ������ĵ�һ��ѩ����ѩ���������θ��Ҵ�绰�����ҵڶ�����һ��Ƭ�ӡ��ҵ��绰���Ҿ��û������ˣ�Ҫ�ı�һ���쵼���ҵijɼ���
�ڶ���һ�����Ҿͳ�ȥ��Ƭ�ˡ������˺ܶ��¥�ϻ�����ѩ��С������������ѩ���ڿ��л���Ʈ��Ŀվ�ͷ������Ƭ����ʮ���ӣ�û��һ���˵�ʣ�ֻ�л��桢�ֳ��������֣��ټ��ϼ�̵���Ļ�����������������ⳡ��ѩ֮��ı仯����״�������ֳ����ˡ�������Ļ���������㼸��ij���г���Ȼ����ȫ�û����ͬ������¼��˵��ˡ������߲˵Ĺ�Ӧ�Ͳ˼۵������������Ļ�ٽ��������㼸��ijѧУ��ѧ��������У��֮����Ļ�ֽ��������㼸��ij����Ժ���������ڷ�����Χ����ů�Ļ�¯���ȵȡ�
��Ƭ�������ڿ���ûʲô������ʮ����ǰ����ͦ���˶�Ŀһ�µġ��ҵ��쵼����֮���ϲ����Ҳ�е�����ȣ�����������Ƭ����ȥ�������������Ͼ�����ʲô�ش���ģ�û��̫������ż�ֵ��û���ϡ��������Ľ��������ƽʱ�������ҵľ�ͷ�ֳ����ˣ������Ƕ���ƨ����
�ٵ�һ��Ĺ�����
һ�ž����꣬���շ��������й�����������һ����ҵ״��������Э�ἰ���ֵ̾İ��ӡ�������ơ������������������Э�ᡢ�����й��̾֡�������Э��Ϊ�ϰ���άȨ�ģ����������ơ�ư������ֶ̾����ˡ��Ȿ���ͺ������ż�ֵ�������������ϣ�����ʡ���ֺ̾����ӣ�����������̨���˵����ݱ���ͥ����Ȼ������Ҳϣ��ý����վ�ڹ��ַ̾���˵����
�������ε���˼����ֻҪȥ��ͥ��һ����Ϣ�����ˣ���ȥ��֮���ҷ����������������ء�ԭ�������Ƹ���������˾��ơ��Ʒ�ƽ�����ơ�ƣ������ݵ������ر����˻�������һ�����úܺá����صĵط������������أ����ݵ�ơ����ҵһֱ�������ơ�Ƽ��������г������ҵ�����Э����һ����ơ�ƿڸ����ȡ�����������ݵز���ơ�Ʒֻ�һ������������������ĩ����������ơ�ƺ�����ơ�ơ�������ݵ��ص�ý�������һ��������˱�������һƪ�����л�������������һ�䣺����ơ��������ɽ��
�������һ����������ơ�������ݵ���������½�����������˾����ŭ�ˣ�����ѡ����쵥λ֮һ��������������Э�ᡢ�����й��ָ̾����ˡ��ڷ�ͥ�ϣ�˫����ʦ������������ͥ���۳�����Сʱ��һ����˵�����ְ���ͥ�����Ŀ����Ժܴ�̫�ᵱͥ���С�����������ϣ�������Ժ��ͥ������������˾���ߡ�
���������ұ����û�ȥ�ˣ���ƾֱ��������Ϊ�о����������⡪��Ȼ���ǵ�һ�νӴ����Ƶķ�ͥ���ϡ������ϸ����δ�绰��������ľ������ҵ��ж�˵��֮��ϣ�����ٸ���������ʱ�䣬�����Ƹۡ����ʺ��˻������ط�����һ�¡����λ��ҡ��а������ȥ����
����һ��������������ȥ���˻����˻�����οڸ����Ⱥ�����ơ�������½����ĵط������صľ����������Ƹ��ܲ�����֮������������Ÿе���̬�������ԣ�Ҳ������֮������ϡ����˻������˽�˺ܶ��һ�������֮������ȥ�˸��ʡ��ڸ����ҵ����˵�������������һ�Ĺ���ơ�ơ��Һܺ���Ϊʲô��������֣��ܶ൱���˶�������һ��ͳһ����Ȥ��˵������Ϊ��ʱ���Ƹ۵�����ơ��������ã�����ơ��Ҫ����������Խй���ơ�ơ�
����Ҳɷ��˺ܶྭ���̺������˽���ؾ�����ֻҪ������ơ�ƾͿ������ܺܶ��Ż����ߣ�����������ơ�������������ơ��������ơ�ƿ�����ƿ����ëһ��������ơ�Ʋ�����ƿ������СС��ëǮ�������ϰ�����˵ȴ�Ǻ�ʵ�ڵģ�һ�������������Ҳ���ٰ�������Ȼ���ڵط������ˡ���ôһ�������ؾ�û���˿Ͼ�������ơ���ˣ�Ҳû���˺�����ơ���ˡ�
�ɷù����У���û��֪ͨ����������û�뵽�����ڸ��ʽ�ͷת�˲�������ͽӵ���֪ͨ����������ί�����������Ѿ���������ס�ı���������ˣ�Ҫ����̸̸�����һ�֪�����ҵ����֡����Ƕ㲻���ˡ�����֮�����������쵼����˵����С�ϰ�������Ҫ��ֲ�ط���ҵ����ǵı���Ҫ�۰�������˵����һ���ۣ�һ���ۣ������ˡ���
�뿪���ʣ�����ȥ�����Ƹۡ��������Ƹ��Ҳ�֪��������ơ�Ƴ���һ�Ҵ��ͺ�����ҵ���ǵ�ʱ����Ψһһ������ŷ���г������ơ��Ʒ�ơ�������ȣ�֮ǰ���ڹ���ơ�Ƴ��������������ڳ������ܡ������Ҳ����˺ܶ����ߺͷ����ļ����˽һ����Ҫ�������������ݸ�ơ�ƿڸ����Ȼ��һ��ǰ������칫������Ժ�칫�����·����ļ�����ֹ�ط���������ҵ����һ�����š����������ȡ���ѡ�����Щ��ѡ����ǵط���������������������Ҳ������Ҫ���ֶΡ����ݸ��������ȼ�������ȻΥ���������ļ���Ҫ��
�ɷ��У����ݷ���Ҳ����һЩ��⣬˵��ֻ�ǿڸ����ȡ��ҷ������ǣ����ڸ������Dz������ȣ���ʵ���ϣ��������ѡ����������ָ�ꡪ����ָ�ꡢ��������ָ��Ϳڸ�ָ�ꡣǰ������ָ��Ҫͨ�����������ԣ�ֻ�пڸ�ָ�������˵������жϣ������ڸ��жϵı����������ʵ�Ʒ��ʦ�������ݸ���Ǹ��ڸ����ȣ�ȴ�������Լ���������Ⱥ���������ġ���������˾�ܲ�����������Ժ�о�һ��������������˾��������������ʡ��Ժ��
�����˳�ֵ��飬������һ���֤�ݺ�������һ��ʱ��Ϊ��ʮ���ӵ����ŵ��顣�쵼��������ˣ������������ɣ��Ѿ��о��İ�����û�и���֮ǰ��ý�岻������������Ϊ����������ʱ��ʡ�˴�ί�ᷨ�ƹ���ίԱ�ḱ���ε�����ϣ��������Ƭ�Ӻ���֧���ҵĹ۵㣬���ӷ��ɽǶȱ�֤��Ƭ��û�����⣬��Ը�����Լ���ְ�����ݽ����ҵIJɷá������Ϊ����ȡƬ���ܲ���������������ר���ҵ���ʱ���ǵķֹܸ�̨����ȷ���ҵı����ڷ�����û�����⡣̨���Ϳ������ؽӴ�����������֮��ͷ������һ�仰������Ժ�о�û�г���֮ǰ��Ƭ�Ӳ��ܲ�������ʱ��������ʢ���Դ�һ�ȣ���̨����֤�������÷���Ϊ����Ƭ�ӵ����������Ժû�и��У������ˣ���̨��������˵�������Ƭ���ȴ��ţ��ȸ�Ժ�о���������������жϵ�һ���Ͳ�������˵�IJ�һ������Ҳ�������ˡ������о��ǡ��㻹���ᰡ��֮�������ij��Ļ���
��ʱ�Һܾ�ɥ������û�а취���������ŵ���һѹ��������һ�ꡣһ�ž����궬���һ�����ϣ�ʱ������ˣ���ͻȻ�ӵ���������˾���³����ٿɵĵ绰���������ظ���˵�����������罭��ʡ��Ժ������������Ժ��һ���о�������ʤ���ˣ����ڶ���һ�����ҵ�̨������������������̨��Ц�ˣ�����С���а�������Ƭ�ӽ������ɡ���Ϊȷ���������ְ�Ƭ�ӵ���������ؿ���һ�飬��ʮ���ӵ�Ƭ�ӣ�����Ϊû��һ����ͷ�ͽ�˵����Ҫ�ġ������ֻ��Ƭ��ǰͷ����һ����Ļ������һ���ٵ���һ��ı�����
����Ұ�Ƭ��Ҫ��������Ϣ֪ͨ����������˾����˵���Ƹ������������컹��֯���տ���Ӱ��ܴ�
�Һ���������˾����ƽ�����Ǹ����˰���¡�����һ��ı�������֮��Ҳ���������ˣ���ʱ�Ҷ���ѹ������ƪ��������ƾ��һ��������θС�
��ʮһ�º䶯һʱ�ı���
������ơ�Ƶİ�������������̸��ܵ�ý��������ͼ��ߵ�������θ���רҵ�ж��ж�ô��Ҫ���������д��桷���ø����ҷ����������������θе�ƽ̨�ͻ��ᡣ
һ�ž��������һ�ڣ������ͼ������ڰ����ӣ�ͻȻ�ӵ�һ���绰��˵��һ��С��������ĸŰ�����Ѿ��������ҽԺ����ȥ�ˡ������̺���һ����������ơ�Ʊ������Ǹ������ٸϵ��Ͼ�������ҽԺ��
�Ǹ�����ĺ��Ӳ����꣬����ó��Ӷ��ϳ������أ������ϲ��˺ü������ӣ���ɫ�Ұף�����һϢ�������ر��¶�������Ҳ���ߺߣ�Ҳ���ޣ�����ʲô������˵��ͬ�������˿���ֱ�����ᡣ��С���������������֪�����ӽб�����˫��̥�е�һ������ĸ��������˰ְ֣�����Ǹ�������������Ů�˹�������ˣ�������һ����������Ů�ˡ��Ǹ�Ů�˾���Ű���������Ѻ��Ӵ���˳����ס�
��ҽԺ��������ȥ�˺���ס�ĵط���λ���Ͼ��ϳ��ϵ�һ���ĺ�Ժ���ھ������������˺��Ӹ���ı�����������ĸ��ʱ��ˮ�������ȣ����ӿʼ��˾ͺ���ˮ�����ھӷ���Ժ������������ˮ������������ͷ���ȵȡ��ɷý�������û�лؼң�ֱ�Ӿ�ȥ̨���Ƭ�ˣ�ͬʱ�����α���ɷõ�����������д��桷��һ��ר�����ţ���ǰ�ڵ�������ɴ�ԼҪ������ʱ�䣬���������ҵĻ㱨�����̵��������ƻ���Ҫ��������������ó�Ƭ�ӡ�
������ҹ��Ƭ�����ڸ��������������ϲ����ˣ�û���뵽Ƭ�Ӳ�����һ��������ǿ�ҵ���ᷴ�죬�������й����ڴ�����ܲ������ֱ������ӽ�Ŀ����һֱ������ʮ���㣬̨�����ֵ��绰���������ߵ绰��һֱ�����ͣ�����е绰����ŭ��Ǵ���Ǹ���ĸ�������˽�Ǹ�Ů�˻����Ǽ�ĸ����Ϊ��ʱ������û�к�С�����İְֽ�顣
��ʱ��û��ʲô������һ˵��̨��һ��Ҳ���ٽӵ����ڵĵ绰��ͨ����������Ļ�����ż�����������绰������������ͻȻ�ӵ���ô��绰��ֵ����쵼�����ˣ���֪��������ʲô�¡������������ָ��Ҵ��˵绰��˵�ڶ���Ҫ���ٱ�����ȥ��Ϊ�˻�ר�Ű�������·���߸��ҡ�
�ڶ��죬���Ҹϵ�������ҽԺʱ��С����IJ����ſ��Ѿ�ȫ�����ˡ���ʿ˵����Ŀһ������й����ܵ�ҽԺ���������ˣ������˵�����Ǯ�����鷢չ����һ��Ӱ���Ѿ��ܴ��ˣ�С�����IJ�����Σ����Ʒ��������ʵ����û�к���֢�����˵��������Ķ�����γʹ��ȣ����ǹ��ڹ�ע�Ľ��㡣��������������ȫ���Ĺ�ע��������ȻҪ������һ��������Ƶ��Ϊ�������ͣ������һ����Ŀ����ʱ��ͼ�������������˹������ȵ��ڶ����Ŀ���������Ѿ�����ȥ�ˣ�ֻ�ܴ���̨��д��ͼ�Ƭ����ͬ���dz�ȥ�ɷá����㡣�������죬�ݱ����ֻ��˯�ڵ�λ��ͬ�����Ļ�����¼�������һ�أ���Ƭ�ӵ�ʱ���Ҿ�ͷ��Ҫ�Ұ��졣
���ϵ�б���һ���������ڣ��һ��ǵ�����Ļʱ����һ��ְԱ���Ǽ����Ϸǣ�������䭣��ڶ��ڼ������־������߸��ˣ������ڣ��������������ʮ�����������һ�ڣ���Ļ�������ǵ�ʱ����Ƶ������Ա�����ᣬ����Ļ�����˰���ӡ�
���������ŵ���������Ҳ���dzɹ��ġ����ڽ�ͷ�ɷ�����һ�ʶ���������������ɷõ�ʱ��ܶ��˵����;�����һһ�Ǽǣ����Ѿ���ڽ�Ŀ�Ϲ����˳��������æ�г����������ȥ��Ǯ�͵Ǽǵ�Ǯ����һ�ٿ飬�Һ�����ֻ���������������ˡ�
�ҵ�����ƽʱ��Ƭ��������Ϊ���£�����Ƭʱ������Ȼ��Ϊ�����Dz�¥��һ�������ķ羰�ߡ��ܶ��˾��ø���һ�������ۡ������ģ������������Ҿ;��������Ǻ��Ҹ��ģ������Ǵ��ҵ�������������Ƭ��ʱ��Ȼ���������ᡣ
����������ĸ���Թ����˺��ﱻ�������ꡪ������˵����ʱ�ɳ���ֻ����������ͷ��˵ġ�
�߳��ȡ�
�����д��桷����һ��࣬�����������ߺ�ҵ��������������ʱ���ҵ��ۺϵ���ҵ��������������ʱ�����˷dz���ʵ�Ļ��������������������������������������̨�Ͽ�Ƭ��ʱ���Ҳ��ܸ�������ļ��ߣ�Ƭ��������������⣬���ܸ��߹��ڣ��ҹ���Ƭ�������һ��ϸ�ڡ�����ʲô������
1���ӱർ����Ƭ��
һ�žŰ����ʱ�����ӵġ�ʵ��ʵ˵�����������̸�����ڴ����ϣ��ط�̨Ҳһ����ϸ�̸�����ɷ����Ŀ���й�������ë������Ҳһ���������ǡ����д��桷Ī�������ͣ�ˡ��Ǹ�������Ϊ�ֵ����θ���һ���½�Ŀ�С��߽�ֱ���ҡ������൱����һ���������ߵ����ﶼҪ���Ҵ��ϣ�ͬ���Ƕ�˵��������Ϊ���������ûʲô�о�������������ô�������죬�����벻�����ˡ������ҳ��������Ŀ�ıർ��������Ȼ������ˣ����ǰ���ŷ�һ�ι��ʣ����ǽ��յ���̨��ȵ�ʱ�ڣ�������һ�ž�����Ů�������ˣ��ҵ������ֿ�ʼ���ý����Ͱ��ˡ�
˵ʵ�����Ҳ�ϲ�����߽�ֱ���ҡ�����Ҳ�����ڽ���̨�������������Ŀ�����ϲ����һ����������Ϊ�������Ҿ�û���á�ʵ��ʵ˵���ж�ã������ᡰɽկ����ʵ��ʵ˵������Ŀ�ˡ���ʱ����һ������˴����ˡ�����ʱ�ա������治������Ŀ�Ҷ�ͦϲ���ģ����硶����桷��������ռ䡷��Ψ��ͬ�ڳ��ֵġ�ʵ��ʵ˵�����Ҿ�������һ�����۹��ߵĽ�Ŀ�����ܵ�ʱ����Ԫ�����й�����һ�����ϲ����ʵ��ʵ˵����������ֵ�ʱ���������������ͬ�����𣿵�ʱ�����й������˺��������硰ҪӰ����ߡ��Ŀںţ����ܿ췢������һ���Ρ�
�ڴ�ý������������ң����ơ�ʵ��ʵ˵�����ѿ����Ŀ���Ļ�����Դ�������λ������ְ��ԣ������й����������ⶼ�����ܷſ�̸���ҿ��˼��ڡ�ʵ��ʵ˵��������ʲô���ҵ��ղء������ҵ����֡���Ū��һ����Ʋ��̸��Ʋ�ӵ����֮��ġ����ֻ���ġ�ʵ�������ж��ټ�ֵ�أ������ڡ��߽�ֱ���ҡ������������ҵ�Ҳ�����硰���й�������̫�١���������ƭ�֡�֮���������Ļ��⡣���ⶨ�����������ĸ��α��Ͻ�Ŀ��Ȼ���Ҿ����������д̨������Ŀ�ּ������֣�ÿ�����ֶ�̸ʲô��������ô�ݽ��ȡ��кܶ���쵼�����ҵ�̨����˵�ң�������ë���ַ��ˣ���д���簡��������̸����Ŀ�Ͳ���Ҫʲǫ̂�������쵼��Ҫ��̨��������ô�죿
�ܿ��ҷ��֣�̨�����Dz���д�ģ���Ϊ���ֽ�Ŀ�������˼α�����ʲô����д���˼�Ҳ��˵�úܺã�Ҫ������˲��ԣ�̨��д���ٺã���ĿҲ�����ˡ���һ�Σ��и�����ʵ���Ҳ��ź��ʵļα����Ҿ��Լ����ˡ�������˵��������ô�����ͷ�𣿡���û��������Ƭ�ӵ�ʱ���ҷ��֣������Լ����Ļ��е����˼֮�⣬�����α��Ļ��Ҷ�����������������ҵ������ν�Ŀ�α���������һ������д̨���ˣ��������ܶ������ٿ�α��ѡ�
����������һ��࣬����û�����ң�˵������Ƭ�Ӹ�ʺһ�������Ⲣ�������Ҿ�ɥ�����Ҿ�ɥ���ǣ���ʱ�Ľ���̨����״�����˼��㣬һ���ߡ��ർ�ǰ�����ܱ���һ�Ρ���һ������ø�ʲô�Ƶ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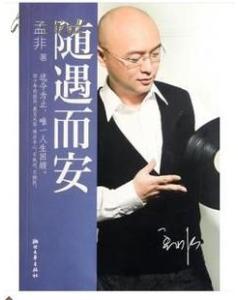
![Ȼ��,����������������С˵[1][1]_����С˵����](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