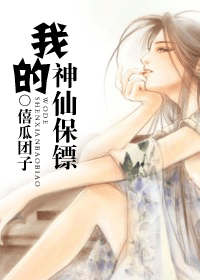贝拉的神秘花园-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故作镇定,毕竟我已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在人生舞台上,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嫩角色了,于是,我主动转换了话题。
“Peter,你什么时候有空,也给我看相,好吗?你看得挺准的。”我说。
“行啊!现在就可以,走,我这就上你家去。”
我们来到了我木屋的客厅里,我给他拿来一瓶矿泉水,随后,端过两张大木椅,就像上次给John看相那样,我直直地坐在他的面前。
“抬起你的脚,女人的命运全在脚上。”他说。
我有些不知所措,迟疑了一会儿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看相要看脚的呢。上次你给John看相时,没见你看他脚啊!”我的声音像蚊子叫一样轻。
但他还是听见了,他说:“对呀,男人的命运是在手的掌纹上的,而女人的命运写在脚上,每一道脚上的掌纹都是一个故事或某种命运。”
无奈中,我只得伸出我的脚,可刚一伸出就退缩了,我实在感到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去洗一下好吗?”
“这么细皮白嫩的,还洗什么呀。”他说,“把你的两只脚都给我好了。”
我像个听话的孩子,竟乖乖地把自己的脚放在他的腿上,任由他的一双手抚摸着。
看他那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你就明白他决不是混江湖的人。
他不可能是混江湖的,我暗自揣测着他:他应该不像是一个算命先生,因为他来挪威这一阵,也从没有看见他给别人看过什么相。再说据我所知,在美国一个“看相”的华人是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游山玩水的,怎么可能租下这个大农庄呢?我问过经纪人凡普鲁先生的,这座农庄的租金是每月3800美金,他怎可能只是一个算命先生这么简单的生存背景呢!而且,一个算命的有这么逍遥的情怀吗?
他将我的脚当成工艺品似的左观赏右揣摩,感觉像在给我做脚底按摩一样又捏又点,只是手法要轻柔许多罢了,弄得我痒痒的想笑出声。
“还没看好吗?人家痒死了。”我冷冰冰的脚,攥在他一双热乎乎的手中变得暖和起来。
如同冰块晒在阳光下,都成水了,他手心的汗,弄得我的脚底潮潮的,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不对劲。看手相看面相都很普遍,哪听说过有看脚相的?
“Bella,你想听什么?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有关事业还是爱情?”他终于开口了。
“说说过去的吧。”我说。
我心想,说将来的,我无法未卜先知,任你怎样海阔天空乱吹了,就说过去的吧,那才能真正检验你这位“神秘高人”的水准。
“你是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背井离乡了?”他问。
我故意装糊涂,“很年轻是指哪个年龄段?”
“应该是二十一二岁吧!”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的心开始慌乱起来。
“你还是逃走的呢!当然我不是说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逃犯,而是逃离一种难以承受的生活,比如感情啦婚姻啦,是吗?”他平静地看着我。
“算你这一点说对了,你接着说。”
“你很早结婚,也很快离婚。而从此之后,你似乎对母国的男人彻底没有了兴趣。每一段都是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的异国恋,但是你却无缘再成为新娘了。你最钟情的非美国男人莫属,我指的还不是John,在他之前的一个美国男人才是你一生的最爱,Bella,我说错了吗?”
那一刻,我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我惊呆了,这个陌生的神秘客,他究竟是谁呢?渐渐的,我的情绪自己也无法控制了,泪水一下子充盈了我的眼眶,我努力地克制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故意俯身用手在大腿上搔痒,头低下,以避开对方的眼睛,“虫咬的,好痒啊。”我说。
我必须要弄明白,这么清楚地知道我底细的他,是何方神圣!
“你必须要住在有江湖河海,有水相伴的城市。你似乎是死而复活的第二次生命,在自己的故乡找回遗落的自己。你一生注定要远游,四海为家。”他还在说着,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开始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怎会知道我和John的一切,他究竟是谁,他想要干什么?
会不会是我的读者?对于看过我的那本《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的人来说,都清楚地知道他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那本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悄悄地想试探他一下。
“我真服了你看相的本事,你都说准了。你除了给会讲英语的人看相外,还给听不懂英语的人看相吗?也就是说,除了英语外,你还会其他语言吗?比如中文。”我问道,我暗暗地思索,要是他会中文,答案就有了。
他思考了一下,随后说:“我只会说英语,中文我不会写,不会看,只会说这两句:你好吗?我爱你。”他的那两句中文确实说得很糟糕。
这就奇怪了,因为我英语版的《9?11生死婚礼》至今尚未出版,他不可能读到,而已出版的中文版的书他又看不懂,再说就是一个看过我中文书的读者也不可能想到我,一个躲在挪威森林里的女人就是贝拉呀。对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的名字,上一次他才问过John我叫什么名字呢。而且在中国,每月都有那么多新出的好看的书,谁会记得你这一部呀!谁又会看得这么仔细的呢!
我否定了他是通过我书中所描绘的一切才清楚知道我的过往的设想。
但这样的设想让我更可怕,有那么一刹那,我的心在瑟瑟打颤,我想待会儿等他离开后,一定要打电话给John,我觉得自己太危险了。
他是谁?
他绝不是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农庄客。
“Peter,你住的农庄看上去挺大的!什么时候,让我去参观一下呢?”我问。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很快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样吧,明天下午你过来坐坐好了。”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他的农庄,我急切地想从他的住宅里了解到一些什么。天哪!他的农庄大得简直就像一座迷宫,室内的一切都十分古朴,用的建筑和装修材料都是厚厚的大木头甚至只是一段段大树被砍下来,就直接用上了。
“你坐,想喝什么自己去冰柜里拿!”在参观了他的农庄后,我们回到了客厅。他告诉我楼上是他的睡房,我就没好意思上楼去看。
我随意地拿了一瓶橙汁,就坐在了大客厅的一张单人大沙发上。
“Peter,恕我冒昧,你在美国给人看相的,怎么有闲情逸致来这里度假呢,再说,你并没有给这儿当地人看相呀。”我道出了我的好奇。
“嘿,怎么说呢,我是属于更高层次的。我实话实说了吧,我应该说是属于研究人的过往经历和末来运程的专家,不是你所理解的通俗意义上的那种在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对了,我还需要与你合作一件事呢!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人类掌纹寻根图》,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文献性图书。昨天,我在给你看脚纹时发现,你的脚纹很特别,所以,我要将此写入我的书里。你放心吧,我不提你的尊姓大名,我也不了解你的真实背景,我惟一需要的是为你的一双脚拍一些照片。不要拒绝我的这一请求,好吗?对于我,那实在是很重要的,我不会拍到脚以外的任何部位的,这你放心好了。”他侃侃而谈。
我想了一想说:“那好吧。”
我终于释然了,原来人家果真是“高人”呢!怪不得,什么也逃不过他的那双火眼金睛。
不一会儿,他从楼上取来相机,又找来一张方凳,放在阳光照射进来的地方,并在那上儿铺了一块深紫色的布,他让我将右脚先放上去,当那双白嫩的脚放上去后,紫色的布映衬的汉白玉般的脚,竟折射出一种迷人的光晕,看着的确很有艺术感。
他对着它不停地拍摄,从各个角度拍摄,他还要我腾空悬着脚,以便他可以拍到深凹的脚心。
之后,又换成了左脚,一样地拍个不停。
“你知道吗?脚心这么凹的女人,在性爱方面非常出色。”他突然冒出这句话。
我的脸上立即泛起一阵红晕,“你胡说些什么呀?”
“有没有人赞美过你的这双脚啊!它实在很漂亮,少见的漂亮。”Peter边收起相机,边与我说话。
“没有吧,”我说,“谁会注意女人的脚呢!”
说完后,才猛然想起格兰姆不是赞赏过无数次吗?对了,还有那个华裔画家不是也专门给我写过一封信,说起当年他为了我的这双脚在故乡淮海路上的雨中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个回合,为了要看它个够。
忽然,我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在大路上碰到那个画家,他也许能认识我,毕竟他见过少女时代的我,我出版过的几本书上又有那么多的照片。可我根本不可能认出他来的,尽管我也应该在什么杂志报上看过他的照片,名画家嘛,但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或者说他的那张脸太大众化了。哪怕有一天,在他生活的纽约或他常回的上海,他就是坐在我的对面,我也不知他是谁。
知道了,又能怎样?
在走火入魔的艺术家面前,我是个正常的人,而在正常的人面前我却往往是个不正常的爱起来要死要活的女人。
不过我想说: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时代里,我们背负的苦痛与空虚已经足够沉重和乏味,因此,我们需要诗、需要梦幻、需要艺术、需要爱情。
“Bella,我要说,怪不得你的John要从你的脚爱到你的头呢!”他说。
“通常应该是说从头爱到脚吧。”我纠正道。
“是啊,是啊!从头爱到脚,仰头慕脚,彻头彻尾,总不能倒着来说。”他笑了。
“噢,Bella,你的故乡在哪里?从没有听你说过。”他好奇地问,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透过镜片大胆地凝视着我。
“很远的东方。”我模棱两可的回答。
“如果我没有说错,你是钢琴家吧!”他说。
“这次你恰恰说错了,我不是,我只是喜欢在家里乱弹琴。你猜,我那架钢琴是花多少钱买来的?”
“是高价还是廉价?”
“当然廉价,才付了200美金给杰茜卡。”
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杰茜卡,她是个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孤老太,快80岁了吧。不久前,她廉价卖掉了她的农庄,连同里面所有的家具,因为她的生活已无法自理,就搬进了奥斯陆市中心的“老年护理中心”去了。
“你是旅人而已,再说,廉价的钢琴不等于就是廉价的钢琴家。你不必谦虚,我还懂点儿音乐,你不是音乐家,也至少是一个不错的钢琴演奏手,你的确弹得很有味道。”
我不记得我在他来的时候,给他表演过弹琴啊!也许是他路过我的木屋时听见的吧。
“嗨,Bella,在别人面前,你是个谜一样的东方女人,好几次,我去酒吧喝酒时,碰上凡普鲁先生与几个你的左邻右舍,他们老向我打听你。以为我们都是华裔就必然有联系了,他们喝着酒,脸涨得红红的,总是说:‘你认识那个东方女孩吗?她真是可爱啊!走起路来那么缓慢,像柳叶轻拂一样,我真以为她是从东方童话里走出来的呢!不过,整天少见她的人影,关在一个单调的木屋里,不知在干什么呀,好神秘的,不知她从哪儿来?’他们一个个在揣测你,一个个都在想像那会是一瓶怎样甘冽而醉人的酒啊!”
“北欧男人也这么无聊吗?”我问。
“全世界的男人只要一走进酒吧,都一样。所以,酒吧文化最没有文化,或者说酒吧文化是最没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说起酒吧,我忽然就想起了玛雅:“对了,Peter,你认识玛雅吗?”
“见过,但最近好像好些天没有见到她的影子了,不知漂到哪里去了?”
“我知道,她去日本了。”
“人如浮萍,任由漂流啊!东方女人要来找这片神秘的挪威森林,挪威女人又要去东洋寻旖旎的梦影,我不知道她们最终能找到什么?也许她们都不清楚自己要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失落的,其实是找不回的,找回的也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了。”
那一刻,我不敢正视他,对于一个如此深不可测的“命相高手”,我有几分敬畏和羞怯,被人触摸心灵深处比褪去衣裳,让人解读自己的身体更可怕。我只想逃离,越快越好。
我推说家里的电炉上还煲着汤,就匆匆离开了。当他为我打开门时,迎面吹来的是如此清新的森林的空气。这才感到他的身上,甚至这屋子里弥漫的一种味道竟是那么熟悉,那么久违的一种熟悉,它是近乎于一种东方男人的体味,或者是保留在我儿时嗅觉里的像我外公和父亲身上那种上海男人特有的一种体味,是从当年上海石库门里飘出来的一种味道,有点甜腻、有点酸涩、有点混沌、又隐隐交织着黄浦江与苏州河里那种浊气。
那种味道让我说不上喜欢还是厌恶,只是它让我的心漫过了童年的故乡。
故乡,你在哪儿?
你还在那儿吗?
你已经迷失了吗?
你是否深藏在一颗心里,
一个女人的心里,
一个叫贝拉的女人的心里。
七 揉碎的太阳季节
许多年后,当得悉那男人死了,她的女儿身也跟着葬了。
17岁时的冬季,林歌生命中惟—一个男人舒凌进入了她的生活。舒凌是林歌的班主任。他们的故事还得从高三时的寒假说起。
那次,他们班在昌平县农村的一个大队进行为期一周的寒假务农活动。当时,林歌在学校是一只有名的“百灵鸟”,歌唱得好听极了,经常在少年宫演出样板戏选段和唱革命歌曲。由于她还担任班长,平时自然与舒凌老师接触比较多,那次安顿好同学们,在大仓库里放好铺盖入睡后,舒凌就带上林歌和另一位副班长女孩回到了大队支部书记为他们准备好的两间有炕的农舍。
这两间农舍在荒草萋萋的村头,互相只隔10米左右。说是农舍,完全就像茅棚,它原是大队联防部简陋的值班室。入夜后的农村,漆黑的一片,走路时得要一个手电筒照明。本来另一间农舍是准备给一个教导主任入住的,偏偏教导主任在出发前,老婆提前临产了,只得取消参加这次务农活动。所以,舒凌就提议让正副班长去住。其实破旧的农舍也比大仓库好不了多少。
他们三人并肩走在夜色中,林歌夹在其间,当她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舒凌的手时,霎地被电了一下,少女之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颤栗,这缘于她心中长久以来对舒老师的暗恋,无论是身体和心智,她都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而舒凌亦一直对林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这与林歌的品学兼优无关,而是另一种的感觉。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视线总要有意无意地落在林歌闪亮的眼睛和高耸的胸脯上。舒凌已经成婚,老婆是返城的北京知青,其实人还是蛮漂亮的,就是太干太瘪,缺少女性魅力。


![96产生新人类的神食 [美] h·g·威尔斯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