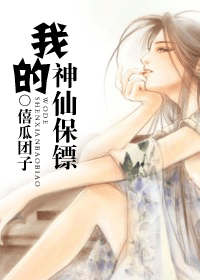贝拉的神秘花园-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歌,快告诉我,不要哭,你到底是怎么了?”
“不是我,是你……”她缓和了一下情绪后继续说:“我太为你伤悲了,刚才我看到“新浪网”特别推荐你的《9?11生死婚礼》,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可是一点也没有告诉过我呀。我现在总算明白你一个人来到奥斯陆的森林,终日把自己关在木屋里,原来就是在写自己的爱情故事啊!做梦也没有想到你遭遇到这么大的创伤……”
“没什么,一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生与死了。”我平静地说,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
“你真勇敢,贝拉,我要向你学习,他都离开这世界10年了,我还没有走出来。”
“林歌,人生短暂,学会重新去爱吧。”
“是的,我今天一边流着泪看你的《9?11生死婚礼》,一边就在对自己说,贝拉的文学祭奠也是我的情爱祭奠,我要像贝拉送走她的“9?11”一样,送走我心中的这块墓碑。”
“太好了,林歌。”涌动的激情让我感到眼角湿了,我格外地感到一种生之温情,我没有想到我的书不仅是为自己心灵疗伤,还把林歌从情爱的死胡同里拉了出来。
来自巴黎少年的爱,来自挪威森林天使的心灵独白,更让我勇敢地走过“9?11”这个伤心的忌日。
是的,我,我们,用活着的人最深切的爱,追思着一年前离去的脚步。
从烛光晚宴到无眠之夜,我们在哀惋的浪漫中送走了9月11日的夜晚,我和John在身体上虽然没有做爱,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唇齿相依,做了一次从来也没有这么切肤和彻骨的Makinglove……
几天以后,我们离开了纽约,回到了我的挪威的森林。我们说:走吧,我们的人生之旅就从那一片挪威的森林开始。
七 画展
所有的人都在悄悄地看我裹在黑色凉鞋里的脚。这当儿,让我觉得我的脚成了我的乳房或私处一样应该遮盖起来的秘密部位。十分平常的一双脚,十个脚趾却成了男男女女都想窥探的东西,我甚至暗暗为它的裸露而羞愧。我感到我的脚趾已受不了众人的目光,很不好意思地绯红成了一排,恨不得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暂时让它们遮避一下。
大概在收到那个华裔上海籍画家的第一封E…mail后的五六个月的时候,我又突然收到了他的第二封。这封E…mail很短,只有寥寥的几行字,他告诉我说,他将于今年的9月12日在纽约举办他的画展,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参加。
E…mail上还有个附件,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帧请柬,封面上是画家的一幅作品。我仔细一看,天哪!竟是一双女人的脚,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一定就是他多年前的毕业画作——那幅我少女时代的脚形。我留意到画的右面一页是一行字,写着被邀请人的名字,画展的具体时间、地址和电话。
我久久地望着那幅画,那幅灰蒙蒙的雨天背景下,泛着藕一般蔷薇色光晕的少女千娇百媚的靓足,我的思绪飘到了悠远的彼岸……
我当然想去看一下画展,那段时间我本来就是在纽约的。说实在的,我只是十分好奇地想看看那个画家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怎么会迷恋我的那双脚到这种程度。当年为了追踪我,竟在雨中来来去去折腾了好几个来回,要是他当时就对我说那番话的话,我肯定会骂他神经病、花痴的,因为哪有称赞小姑娘脚长得漂亮的,完全会当做不正常的人说了一通不正常的话。
画展设在曼哈顿时代广场内的一家艺术展示厅里,我到达的时候正是10点半,当我和John在签到簿上落下自己的名字后正欲步入画廊时,被门口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叫住了,“哇,你就是Bella啊!你瞧瞧,那是什么?”
我顺着她指点的方向,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满眼望去全是一幅幅姿态各异眼花缭乱的女人的脚。更让我吃惊的是画展的主题就叫“贝拉影履”。这是万万出乎我预料的,本以为我的那幅足形画只不过是画家许多作品中的一幅而已,至多是最出名最经典的那幅,哪里会想到画家全部的画作都是我的那双玉足呢!天哪!他真疯掉了,我的那位老同乡真的是在对我的玉足迷恋中疯掉了呀!
我胡思乱想,当年的梵高可以为了女人的一句戏言割下自己血淋淋的耳朵,同是画家的他,最后会不会疯到要想砍下我的脚?
我是不是比画家更疯狂。
我在每一幅画前驻足。
真是大手笔,大手笔啊!
“贝拉影履”的主题其实是那么深刻,她表现了一种“人在面对世纪苦难中呈现出顽强不息的精神”,通过一双女人柔弱的脚的挣扎来宣泄生命无法承受的悲剧。相对20年前他在我的少女时代对我那双玉足单纯地出于艺术美感上的迷恋,那今天,他已将此内涵大大地升华和演绎了。如同我的《9?11生死婚礼》一样,他的作品是从艺术的角度来激励破碎迷惘的心,从风雨飘摇中归来;无声地呼唤罹难者的亲人们,跨出你的脚步,重新站立到阳光下的世界来。
看吧,你看吧。
无论是表现状态的——脚裸精致的骨感,脚背丝绸般光滑柔软,脚趾千娇百媚的动感和性感,脚底粉藕色些微的褶皱;还是呈现视觉的——在近景、远景、特写、局部、写意、背景感觉;或挥洒技巧的——每一条掌纹的细微,肌肤的呼吸中血液的汨汨流动,以及指甲的光泽和脚趾的神态……
无可否认,他的画作是十分出色的,因为就从艺术地表现那双脚的境界中,人间的喜怒哀乐竟然可以通过那双脚的伸展、弯曲、撒野,以及阳光下柔和的自然状态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脚会哭、脚也会笑、脚会撒娇、脚更会唱歌跳舞呢!
这就是艺术,我领悟到的艺术,就像我领悟到的海洋,我所倾慕的艺术,正是一种从挪威森林的精神中感悟到的东西。我急于想找到素昧平生的画家——我心中的另一座神秘花园,当着他的面,我要好好地谢谢他,我要以灵犀相通的理解去拥抱他。
“请问,画家在哪儿?”我问那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她正在忙于为来宾签到服务。
“他很快就会到的,他嘱咐让你等着他。”她笑容可掬地答道。随后,我听见她在对别人说,“这位小姐就是Bella。”
我这才注意到转眼间已来了越来越多的来宾,这一看不得了,他们的目光全朝我投射过来,有的大胆,有的好奇,不少人还在悄悄地俯视着我的那双露趾的穿在简洁的黑凉鞋里的那双脚呢!
“贝拉,你好!”有人向我打招呼。
“贝拉,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有人要求道。
“贝拉很有神韵,她的气质真是高贵极了。”有人在窃窃私语。
“贝拉身边的男人大概就是她书中写的John吧。”谁在说着国语。
“贝拉桑,澳西萨希布里迭寺,空尼几娃。”(日语:好久不见了,你好。)我随即一转头,竟是当年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日籍同事光宁龙太郎。
“你好!”我亲切地说。
“我为你感到自豪,贝拉桑。”龙太郎说。
这时候,一位自称是某某华文报纸的女记者要采访我。
“对不起,我不接受采访,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说的。”我扭过头去。
“请问,你是John吗?”她紧接着问我身边的John。我拉着他马上就跑。
她转而又用中文问我,“如果没有猜错,他就是你的男朋友吧。”
我对在公众场合,在陌生人面前谈论隐私十分反感。
“这与你有关吗?”我也用国语回答说。
“我们都想了解你,贝拉。”
“人是没有办法被真正了解的。”我说。
她来了劲似的,“贝拉,你也太傲慢了,刚出了本书就不知自己是谁了。你知不知道,你的成功是建筑在多少人的痛苦上,你是靠‘9?11’出名的,更应该低调些,并不值得这么高傲的。”
我被她说得一头雾水。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没有我的《9?11生死婚礼》,罹难者亲属就不痛苦了吗?就是为了让自己和所有痛苦的心不再痛苦,我才含泪写出来的呀!
我十分平静地对她说:“小姐,你真的好有个性,我很欣赏你,你敢说别的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是啊!我确实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叫贝拉的女人好像是我又好像并不是我,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是谁?”
她被我神闲气定的语态给镇住了。
“贝拉,我们不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读者都有兴趣知道,你为什么不找中国男人当情人,是不是吃惯了西餐,再吃中餐就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我听傻了,彻底听傻了,怎会有这么低俗的女记者?
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反击道:“请你离开我远一点,好不好?将餐论餐,我告诉你,中餐永远是最好吃的,其他的隐喻,你不认为格调太低了吗?我不屑回答你了。”
她怏怏地走开了。
“亲爱的,你怎么了,不高兴吗?”一旁的John揽住我的腰说。
“没什么。”
“你看上去真的不开心啊!刚才那个女人对你说什么来的,惹得你这么生气?告诉我,我去找她痛骂一顿。”
“真的没什么。那个华语报纸的女记者只是问我为什么老是找美国男人当情人,而不找同族同根的中国男人,是不是对美国男人有特别的情结。”
“这是你的隐私,关他个屁事啊!”John也恼火了。
“算了,算了。”
就在我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我无意猛一抬头的当儿,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悄悄地看我裹在黑色凉鞋里的脚,这当儿,让我觉得我的脚成了我的乳房或私处一样应该遮盖起来的秘密部位……
慌乱中,我留意到John的脚上穿着干净的白袜子,我悄悄地对他说:“亲爱的,你能不能去洗手间把你脚上的袜子脱下来,随后,给我穿上。”
“为什么?”他一副不解的样子。
“因为他们都在看我的脚。”
“有什么不好,给他们看个够吧。”
“你……”
我想这位美国男人没有看过《金瓶梅》。
我不能不惊叹艺术的无限魅力。
“天哪!亲爱的,你看那个叫什么来的,他竟也在这里?”John拍拍我的手臂吃惊地说。
我朝他指点的方向投去一瞥。
在一扇通向画廊的通道口,站着一位男子,不用说出他是谁了吧?
还用吗?
他为我打开了门,打开了这扇通向神秘花园的门,通向挪威森林的门,通向艺术境界的门。
我愣在那儿,全然忘了身在何方,是在挪威的森林吗?一瞬间,我全然不知道是该走向他,还是我在等着他的走近。我只感到中等个子的他一下子显得是那么高大,在身高马大的老美面前一点也不逊色。我的目光静止了,再也不需要什么语言,不需要什么谜底了,我……
“你好,贝拉,瞧,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他伸出手,用我们都如此熟悉的沪语意味深长地说。
那是十分地道的,飘在少女时代淮海中路上的,来自故乡的声音。
“是啊!”我狡黠地说:“其实我早有预感了。难道你忘了我告诉过你的那位上海画家的事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为什么故意要提到淮海中路的少女时代呢?”我有力地握住他的手。
要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把我的脚从鞋子里伸出来交到他的手里不可。
他笑笑,很难以捉摸的意味。
我的耳畔回响起他临别的声音:“Bella,我想说我其实已经迷恋上你了,你不用说更多,我已经发现我们共同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明白选择一生远远地离开你并祝福你,并以我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你的感情是最恰当的。我相信,只要人长久,我们终会再见面的,也许还会很快呢!”
真的好快啊!我们又见面了。
我对他这样的“独特的方式”特别的敬重和感动。
那是艺术,更是内心最深沉的东西。
临别的时候,他把那幅当年轰动画坛的画包装得十分仔细,用双手把它送到了我的手里:“现在你应该说,你有好运了吧。”
“嗯。”我感动极了。
我拥抱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拥抱了他。
当初在挪威森林里的那段对话犹在耳际。
“看到这幅画了吗?”
“没有,真的好想看一眼,甚至出个价买下它。”
“你应该可以向那画家要求版权,或让他送给你。”
“那怎么行呢?那是人家灵感的果实。要是你是那画家,也百分之百不肯出手的。”
“那倒不见得。”
“可你并不是那画家,我也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是的,我很好运,一次次遇上了我命中必须遇见的人,得到了不少出色的男人们的倾慕,他们都愿意成为我手中放飞着的蓝风筝。包括当初认识格兰姆,何曾不是我的好运气呢?
人,享受生命欣悦的过程吧,把苦难沉淀到岁月的荒原里。
八 向戴墨镜的男子挥别
如同我们是久别之后的第二次握手,阿根的手是直接握在我心上的。或许,我们永不需要这第二次握手,因为那留在了故乡军营大墙内的一对少男少女,他们紧紧拉着的手从来就没有松开过。只不过当初他们握住的是爱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而此刻他们握住的是爱心,以及对沧桑岁月的回望。
在离开纽约的最后一晚,我从包里拿出那张陆露给我的纸条,上面有阿根的电话号码。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无论如何得感谢他给我的那一个使我终身难忘的总统套房内的白玫瑰之夜。
可是,当电话铃声响了,我的心也紧随着怦怦地跳了起来,慌乱得很。随即,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Hello”,那一瞬间,我的思维凝固了,本能的反应下,我搁了电话。
十五六年的岁月之河,早把我们隔在了河的两岸,我们看不见彼此,只有月夜下的河流见证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一直以来,我没有怨恨过阿根甚至他的母亲,他们不曾有什么需要得到我原谅的,在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面前,他们要求一个新嫁娘的贞操有什么错呢?我之后因此所经历的一切,全是冥冥中逃脱不了的命运所致,与他们无关。而且,对那些经历,我是如此缅怀,我不可想像如果当初老老实实地当上一辈子李家的媳妇,生命中不曾出现过海天、格兰姆,还有John,我的生命足迹也从未踏出过那个小城,我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意义?唉,往事不去想了,我珍惜所有我曾拥有过的,他们不会失去,他们不会在我心里失去的。
这样想着,心绪就坦然多了,就在我鼓足勇气想再次给阿根致电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接过一听,一个男子的声音:“请问,刚才有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96产生新人类的神食 [美] h·g·威尔斯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