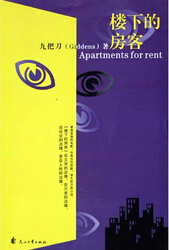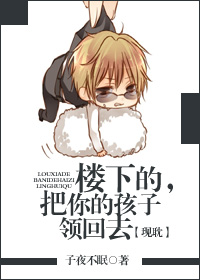倾风楼下-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救了我?”一说话,满口都是血,他这才注意到孩子手腕上的伤口。那道伤口很深,下手不留余地毫无感情,好象这只手根本就不是他的,所以下起手来一点都不感到疼不感到……不忍。
“多少人对我的血梦寐以求……你喝了这麽多还不知道,真让人气闷。”那小孩叹了口气,将手腕凑到他嘴边,“继续,不要停,你的毒很深,加上刚才又在湖里浸了那麽久,毒上加毒……你可不要以为是以毒攻毒。”
喝、喝他的血?他无法相信自己听到了什麽……他动了动身体,觉得之前那种如影随形地痛倒真是好了不少。於是他稍稍运起了内力,将内息顺著经脉一点点探去,发现气息顺畅得就象没有中毒那样。
“现在你相信了?”那孩子收起了笑,将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不想死,就快点喝,别浪费了我的血。”
孩子脸上带著抹嘲笑,却并非轻视的嘲笑,好象那是在笑他自己,笑他自己那样的体质、那样的言论……他低下头,看著那道很深的伤口,猜想著他到底是怎麽做的,怎麽做才能下这样的狠手在自己手上留下几乎无法愈合的伤口。
心里有个地方微微动了下,他觉得很不自在。就好象是那道伤口用相同的方式相同的样貌,然後在自己的心里也划了一道。
於是他和他一样,从那天起,两道伤口一起留血、一般疼痛、一样不堪、一同辛酸。
晚枫……祁煜抱著轻轻喘息著、神思涣散的人,他收起了回忆,收起了往事,也收起了他曾放任了十二年的感情。
“那天,我救了你,你救了我……”高|潮过後的疲倦不可阻挡,但祁煜还是抱紧了他,一次次拥有过後,席卷而来的,是一次次的空虚。
好象无论他抱得再紧,都无法填补。
不知为何,直到今时今日,祁煜仍然能记得,那一天,在他唇舌间的、血的味道。
那种代表著生命的温暖在口齿间流动然後蜿蜒著流入他的身体、进驻他的心,酸涩的感觉在一次次演化中,成了他生命中无法拒绝的甘甜。
他将脸深深埋在曲晚枫的颈间,眼中有种滚烫的热度盈盈欲坠。
我一直以为,那是命中注定,我一直以为我们就是命中注定……於是我毫不动摇没有犹豫的这样喜欢著你。他深深闭上了眼,不愿承认所谓的命中注定其实根本就是自己一相情愿,失落和遗憾在每一次相拥过後都朝他汹涌袭来。
曲晚枫闭著眼,感受著压在他身上的人,那种太过明显的心潮起伏。他有点无奈,於是伸出双手搂在他的肩上,情|欲过後独有的沙哑衬得他的声音终於有了一分真实。
“祁煜……”
对方立刻更紧地拥住了他,让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还能再说些什麽。
“挽风!我一直以为我是你第一个见到的人,我一直一直这麽以为的……我以为你从不开心是你不喜欢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安排,於是我尽我所能地满足你,只要你开心、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心满意足。可是我从不知道……”可是我从不知道就算是那种非你不可的相见,竟然还是、竟然还是太晚了……祁煜暗哑的声音好象印证了他黯然的心,就这麽一句就让他觉得悲从中来。
“太迟了,祁煜,太迟了。”曲晚枫回抱著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他的深情,可是人世间就是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无缘无份。
“你要的,我已经给了别人,放开我,你就能过得更好。”
因为你是祁煜,是万万臣民的皇帝,你为我做了太多不容於世的事,说真的,我承受不起,也不配承受。
“我不行吗?就真的非他不可吗?”难道我做了那麽多,即便伤害得你这麽深……可是我不行吗?祁煜突然有种想杀了他的冲动,毁灭一切的疯狂,这个他喜欢得太深太久的人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弱点。
“别人不行吗?就真的非我、不可吗?”曲晚枫听过,只是无力地笑了笑,拍著他的背,轻轻在他耳边反问了一句。那淡淡的笑听在耳里如同十二年前那样,还是冷漠的、深远的,随著年月的增添一点点沈在了心间。
“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回到那一天前……回到你救我之前,让我死那一天……”曲晚枫捧著他的脸,与他对视,遥远的过去在此刻慢慢清晰起来,那个因自己的血而重生的少年,他想,其实这一辈子,他也不可能真的忘却。
“让我死,这样,祁煜,你就解脱了……”
为了这无法得到的情感,我们终於可以不必再忍受,我们终於都可以得到解脱,也终於,你不必再为我而活。
就像我不因你而重生一样,我所有的感情早在相遇之前,就全部给了他。
祁煜……
曲晚枫有点哽咽地在心里唤了一声。
我们相见的太晚了……你对我的这些情意我注定了不能回应,注定了要辜负你。
真希望你能忘了我,真希望你能不要非我不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下去,那麽我宁愿死在你手上,也比看著你为我疯狂要好。
祁煜,我不是你生命的开始,更不是,你生命的结束。
☆、第十一章 覆水难收
第十一章 覆水难收
【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那一段莫名其妙的对话过後,弋倾文没有再说什麽,当看到司徒焰和南宫天宁的身影後,他冷笑一声,转身走了。施文然也调整了下心绪,於是跟在他身後穿过了第二片梅林。
走了一会儿,当确定後面两人与自己有一定距离之後,施文然考虑再三,终於还是问出了横梗在他心理的想法。
“弋倾文,你为什麽故意接近他们?故意弄坏他们的马车?”
当时他们的对话他在马车上听了有七分清楚,他觉得事情并不象表面上弋倾文不喜与人同行那麽简单。
前面从容的步伐声停了停,但前面的人并没有回头。
“为什麽这麽说?”
“刚才在客栈里,他们明明已经报出了身份,你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知道谁是谁……”施文然见他渐渐放慢了脚步走到了自己身边,也不避讳,於是索性把心底的怀疑都说了出来。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还做出一副不想和他们同行的样子。”
“哈哈,文然,说得好……” 弋倾文真的很意外,於是含著笑瞥过一眼,“好吧,我是故意的,那又怎样?我又没做什麽,我不过是给我们的上山找了两个不错的同伴。”
“可是据说山上很多毒也很危险。”施文然想起刚才南宫天宁说的,有点忐忑,“你该不会是……”
“猜对了。”不仅如此肯定了他,弋倾文还很好心的提点下去,“就是因为山上有很多麻烦,我们才需要多点同伴。”
“可是风析已经派了人一路跟著你……”他想起刚才那个叫司徒焰温和的脸,觉得弋倾文的做法实在很不好。
“而且就算有什麽事,反正我们都是随时可以替你死的,你又何必再拖两个人过来?”
“我实在不知道,你什麽时候这麽好心了。” 弋倾文突然哼了哼,不以为然的讽刺了句,施文然皱眉不语。
“算了,你就等著看吧,看到时候我们双方是谁利用谁。”不想再和他在这个问题多讨论下去,弋倾文嘴角微微翘起一丝很浅的弧度,有些挑衅的看向施文然。
“文然啊……其实对一些人,你最好不要用太好的心去想他们。”说著他低了低头,在他耳边最後留下一息温热。
“因为他们往往会辜负你的。”何况,我也不舍得让你替我来死啊……
语毕,他突然伸手揽住了施文然,施文然只觉腰间一麻,转眼间整个人就被他带著腾空而起。
施文然可以说是第一次体验到什麽叫轻功,什麽叫凌波微步……弋倾文稍嫌宽大了点的袖子在一点一飘间翻翻不停,不过是呼吸换气了几次,两人转眼就来到了山脚下。他回头一看,身後仍旧是刚才置身的梅林,而前方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壁。
轻轻将掌心贴在冰凉的石壁上,那粗砺的质感立刻在掌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施文然叹了口气,“要从这里爬到上面吗?”
“呵呵,谁说要爬?走上去吧……” 弋倾文走在施文然前面带路,绕开了左手边的石林後,脚下便露出了空地。只是那块空地狭长陡峭,沿著山壁一圈圈环绕直上,施文然抬头看,不消几圈就看不到路……因为被全部埋进了云层。
“从现在开始,每一步都小心,跟著我走,不要四处张望也不要回头看,这山路太陡太窄,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
弋倾文的声音在前方淡淡响起,混著他一步步踏上山路的脚步声,然後渐渐回荡在耳边,很低很沈。但施文然知道,这是一种绝对的警告,即便对方的语气漫不经心。
“我知道。”施文然点头。
“还有,别管後面的人,他们出了什麽事都和我们无关。你记得走我走过的路,其他不要看不要听更不要想。”
“好。”
简单的回应、干净的语气,弋倾文听後满意一笑,不再多说。他看了看渐渐要落下太阳,心想著如果夜里山行,实在是个不小的麻烦。
********
司徒焰和南宫天宁是第一次上祁冥山,两人慢悠悠走著,当看到山路在眼前渐渐显现了出来後,彼此相视一笑。
“我们能活著下山吗?”南宫天宁望著已然走上山的两人,缓缓而去的背影让他心里陡晃起来,“我现在觉得我们来唐门求玉,真的不怎麽明智。”
“你後悔了?”司徒焰轻笑。
“也不算吧……反正我差不多也就那样了,该说後悔的是你吧?你现在一肩挑的是整个南安司徒,你要是出了什麽事,那才是大事吧!”
说起来,四大家族里就属他们司徒一脉最单薄。司徒焰有个弟弟,只是那个弟弟还太小,算算如今也不过八岁。八岁的孩子能干些什麽?偏偏司徒焰的父亲又不是个能统领整个家族的料,早早的脱手却让司徒焰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
旁人看上去,他们四大家族又隐讳又庞大,好象隐秘在一团无上的光荣里,高高在上……其实也只有他们身为这四个家族的人才知道,要在朝廷与江湖中各不相牵、两面周旋,这中在夹缝中求生的感觉有多累。
“我?我为什麽要後悔……”司徒焰不是不了解南宫天宁的好意,只是他这一生过得太过安稳太过单调,所以这一次他借了这件事离开家族离开束缚,为的、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些什麽然後让他可以在往後的日子里一天天回味。
“我一直在想,接近我的人,都是些什麽样的人。”他又一次摸出了自己的扇子,那柄“画骨扇”上的缝隙好象是在他的心里。
“我身上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荣耀都像这把扇子上的裂缝,远远看去它完美无暇,然而仔细一看,其实有一道最丑陋的伤疤。而偏偏那些接近我、赞美我的人都为了这条伤疤。”他叹了口气,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人生,就有种很沈的无力感,“天宁,有时候我很累,我想找点什麽可以撑住我走下去的东西。你其实明白的,我们从小都看惯了那些人还有那些事,他们藏得太牢掖得太深,只有我们看得到……以前我一直觉得看多了是为了过早的了解什麽叫做世情而不受人欺骗,可是天宁,我偶尔就感到很可怕……因为将黑白分得太清楚,我眼睛很累,我开始把所有的颜色都归类成非黑即白。可笑吗?我觉得是,像我这样的人,居然对这样的人生有这种埋怨。”
南宫天宁边走边听,听到最後一句,他停下脚步伸手扯著前面人的衣服,“我不会笑你的。”
“是吗?”司徒焰并不介意他的答案,他知道天宁的脾性,虽然很极端,可是关键时刻总值得托付,可以信赖。
“像我这样的人,以後会怎麽样……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做妻子,然後生孩子,接著扩大或者守住家族事业……然後,抚育儿女、等待死亡。天宁,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人生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我二十四年来没有真心笑过没有真心哭过,天宁,我想好好活著,活一次,哪怕一次之後就是死,只要它值得,我就愿意。”手里的黄玉古扇是曾经一位古玩店的老人送给他的。
他记得那位老人有很温和的眼睛。
老人告诉他,人的一生不是尽情就要尽兴,如一滩死水般活著,不如早早地死早早地投胎,何苦在这人世多做停留。
司徒焰知道,听到那一句话时,他被打动了。
“哈!”南宫天宁突然抚著额头大笑一声,然後连连摇头,道:“真是听君一番话,胜读十年书啊!”他“哎”了两声,望向前面已经渺茫的背影,几乎已经快成了很小的点,再也看不清。他幽幽说道:“你这麽说的话,我真是得立刻找块豆腐撞死了!”
“你笑我吧,反正你是个多情公子,怎麽会烦恼这些事……”司徒焰其实挺欣赏南宫天宁的潇洒。他是真正的风流公子,他执著於一切美好的,无论人或事。尤其像他这样一个人,能做到真风流真性情,随意而为随性而活,不容易。
“我和你不同,我身上哪有负担?我爱做什麽做什麽,天下之大处处皆是我容身之处。讨个美娇娘做老婆有什麽不好?”只不过用一辈子喜欢一个人对他来说太不划算,所以南宫天宁多情,但不烂情……他只是懒得把所有注意力放一个人身上罢了。
“哦?这麽说,你是要打算娶立春姑娘为妻了?”司徒焰见他一副轻浮样,忍不住刺探。
“额……”冷不防被说到心里一直放著的那个人,南宫天宁忽然少有得板下了脸孔,“胡说些什麽!”白了他一眼,南宫天宁赶紧转回头,加快了步伐。
司徒焰看著他不打自招的样子,连连摇头,其实有些人还真是纯真得让人不忍去笑。
只是这麽一会儿工夫,南宫天宁走快了几步,当他回过神往前看时,突然发现前方竟然已空无一人。
他顿了顿,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於是将手里的扇子打开挥了挥,事实让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眼睛没有出什麽差错。
他真的看不到天宁了。
不会吧?他们才走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隔开了几步距离啊……眼前匪夷所思的景象让司徒焰不禁吞了口口水,在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前,一个身影忽然从後面撞上了他。
“哎呀,对不起……”熟悉的声音从後方传来,司徒焰直觉转身後退几步,待看清了人後,这次的他真是从吃惊转成了震惊。
“小兄弟!?你怎麽在这里?你什麽时候走到了我後面?!”
然而吃惊的又怎麽会是司徒焰一人,施文然半张著嘴盯著他,显然是眼前的人已让他匪夷所思到了极点。
“你,你怎麽在这里……”他记得他刚刚才和弋倾文说话,怎麽突然之间别说弋倾文人了,连自己现在在哪他都不知道。
“为什麽……”司徒焰看他也是一脸茫然,转身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前方,喃喃道:“那天宁呢,天宁去哪了?”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司徒焰心里生出了心慌,“就和你一样,你不见了弋倾文,我不见了天宁。”
此时西方天际的阳光已经混混沌沌,漫天灰色随著身处山间就这样压了过来,山路只围著走了两圈半,竟然已有身在云间的感觉,两人都觉得不太好。
“你怎麽走丢了?”不知道怎麽回事,只好先问问这位小兄弟,看看两人经历是不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