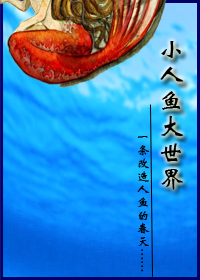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之一国色-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是一串长长的精彩的故事。这是后话。当时,我曾到他们的住地,小镇东头王伯瀚祖宗留下的绣楼。噢,对呐!当年,打死在涞滩码头上的地下党叛徒、廖佐煌的军师王伯瀚,不是很喜欢绘画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祖宗灵魂作怪,才导致这对远道而来的男女画家险遭裸体游街?这个世界的复杂与难解,也许,就从这时在我心里萌生。我在绣楼精巧棕色的正厅里,看到过鹰钩鼻子男画家故意留下来的那幅取名《寻觅》的油画,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冷调子的荒凉大漠和戈壁滩上,行走着一位朦胧绰约的妙龄少女的裸影。
画家(2)
哦,我惊呆了。世界上有如此的油画如此的美。不过,这个鹰钩鼻子,这个男画家,一边和实习女画家一起念主席语录,把小镇街道涂得通红,一边在绣楼上画如此清丽的裸女,难怪他们会犯男女关系错误,难怪他们会被专政队员,从女儿泉瀑布裸体抓出来游街。
卷发亮眼、高贵忧郁的实习女画家,是刚被打死或自杀吊死的走资派,原某某美术学院院长、反动学术权威、老雕塑家易仲天的女儿。她有一个很奇特的名字——易安。那时,她还不满十八。
已经造累了反,或已经厌倦了造反,不得志的鹰钩鼻子男画家,那时的名字很时尚,莫卫青。后来,“文革”的色彩褪去,他尤喜印象派,改名莫尚。
哦,我知道,也许,那幅油画《寻觅》上朦胧的少女,就是他心中的美神。
沿着这条道路,从如诗如画的乌溪小镇出发,我迈向了通往省城全国和世界的艺术与人生之旅。那片山水给我的诗情画意,牧笛一样悠远绵长。梦幻般的生命意象,像酵母一样在我灵魂中发酵膨胀。男画家莫尚,白净的脸庞,曾给我岁月的画板带来艺术的芬芳。朝云晚露,白鸟鸣蝉。不堪回首的烟云,岁月的沉淀。乌溪下游,竹海掩映的河边,我和郎天裁赤身裸体捉鱼虾,差点淹死。被打鱼的老爹救上岸来,夜夜噩梦。如风老辈请绣楼上的鹰钩鼻子男画家,给我画符驱鬼。粗糙的白布上,画的是那时最大的坏蛋刘某某的标准像。贴在我蚊帐中的驱鬼符,高颧骨,小眼睛,尖下巴,大鼻子上,麻斑点点。门牙暴在薄唇之间,那是碳青笔画,也是我的绘画启蒙。后来,男画家教会了我画主席像。后来,我带着画得特像特精的主席像,背着画笔画板赴省城赶考。天助神佑,我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神采飞扬构图,拧着眉头写生,我奔赴革命圣地体验生活。我开始《国色I号》系列油画作品创作。强渡乌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和如炽的硝烟,一路攻关夺隘。我画中心中的伟人,黄土高原,横刀立马。或叉着腰,面对亘古荒原,抒发豪情。或和牧羊老汉亲切交谈,那是土地与战争的优雅牧歌。我喜欢红色的热烈。我喜欢黄色的庄严。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流过太多的鲜血,包括我的父辈和亲人。有评论家认为,我的作品包含着皇权意识、平民忧思和战士一往无前的精神。对评论家的话,我不知所云。他们都没有来过乌溪小镇。我曾在芳草青青的乌溪河边放牧。早晨的露珠,滴下清脆的鸟语,轻轻拂动牛背上淡淡的茸毛。我从生活底层走来,我把手中的画笔,交给了乌溪小镇,交给了那条奔腾的长江。长江两岸,悬崖峭壁,我去寻找民族艰辛的历史。礁石,河滩,荆棘丛中,流淌着纤夫的血泪汗水,闪耀着“虽九死而未悔”的民族精神。那是一种“国色”,一种精神灵魂之“国色”。我获得了我们国家艺术荣誉奖章和证书。政府官员,包括文化行政官员蓝一号,都曾给我颁奖祝贺。他们希望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这是主旋律!”蓝一号认为,“这是立党之本,立国之本,立人之本,也是立艺之本!”
他铿锵有力地说了一串排比,因而他的话就显得很有分量。我也深信,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某一天获得国家甚至世界最高艺术奖项。而今,望着那些奖状奖杯和证章,我的心潮早已不在澎湃,反而常感空洞茫然。我手中的画笔和摊在面前的画布,对我的人生和生命,究竟有多大的意义?难道,我就这么永远做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军旅画家?我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我该到哪里去寻找,我心中的美神?
“高处不胜寒!”
我后来的同事和朋友,当初来乌溪小镇宣传革命思想的实习女画家,朦胧诗人,现在全国著名的女雕塑家易安,常常这么半开玩笑地对我冷嘲热讽。
我告诉她,不是因为我们爱情和婚姻都受挫,不是因为当初的乌溪小镇和现在的西岭画院,我都在她的关注下成长,我们之间过去的那点经历,仅算认识,无论对人生还是艺术,都算不了什么。何况,你和当初的鹰钩鼻子男画家莫卫青,现在的光头港商莫尚,你们,当年,革命思想宣传了,人体模特、裸体山水也画了,裸体游街批斗了,现在你们大家都活过来了,而活过来本身,似乎并不能代表什么。你想,艰难的日子,生生死死在一起,裸体批斗受辱也分不开。自由的时候,却天各一方,情感,啊,当初的情感,还在吗?又迷幻在根本就不属于你们裸体的丛林。哦,啊啊,我不是有意揭你的伤疤,如果这些对你而言是伤疤,对我又算什么呢?我没有故意揭你伤疤的资本,而是,呵哦哦,我不算老吧,情感似乎已经结了痂。而是,我想,在当今美术界,我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艺术做到了我们目前这个份儿上,要继续往前走。面对万花筒一样迷幻的时代,迷幻的艺术,迷幻的人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怎么生存,怎么选择?我是真正感到不是无聊,而是有聊的空虚。说着说着,我离开了正仰着不再卷曲的潇洒分头,为一国内著名企业做形象广告,雕塑一尊俗艳的裸体女神的女雕塑家易安。不打扰她了吧,连她都无法对话,更使我陷入无边的空虚。这种空虚,常使我深夜,或者黎明,在我暂时居住的单位和供职的家,古老而充满现代艺术情调的西岭画院,幽灵一样晃荡。无事可做,就不断读书吧。读哲学,读艺术,读达·芬奇、罗丹,读凡·高、塞尚、毕加索,读莫奈、福科、德里达、胡塞尔……我在文学哲学、艺术绘画作品与理论精神氛围中,踽踽独行。这种有聊的空虚,弄得我食不甘味,烦躁不安。面对生活和艺术,我无计可施。于是,我才于那年春节,只身回到我那如诗如画的家乡。
画家(3)
乌溪小镇,曾给我诗意和灵感,曾晃荡我的身躯和灵魂,从肉体到心灵,都曾滋润养育了我的家乡,现在,我将在你的怀抱里,寻找到一种怎样的“国色”呢?
红海洋和武斗炮火中的某某美术院校,那片绘画学术都已是荒芜的土地。牛棚集中营或者校办农场厕所垃圾堆,似乎还有月光照耀,月光中静静矗立着的那株孤零零的麻柳树,清冷遥远而苍凉。易安的父亲易仲天,一位来自延安毕业于鲁艺的红色老雕塑家,吊死在这株颇带艺术情调的麻柳树上,月光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农场背后那片松树林成堆的垃圾中,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紧紧抱着一尊残破的石膏像。那是打断了下半身的维纳斯高高昂起的头颅,虽然残缺不全,依然洁白如玉。尤其是维纳斯的半截胸脯,在月光中依然像洁白的轻纱,穿过古老麻柳树枝树干,照进少女的胸怀。维纳斯雕像是父亲留给她的唯一财富。当时,鹰钩鼻子造反派画家莫卫青,还不叫莫尚,在少女心目中也并非张牙舞爪。大规模的武斗已经过去,新事物的消息已渐露曙光。莫卫青并不是直接迫害老院长老雕塑家的罪魁祸首。他是老院长暗地资助的一个福利院的孤儿,从小又被学校守门的老头收养,很有艺术绘画天赋。一九六六年。革命了,他积极革命积极造反,二十一岁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一九七一年,结合进了某某美术学校“革某会”第三把手,他在巡视学校农场的时候,在如水的月光下,发现了易安蜷缩在垃圾堆里,紧紧抱着残破了的维纳斯。他居然在月光中和易安一起,在农场厕所旁的木板房,或者和堆放农具教具的黑暗仓库里,把打断的维纳斯一块块缝合修补拢来。他看到了易安卷曲头发下面的脸庞,在修补维纳斯胸脯的时候,流下了两行清冷的泪,月光中显得那样凄清而圣洁。老雕塑家的胸前和后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教具维纳斯,弓着身子像虾米,站在主席台上被批斗受凌辱,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经历和他取得的成就。他疯了似地守护着教材教具仓库,不准造反的群众把教具仓库里装满了的人类美术文化精品付之一炬,他被红海洋的烈焰灼烧得遍体鳞伤。矮胖的身躯蜷缩在主席台,没有剩下几根长发的光亮脑袋上一片血污。押回教具仓库之后,他被乱扔在维纳斯雕像的断肢残臂丛中,不吃不喝。月明星稀。老雕塑家把身上吊着维纳斯的绳子挽成一团,摇晃着走出教具仓库,吊死在校办农场边垃圾满地的麻柳树上。这就是一代蜚声海内外的老雕塑家的结局,而他唯一的女儿更加奇特的命运,即将开始。当然这是易仲天死因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看到了一张名为《某某某战报》大红的标题《一个红色艺术家的男盗女娼》,把他即将解放回到省城,以红色文化人的身份做地下党某省委宣传部长,和某某官太太打得火热,说不定还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已经出现在批斗他的队伍里。或者,因他失误出卖的地下党学生某某某,作为叛徒被某某某枪杀,要来找他算账。总之这是一团历史的疑云。易仲天带着维纳斯和一团历史的疑云远去!唉,革命啊,人的情感的某一角落,真是复杂啊!但是,无论多么复杂,总有一片月光静静地为自己照耀。生命的烈焰,总能点燃心灵的激情。
失去父亲的易安,那时十六七岁。她想在莫卫青身上体会艺术体会兄情父爱,体会那样病态年代里,一个男人的激情。他们到乌溪小镇采风写生,究竟受到谁的指派,有没有得到谁的批准?莫尚也并不是造反派里多大的官,他不过是易安父亲的一个很有绘画天赋的学生而已。结合进入“革某会”队伍,他那种小毛孩子,也仅仅是一种点缀。而之所以要把老雕塑家迫害致死,也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哪一派学术头头和造反派头头,谁有资格在校园的广场上雕塑主席大型雕像而已。为了获得这种权利,来自延安来自鲁艺的红色老艺术家,失去了生命。后来,在乌溪小镇东头的绣楼里,莫尚和易安都教会了我,如何掌握画主席像的尺寸和比例。他们在镇东头石桥上,涂写很红的革命语录口号标语,桐油灯在吊脚楼屋檐上摇曳,映照着崭新大红金黄的主席语录,把小镇带入又一个难忘的节日气氛之中,正如当年石达开和红军的队伍,路过涞滩码头乌溪小镇刻写口号和标语,燃烧在当时和后来人们的心灵深处。
画家(4)
至于他们闹出的那场裸体绘画风波,在当时的乌溪小镇,毋宁是投下了一磅重型炸弹。我不知道绣楼上的洋槐树叶丛中,洒下那片月光,怎样把他们偷偷摸摸地引向乌溪小镇背后的那片青松林里去,有人说他们是到青松林里去考察石达开和红军留下的标语。本来那些标语在那个时候是不能算“四旧”的,关键是它们衬托着廖家雕刻精美的祖坟,显示着廖家的威风。悬崖上那些标语,被镇上的造反派和小孩子扔了牛粪狗粪和大便。他们是去清洗那些粪便,并用石灰在标语上覆盖着“某某某万岁”的字样,标语才能保存下来。的确,后来,我看到悬崖上“赤化全川”的巨幅标语上面,隐约覆盖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字眼。当时,在阳光下如此耀眼的标语,成了一句箴言,他们自己就变成了“牛鬼蛇神”,遭人批斗。虽然他们那样文静,那样谦逊,那样热情。我不知道易安那对青春靓丽而略显忧郁的眼睛,怎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巨幅标语的映衬下,看流水,看太阳,看一群群百灵鸟欢快地鸣叫着,从下游竹海中点点飘起来,匆匆划过乌溪小镇上空,一直悠悠飞进青松林、遥远的老君山,那广大神秘遥远的山峦之中去。
青春四溢的易安,那时,也许在寻找着萦绕在乌溪小镇山水间的艺术、灵感、爱情与自己人生的美?
那天,莫尚和易安在万年台歇马场背后的青青山崖上刷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已经很晚很晚。不知不觉,弯弯的月亮从他们前面遥远的薄雾袅袅的河湾竹海中升起来。那时,喜欢他们的小镇农民大哥,给他们送来了两根甘蔗和几个甜地瓜。他们就是拿着甜甜的甘蔗和地瓜,望着远处的月亮,走上了通往青松林的那条曲径幽幽的山道。不用说,他们心中充满了异样的甘甜。晚风拂拂。山路上的野花野草、青松林、马桑坡那丛烈焰般的小红豆,传来阵阵幽香。他们为了放松写标语时累坏了的腰身和手臂,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为,青松林中双双漫步,已经就是这段山峰、这个小镇很美很美的景致了。他们慢慢地走向了青松林里的那片月光。他们在林荫小路边的山涧泉水中,把甘蔗和地瓜洗得干干净净,心中快乐幸福的潮水,像山泉一样荡漾开来。虽然,那个年代的甘蔗和地瓜,并不十分饱满,毕竟那是来自大自然的清香和甘甜。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在青松林里的清泉旁边,相隔不远站着,怎样望着欣赏着乌溪小镇黄昏动人的晚景,也许有袅袅炊烟从乌溪河边古镇的吊脚楼上升起来,还有河滩河湾里一群鹅鸭在戏水唱歌,有老农吆喝着牯牛,从青翠的桑树林旁边的田埂上穿过,他们看到了一幅多么幽静的小镇美景。他们也许忘掉了自己是画家,因为他们已经构成了这幅美景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莫尚掏出白手绢,把擦干净的甘蔗递到易安手上,易安慌乱地接了甘蔗,青春洋溢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那样清冷。她说这幅美景谁能占有谁能占有啊!莫尚望望远处,望望背后的青山,用手框着瞄着图面取景。他说,我们能看到这幅画,我们就能短暂地占有它,走,到山顶上去,选取几种角度来观察。他们拿了甘蔗和地瓜,而易安的纤纤玉手,有点激动的好几次都把地瓜拿不起来,掉在泉水中。莫尚帮助易安捡捞水中甘蔗地瓜的时候,他们的身子几乎就蹭到了一起。他们的眼睛很近地望着,突然又隔得很开,他发现易安的眼神里飘飞出一丝慌乱甚至恐怖。他们不知不觉走进了那片月光,向青松林里更高的山峰攀登,他们为了观赏更辽阔的山村夜景远景,为了此刻甜蜜的心灵,一对青春激荡着的男女心灵……而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简单,也还要复杂。因为那天晚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在青松林里自由张望,甜蜜行走,一前一后,或并肩而行。他们并没有在那条岔路口坐下来吃甘蔗和地瓜,也没有被后来专政的群众从青松林里裸体抓出来。跟踪他们双双进入那片青松林的有一群基干民兵,当然不包括当时还不是小镇镇长的郎天裁。郎天裁那时还是一个只会在田里犁田、河里捉鱼、湖里捞虾、河湾里抠黄鳝的小伙子。他们也是后来从青松林里那棵双人松下发现了两堆甘蔗渣和地瓜皮,并由此推断他们在青松林里做了什么。当然,那种推断是他们在女儿泉瀑布旁边的小木屋里,被专政群众裸体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