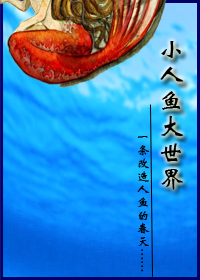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之一国色-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由此推断他们在青松林里做了什么。当然,那种推断是他们在女儿泉瀑布旁边的小木屋里,被专政群众裸体拖出来之后。既然这样,镇上的人们就可以把他们在青松林里做的一切描绘得绘声绘色。即使如此,那种描绘绝对不会超过西方名画,裸体的亚当和夏娃,或者,草地上的午餐。乌溪小镇上的人们从来都不知道亚当和夏娃是怎么回事。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把那对从遥远省城来小镇宣传革命思想的画家,描绘成不知羞耻的偷情男女。可能描绘成在那片如水的月光中,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之中,或者绘画,或者裸体。画家嘛,要么裸体画别人,要么别人画裸体。总之画家和裸体模特,都不是好东西。实际情况是,在那片松林那片如水的月光中,在那棵古老的双人松下,他们都没有裸体,也没有画裸体。他们只是作为从事绘画的一对青年男女,在那样的时刻,坐在青松林里谈了许多各自想说的那些话而已。这里清净自然,远离“走资派”、“牛鬼蛇神”和革命夺权的喧嚣。他们的谈话也并不是从牛鬼蛇神开始,莫尚认真地告诉易安,自他在农场的厕所垃圾堆旁边,看见易安把断臂的维纳斯寻找回来的时候,你和你父亲一个因维纳斯而死,一个因维纳斯而活,我心灵中就荡起了从没有过的震撼。他觉得当年他们打碎用做教具模特的汉白玉雕像维纳斯,也许就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犯罪。也许,我们都不该那样对待你的父亲,不让他“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清冷的秋夜,寒鸦鼓噪的黎明,孤零零的麻柳树,农场厕所垃圾堆中,少女易安,把打碎的维纳斯紧紧抱在胸前,像她遭批斗上吊麻柳树的父亲,至死抱着的维纳斯。那晚,她哭着告诉莫尚,父亲对她说,像维纳斯那样横绝千古的艺术珍品,屈指可数的无价之宝,大概只有蒙娜丽莎、思想者和王羲之的兰亭序……人类的绝美艺术,总和人类生命与美同在。是的,莫尚说,正如我们眼前的这幅美景,它就是我们心灵中的维纳斯。不用说,他们也是谈了各自的打算和忧伤。易安失去了父亲,而莫尚也失去了新的革命政权中的造反派地位。我会继续革命的,莫尚说,画主席像写标语大批判,但是,我们绘画写生的功夫不能丢。我要在这个小镇上绘出表现自然山水的作品。现在不画,就把它深深埋在心中。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心中的生活、心中的美,表现得栩栩如生。其实,那天晚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带着画笔和画板。他们也不可能在那样的月光下裸体绘画。他们也许美滋滋地吃了在清泉边洗好的甘蔗和地瓜。月上中天。小镇东头绣楼一带,传来几声狗吠。莫尚站起来走了几步,转过身,看到靠在双人松前面仰望月色的易安,那张他熟悉透了的脸庞,从没有像今晚的维纳斯一样,光彩照人。他们甚至没有牵手,也没有像我们现在一对相爱的男女在一起,经常发生的接吻拥抱。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在青松林里究竟待了多久。而浩瀚夜空中那轮晶亮的圆月,什么时候悄然挂在遥远迷蒙的老君山巅,静静地望着……他们靠在双人松下的身影,像月光下的雕像,默默生辉。
画家(5)
那天晚上,是乌溪小镇专政群众基干民兵,虎头虎脑的小伙子郎天裁,为了寻找那对男女画家回来吃晚饭,发现了他们在青松林里的月光中偷情的。那顿派饭,正好派到小镇西头柳如风家。我也正好在他们家躲避“文革”武斗的炮火——当然,那时的武斗炮火,已经渐渐熄灭了,我还没有走,所以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别看如风老辈那时似乎已经是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做饭的手艺毫不含糊,因为他解放前曾在万年台廖家大院当过管家。那晚的晚饭,现在想来,真是丰厚的精品。蒸了一屉老君山山地里种出的玉米棒子磨成面粉做成的馍馍,特地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小碗米饭,煎了一盘从河里捞上来的金黄虾米,清香味飘到了吊脚楼外面的皂荚树下的月光影子里去。左等右等,画家都没有回来,郎天裁就找到山上去。他在万年台背后找到了他们用来刷标语的石灰桶,而没有看到他们本人。究竟那天晚上是他们自己回来,还是专政队员把他们请回来押回来的,我似乎已经不很清楚。总之,那晚的派饭,他们并没有来吃。因等得太久,就着虾米,吃了两块香喷喷的玉米馍,我也迷迷糊糊入睡了。但从此以后,小镇上的人们,不仅专政队员,就已经对他们的行动发生了怀疑。看得出来,那对画家从此把街上的标语写得更好涂得更浓,他们画的主席像和大批判绘画,更加引人入胜更有光彩。男画家穿得更干净,衬衣领子更洁白。而女画家,虽然那时她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画家,忧郁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丝笑容,路过吊脚楼的窗口,似乎也能听到她留下的歌声在飘走。他们教乌溪小镇上的人们绘画、搞大批判,批斗镇上那些多喂了一头猪两只鸡的老人和大嫂。白天,或晚上,他们还把镇上高矮不等的人们组织在老皂荚树下,或在绣楼下面底层仓库,或万年台歇马场阅兵台坝子里,教唱主席语录歌、大批判战斗进行曲。易安教歌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软的嗓音中带着那时歌曲特有的打打杀杀的铿锵,不知是不是因为那片月光,点燃了他们心中爱情的火焰,还是他们认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弥补发生在青松林里的过失,期望得到小镇人们的谅解。但是,他们这一切行动,都显得做作多余和徒劳。人们对他们的目光,已经从过去的好奇羡慕,渐渐变成了疑问和冷淡。他们似乎想说,你们两个居然可以在青松林的月光中,把自己脱光画裸体,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们学习主席的革命思想,一边叫我们横扫牛鬼蛇神,你们为什么要去做比牛鬼蛇神更肮脏的勾当?小镇牛鬼蛇神遭批斗的时候,他们都穿了衣服啊!但是,他们看到女画家,那么美那么年轻的女画家,眼睛和神态都那么坦然……又纳闷了!所以,好几次易安教人们唱斗争进行曲的时候,打倒谁谁什么的,斗争到底等等,音调嗓门都上不去。易安、莫尚和村上的人们都茫然沉默了。他们也许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同时他们又感到眼前的茫然和沉默背后,可能正孕育酝酿着什么,或者一场风暴,一股暗流,一场阴谋,或一种古老的声音,从小镇古老的绣楼里传出来。年轻的实习女画家和鹰钩鼻子男画家,住着的绣楼板壁裂缝里,出现了一双双眼睛。他们风流韵事之外更加神秘开心刺激的风流韵事,正在上演。有人夜晚偷偷地搭着木梯爬到绣楼上面去,隔着板壁缝偷看女画家洗澡。乜斜着眼睛偷看女画家洗澡的小伙子或成年人,“砰”的一声,从绣楼木梯上重重地摔下来,掉进洋槐树丛中深黑的阴沟里。而那时,不知不觉中,深更半夜,乌溪小镇传来一群野狗追逐狂吠。夏天已经来临。天气渐渐郁闷。偷窥女画家洗澡的人们,可能满足了不少愿望。居然有人添油加醋地描绘男画家和女画家一起坐在大木桶里互相洗澡,或者他们在床上谁扑在谁的身上云云。听这些故事的小伙汉子老光棍,都鼓圆了眼睛,呆呆望着绣楼上桐油灯光中隐约闪现的娟丽身影,咕咕往肚子里吞着口水。当然,绣楼内外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监视,或者偷看女画家洗澡和他们床上镜头的专政队员,背地里做出什么勾当?面对着她、幻想着她、或隔着她房间板壁缝,卖力地涂上一条条长长的液体的斑痕。燥热的夏夜,躁动的春情。而那些有老婆的莽娃汉子,则早早地和自己平时并不十分珍爱的黄脸婆女人,洗脚上床幻想着绣楼上靓丽的人影儿和她月光下的裸体,彻夜温存。春天的故事演绎出夏天的火热,男女工作在激烈而静悄悄地进行。野狗依旧偶尔狂吠,家猫突然凄厉嘶春。明月夜,乌溪河里一对对一群群产子的鲫鱼、鲢鱼、鲤鱼,在黄昏、在夜晚、在青蛙均匀的鼓噪声中,在河边青草丛中,热火朝天地奔腾跳跃。那是一个公鸡打鸣、产子繁殖的季节。深夜,或者黎明,就连烈日炎炎的老君山上,大白天也聚集着那一群群交配的野狗,嘴对嘴、屁股对屁股地疯狂奔跑跳跃大叫。这神秘的一切,预示着乌溪小镇可能因为埋藏在春天里的压抑已久的性欲,会在那对画家住着的绣楼里爆发,或者,以那里为导火索,惊心动魄地在乌溪小镇发生。
画家(6)
果然,不久,在那片洁净如水的月光中,莫尚和易安,被专政队员从女儿泉瀑布山上的小木屋里拖出来,裸体游街。
我不知道,人类像自然山水一样的生命与爱情,在那样如火年代如火的夏天里,沿着什么样的生命轨迹,源远流长,向前流淌,无论什么力量,也掩不住,阻不断。
走进月光,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又都没有走出那片月光。
夏天的日子,燥热而漫长。在乌溪小镇上的人们,把莫尚和易安在青松林里沐浴月光偷情的故事渐渐忘却了的时候,突然,一天下午,小镇东头他们住着的绣楼里,传来一阵纷乱的嘈杂声。他们已被专政队员从百里开外的女儿泉瀑布押回来,关在绣楼下面的杂物仓库等待接受裸体游街批斗。那时,我还很小。从小镇西头如风老辈家吊脚楼临街的窗户望过去,绣楼一带人头攒动。老实说,我心里涨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标语板壁主席语录,鲜艳而清晰。红色墙报黑板报,工农兵铁手攥着牛鬼蛇神,谁看了都振奋开心,怎么一转眼接受批判的,就变成了他们自己?他们在我心中是多美的人儿啊,做的事情多丑多丑。怎么能不穿衣服呢?他们画的主席像,圣洁而端庄。他们漫画的某某奇,虽然大鼻头上有几颗醒目的麻子,毕竟也穿了点衣服。就连鹰钩鼻子男画家,在绣楼上偷偷做的那幅油画,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行走着一个娇小玲珑的少女的背影,若隐若现的,也看不出她没有穿衣服呀!那是一个单凭穿衣服,或没穿衣服,穿衣服多少来表现美、衡量美、创造美的时代,红色记忆与裸体尺寸大小,把我那时还没有形成正常审美意识的脑袋搅成了一团糨糊。但是我想,他们心中绝对不是一团糨糊。他们在小镇上努力表现、努力工作,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各自命运的挫折和失落。莫尚从“文革”开始的狂热,到“革某会”的结合,再到被诬陷为反动“五·一六”组织头目,侥幸逃脱坐牢的命运,而易安正处于失去父亲的深深忧郁悲痛之中。所以,来到乌溪小镇,他们心底都装着各自的苦难和烦恼,他们结伴去参观旅游,到远近闻名的女儿泉瀑布采风写生,难道不是因为寻找心中那片明净的山水?那时的画家,除了革命思想宣传,并没有采风写生的任务。也许,他们只是发现小镇绣楼里住着不安全,或者,偷偷去寻找更安全更美的地方?他们究竟是晚上,还是白天,离开乌溪小镇,背了画板画架,沿着那条粗糙的山路,走进满眼葱绿的女儿山中,走向飞泻如练的女儿泉瀑布。
“我对政治已经厌烦,我对做官已经失去了兴趣,我是画家,当然应该,心中装满美山丽水。”
走在青翠的山路上,鹰钩鼻子男画家似乎对易安又似乎自我喟叹。他们一边走一边考察,考察那一带破“四旧”毁坏了的石刻群雕,考察石达开和红军在观音岩观音洞留下遗迹,在名胜古迹和艺术品面前,他们留连忘返。他们曾在山民守山的草棚里过夜,他们曾在青翠的山坡上向当地住户询问通往女儿山女儿泉的道路。也许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考察中流浪,在流浪中考察,画画写生。当遥远天边那挂高高的瀑布,像女儿的身影,柔美多姿地流淌下来,注入女儿河汹涌的急流,整个山川大地自然景物,都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中,他们激动得拥抱在一起。当然那次拥抱,也许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拥抱。我不知道,那次女儿山中行,怎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为从他们的整个人生来讲,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尽管他们的生命,因这次旅行显现出动人的火花,一直闪耀在他们生命的历程。女儿泉瀑布,灵动多姿的身影,月光下翩翩而来的,是维纳斯生命的气息,石达开小妾佘三娘飞身投河的身影,凄凉而美艳,动人的美丽。大自然创造着无比动人的美,我们的笔,应该把那些美显示出来,可不知什么原因,当那些生命动人的美,仅刚刚显示了一下之后,就被不知谁操纵的生活揉碎了,像雨中的桐子花、桃花、梨花一样,纷纷绕绕,零落成泥。当然,我们已无法考证那一天,云蒸霞蔚的早晨,还是在金色的夕阳静静照耀着的山谷的黄昏,他们可曾在女儿泉瀑布前面或者下面,支起了画架,画起了裸体。真有这么一幅面,我想,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件十分美丽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来自乌溪小镇的专政队员是怎样跟在他们身后,还是早已埋伏在女儿泉瀑布旁边小木屋背后那片茂密的杉树林中。他们那次美丽的女儿山之行,肯定不会如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简单。要使一对年轻画家,走资派遗留下来的女儿和造反派男画家,像山涧流水一样完全融合,也不是十分简单轻松的事情。尽管处于“文革”时代,他们毕竟要么接受过高等教育,要么生活成长在那样浓郁的美术艺术环境中,他们对绘画的共同喜爱,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过那么多著名画家,他们知道画家和模特之间,有过那么多令人神往的美丽爱情浪漫故事和风流韵事,而且,无论现在的我们,还是当时的莫尚和易安,都很难分清楚,哪些是风流韵事,哪些是真正的爱情。他们也许在感叹不可琢磨的命运。莫尚带着忏悔的心态向她描述着“文革”中自己经历的一切,未来的路怎么走,莫尚认为首先要争取获得画某某像的权利。画了某某像又怎么办呢?他感到很茫然,未来,就像戈壁滩上行进着的少女,朦胧绰约、婉约飘渺,谈着谈着,他们渐渐忘却了自己究竟在哪里。也许,易安就是在属于他们的那个精神和心灵的小木屋里,把自己脱成了裸体,变成了模特,或者,易安的裸体和飞泻而下的泉水之间,相互映衬,成了一种生命形式的象征。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女儿泉瀑布下面那弯流水中脱成真正的裸体,他们也不可能在那片美丽风景中,把衣服脱光。因为,他们终究不是神话故事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那次偷偷上山旅行,也是和当地的山民住户有联系,他们晚上并没有在守山的草棚中过夜,他们在深山一位猎户家中住宿,并且交给了老猎户生活费,他们也没有睡在一起。他们带着画板画笔画架,去碧绿的女儿湖边写生,他们眼中的女儿山女儿湖青松林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水天一色,绿得晶莹,蓝得透明。简直就是一个洁净的童话世界,纯美的人间仙境。站在女儿湖边,他们激动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大自然的作品,不用增添色彩,只要真实描摹下来,完全可以和荷兰风景画派的艺术珍品媲美。那时的女儿山、女儿湖,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旅游处女地。满山葱绿,满湖碧水。水岸鸟声悠扬,深山猿猴啼鸣,蘑菇在树丛中静静开放,竹鸡的叫声在山谷中发出空旷的回响。也许看到这幅景象,他们都已沉醉。他们站在遥远的山巅,瞭望女儿泉瀑布在天地自然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