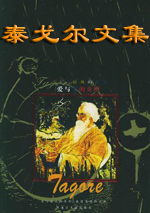琼瑶文集-第12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天天见面,他不了解为什么今天这么渴望着见到她?或者,因为这是她最后一晚做他的女儿了。门铃响了,他急急的跑去开门,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又本能的放慢了步子,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让女儿发现自己正在等她。打开了门,出乎意料的只是一个邮差,是从台南寄来的汇票,又是给絮洁的礼金!郑季波收了汇票,有点失望的关上大门,走上榻榻米。郑太太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锅铲,带着点不由自主的兴奋问:
“是絮洁回来了吗?”“不是,是邮差送汇票来,四弟给絮洁寄了两百块钱礼金!”“啊!”这声“啊”用着一种拉长的声调,微微的带着几分失望的味道。郑季波望着太太那矮矮胖胖的身子,那很善良而缺乏智慧的脸孔,以及那倒提着锅铲,迈着八字步退回厨房的神态,忽然对她生出一种怜悯的心情。不禁跟着她走到厨房门口。厨房桌子上堆满了做好的菜,预防冷掉和灰尘,上面都另外盖着一个盘子。锅里正好烧着一条大鲤鱼,香味和蒸气弥漫在整个厨房里,郑太太忙碌的在锅里下著作料,一面抬头看看他,有点不自然的笑了笑,似乎需要找点解释似的说:“红烧鲤鱼,絮洁顶喜欢吃的菜,孩子们都像你,个个爱吃鱼!”他感到没有什么话好说,也勉强的笑了笑,依然站在厨房门口,看看太太老练而熟悉的操作。鱼的香味冲进他的鼻子里,带着几分诱惑性,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了,郑太太把鱼盛进了碟子里。鱼在碟子里冒着热气,皮烧得焦焦的,灰白色的眼珠突了出来,彷佛在对人冷冷的瞠视着。
“几点了?”郑太太把煤油炉的火拨小了,在炉上烧了一壶水,有点焦急的问。“快七点了!”郑季波回答,望着桌子上堆满的菜。那种怜悯的情绪更具体而深切。
郑季波帮着太太把菜一样一样的拿到饭厅里。一共有六个菜一个汤,都是絮洁平日最爱吃的菜,黑压压的放了一桌子。郑季波笑笑说:“其实也不必做这么多菜,三个人怎样吃得了?”
“都是絮洁爱吃的,明天就是别人的人了,还能吃几次我做的菜呢?”郑季波没有接话,只看了她一眼。郑太太低垂着头、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束了一个发髻,使她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还要老些。她在桌子的四周不住的摸索着,彷佛在专心一致的安放着碗筷,其实一共只有三副碗筷,实在没有什么好放的。郑季波默默的走出了饭厅,回到客厅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要办的事早在前几天都办完了,现在倒有点空荡荡的闲得慌。伸手在茶几的盒里取了一支烟,他开始静静的抽起烟来,其实,他并没有抽烟的习惯,只在情绪不安定的时候才偶尔抽一两支。明天絮洁就要出嫁了,这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不是吗?天下没有女儿会陪着父母过一辈子的。先是絮菲,再是絮如,现在轮到絮洁,这将是最后一次为女儿办喜事了,以后再也没有女儿可以出嫁了。像是三张卷子,一张一张的答好了交出去,这最后的一张也答完了。原可以好好的松一口气,享受一下以后没有儿女之累的生活。但是,不知为了什么,郑季波感到一阵模糊的、空虚的感觉。这感觉正像烟蒂那缕轻烟一样:缥缈、虚无、而难以捉摸。“还没有回来吗?”郑太太走过来问,当然,她自己也明知道絮洁还没有回来,只是问一句而已。郑季波摇了摇头,茫然的望着郑太太那双改造派的脚,和那摇摇摆摆的走路姿势,隐约的记起自己和郑太太新婚的时候,每当他注视到她这一双脚的时候,她就会手足失措的把脚藏到椅子底下去,好像有一个莫大的缺点被人发现了似的。那时她很年轻,很容易脸红,喜欢用那对秀丽而温柔的大眼睛悄悄的注视着别人,当别人发现了她的注视时,她就会马上羞红了脸把头低下去。这一切都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韵致,可是,当时他却并不这么想,他只觉得她很幼稚、很愚昧、又很土气。
“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办好了?照相馆接过头了吗?出租汽车订好了没有?花篮和花都要最新鲜的,你有没有告诉花店几点钟送花来?”郑季波点了点头,表示全都办好了。他倒有一点希望现在什么都没有弄好,那他就可以忙忙碌碌的有事可干了。就像絮菲结婚那次一样,一直到走进结婚礼堂,他都还在忙着。但,现在到底是第三个女儿结婚了,一切要准备的事都驾轻就熟,再也不会像第一个女儿结婚时那样手忙脚乱了。郑太太搓了搓手,似乎想再找点问题来问问,但却没有找出来,于是走到书架旁边,把书架上的一瓶花拿了下来,自言自语的说:“两天没有换水了,花都要谢了,我去换换水去!”
郑季波想提醒她那是今天早上才换的水,却没有说出口,目送着她那臃肿的身子,抱着花瓶蹒跚的走出去,不禁摇摇头说:“老了,不是吗?结婚都三十几年了!”
年轻时代的郑太太并不胖,她身材很小巧、很苗条,脸庞也很秀丽,但是,郑季波并不喜欢她。当他在北平读书,被父亲骗回来举行婚礼时,他对她只有一肚子的怨恨。婚前他没有见过她,举行婚礼时他更连正眼都没有看过她一眼,进了洞房之后,她低垂着头坐在床沿上,他很快的掠了她一眼,连眼睛、鼻子、眉毛都没有看清楚,就自管自的冲到床前,把自己的一份被褥抱到外面书房里,铺在椅子上睡了一夜。他不知道她的新婚之夜是怎么过的,只是,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出乎意料的她竟站在他的面前,静静的捧着洗脸水和毛巾。他抬起头来,首先接触的就是她那对大而黑的眼睛:脉脉的、温驯的、歉然的望望他,他的心软了,到底错误并不在她,不是吗?于是他接受了这个被硬掷入他怀里的妻子。但,由于她没有受过教育,更由于她是父母之命而娶的女子,他轻视她、讨厌她、变着花样的找她发脾气。起先,他的母亲站在儿媳妇的一边,总帮她讲话,渐渐的,母亲却偏向他这一边来了,有一天,他听到母亲在房里对她说:
“一个妻子如果不能博得丈夫的欢心,那她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妻子,我们郑家从没有过像你这样无用的媳妇!”
她忍耐了这一切,从没有出过怨言。
“那时太年轻了,也太孩子气了!”
郑季波对自己摇了摇头,香烟的火焰几乎烧到了手指,他惊觉的灭掉了烟蒂,手表上已经七点半,望了望大门,仍然毫无动静。习惯性的,他用手抱住膝,沉思的望着窗外。月亮已升起来了,那棵凤凰木反而清晰了许多,云一样的叶片在风中微微的颤动着。郑太太抱着花瓶走了进来,有点吃力的想把它放回原处去,郑季波站起身来,从她手里接过花瓶,放回到书架上。这种少有的殷勤使郑太太稍感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他坐回沙发里,掩饰什么似的咳了一声嗽,郑太太看了看天色问:
“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菜都要冷了!”
“她除了烫头发之外还要做什么?为什么在外面逗留得这么晚?”郑季波问。“要把租好的礼服取回来,还要取裁缝店里的衣服,另外恐怕她还要买些小东西!”
“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些杂事办完呢?”
“本来衣服早就可以取了,絮洁总是认为那件水红色的旗袍做得不合身,一连拿回去改了三次。”
“何必那么注意小地方?”郑季波有点不满。
“这也难怪,女孩子把结婚的服装总看得非常严重的,尤其是新婚之夜的衣服,记得我结婚的时候……”郑太太猛然住了口,郑季波看了看她,努力的想记起她结婚那晚穿的是一身什么样的衣服,但却完全记不起来了。
八点十分,絮洁总算回来了,新烫的头发柔软而鬈曲的披在背上,怀里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进门就嚷着:
“妈!你看我烫的头发怎么样?好看吗?”
本来絮洁就是三个女儿中最美的一个,把头发一烫似乎显得更美,也更成熟了。但,不知为了什么,郑季波却感到今晚的絮洁和平常拖着两条小辫子时完全不一样了,好像变得陌生了许多。郑太太却拉着女儿的手,左看看、右看看,赞不绝口,絮洁兴奋的说:“我还要把礼服试给你们看看,妈,我又买了两副耳环,你看看那一副好?”“我看先吃饭吧,吃了饭再试好了,菜都冷了!”郑太太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说。郑季波想到饭厅桌上那满桌子的菜,知道太太想给絮洁一个意外的惊喜,不禁赞叹的、暗暗的点了点头。“喔,你们还没有吃饭吗?”絮洁诧异的望了望父母:“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你们快去吃吧,我到房里试衣服去!”
絮洁撒娇的对郑太太笑了笑,跑上去勾住郑太太的脖子,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又回过头对郑季波抛来一个可爱的笑靥,就匆匆忙忙的抱住她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自己的房里跑去。郑太太愣了一下,接着立即抱着一线希望喊:
“再吃一点吧,好吗?”
“不吃了,我已经饱得很!”
郑太太呆呆的望着女儿的背影,像生根一样的站在那儿,屋里在一刹那间变得非常的沉寂。郑季波碰了碰郑太太,用温柔得出奇的语调说:“走吧,玉环,我们吃饭去!”
郑太太惊觉的望了望郑季波,嘴边掠过了一丝淡淡的苦笑,摇着头说:“可爱的孩子,她是太快乐了呢!”
郑季波没有说话,走进了饭厅,在桌前坐了下来,郑太太歉然的望着他问:“菜都冷了,要热一热再吃吗?”
“算了!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桌上堆满了菜,鸡鸭鱼肉一应俱全。那盘红烧鲤鱼被触目的放在最中间,直挺挺的躺在那儿,灰白色的眼珠突了出来,好像在冷冷的嘲弄着什么。郑季波想起他和郑太太婚后不久,她第一次下厨房做菜,显然她已经知道他最爱吃鱼,所以也烧了一个红烧鲤鱼。那次的鱼确实非常好吃,他还记得每当他把筷子伸进那盘鱼的时候,郑太太总是以她那对温柔的大眼睛热切的望着他,彷佛渴望着他的赞美,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夸过她一句,他不了解自己何以竟如此吝啬?
他应该已经很饿了,可是,对着这满桌子丰盛的菜肴,他却有点提不起食欲来。但,虽然提不起食欲,他仍然努力的做出一副饕餮的样子来:大口大口的扒着饭,拚命的吃着菜,好像恨不得把这一桌子的菜都一口咽下去似的。一抬头,他发现郑太太正在看着他,猛然,他冲口而出的说:
“这鱼好吃极了!”“是吗?”郑太太注视着他,一抹兴奋的红潮竟染红了她的双颊,郑季波诧异的发现这一句赞美竟能带给她如此大的快乐。这才想起来,这一句可能是他生平给她的唯一的一句赞美。离开了餐桌,他默默的想:“这句话早该在三十二年前就说了,为什么那时候不说呢?”
回到客厅里,郑季波缓缓的踱到窗口。窗外的月光很好,这应该是一个美好而静谧的晚上,夜晚总带着几分神秘性,尤其是有月亮的夜。这该是属于年轻的情侣们的,躲在树叶的阴影下喁喁倾谈,望着星星编织着梦幻……可是,这一切与他都没有关系了,他已经老了,在他这一生中,从没有恋爱过,年轻时代的光阴完全虚掷了。
“爸爸!”郑季波转过身来,呆住了。絮洁垂着手站在客厅门口:穿着一件白缎子拖地的礼服,大大的裙子衬托出她那细小的腰肢,低低的领口露出她丰满圆润的脖子,头上扣着一圈花环,底下披着一块雾一样的轻纱,黑而亮的头发像瀑布一般披在肩上,耳环和项炼在她耳际和脖子上闪烁。但,这一切外在的打扮仍然抵不住她脸上那一层焕发的光辉,一种无比圣洁而热情的火焰燃烧在她微微湿润的眼睛里,嘴角带着个幸福而甜蜜的微笑。郑季波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他那跳跳蹦蹦,爱闹爱撒娇的小女儿。“我美吗?爸?”“是的,美极了!”郑季波由衷的回答,想到明天她将离开这个家而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不禁感到一阵难言的、酸涩的味道。是的,小燕子的羽毛已经长成了,你能够不让她飞吗?门铃忽然响了起来,郑季波望着女儿说:
“我去开门,你不要动,当心把衣服弄脏了,大概又是送礼的,或者是邮差送汇票来!”
“不是,一定是立康,他说过那边房子完全布置好之后还要接我去看一次!”絮洁说。
“可是,”郑季波站住了:“絮洁,我以为你今天晚上要留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的,你知道,这是……”他本来想说“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但觉得“最后”两个字有点不吉利,就又咽了下去。“喔,真对不起,爸,我们还有许多零碎事情要办呢!”絮洁有点歉然的望着郑季波。
这个“我们”当然是指她和立康,郑季波忽然觉得自己在和这未来的女婿吃起醋来,不禁自嘲的摇摇头。开了门,果然是立康,郑季波望着这一对年轻爱人间的凝眸微笑,脉脉含情的样子,目送着他们双双走出大门,猛然感到说不出的疲乏和虚弱,他身不由己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三十年来,这一付担子是何等的沉重啊!
郑太太关上了大门,走回客厅里。客厅好像比平常空旷了许多,郑季波无聊的又点燃一支烟,狠狠的吸了一口,把嘴做成一个弧形,想吐出一个烟圈。但是,烟圈并没有成形,只吐出了一团扩散的烟雾。郑太太找出了一个没有绣完的枕头,开始坐在他对面一针一线的绣了起来,空气中有点不自然的沉寂,郑太太不安的咳了一声,笑笑说:
“他们不是满恩爱吗?絮洁一定过得很快乐的!”
郑季波的视线转向了郑太太,他知道她又在给絮洁绣枕头了。她老了!时间在她的鬓边眼角已刻下了许许多多残酷的痕迹,那对昔日明亮而可爱的眼睛现在也变得呆滞了,嘴角旁边也总是习惯性的带着那抹善良的、被动的微笑。“可怜的女人,她这一辈子到底得到了些什么?”郑季波想。于是,他又模糊的记起,当郑太太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絮菲的时候,曾经脸色苍白的望着他,含着泪,祈谅的说:
“我很抱歉,季波!”她觉得抱歉,只为了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其实,这又怎能怪她呢?郑季波又何尝希望有儿子,他对于儿子或女儿根本没有丝毫的偏见,只是,因为对她有着过多的不满,因为恨她永远是他的包袱和绊脚石,所以,没有生儿子也成为他责怪她的理由了。“那时是多么的不懂事啊!”他想。
“记得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觉得这幢房子太小了,现在,房子却又太大了!”郑太太环顾着房子说,嘴边依然带着那抹温驯的微笑。郑季波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三个女儿,三个饶舌的小妇人,常常吵得他什么事都做不下去,现在,一个个的走了、飞了,留下一幢空房子、一桌没有吃的菜,和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我应该给你生一个儿子的,季波!”
郑太太注视着郑季波,眼光里含着无限的歉意。忽然,郑季波感到有许多话想对郑太太说,这些话有的早该在三十年前就说了的。他望着郑太太那花白的头发,那额上累累的皱纹,那凝视着他的、一度非常美丽的眼睛。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变得有点紊乱了,太多片段的记忆,太多复杂的感情,使他感到迷惑,感到晕眩。灭掉了烟蒂,他不由自主的坐到郑太太的身边,冲动的、喃喃的说:





![[综琼瑶]生若夏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