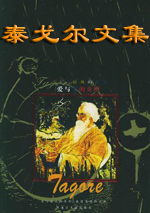琼瑶文集-第12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还早,我请你去凯莉吃一点冷饮吧,怎样?”
不要答应!不许答应!孟思齐想着,但是,她却笑吟吟的说:“好啊!”说着,她对他挥挥手:“孟思齐!再见!”
再见?谁和你再见?你居然和这个小流氓出去!你别糊涂!他跨前一步,想阻止,但,何子平已把她弄上了自行车前的横杠,带着她如飞而去。临行,何子平还对他抛过来充满调侃意味的一声:“再见吧,孟同学!”“我一定着了魔了!”孟思齐想着,靠在一棵榆树干上,怔怔的望着前面的女生宿舍。那幢两层楼的建筑耸立在黑暗的夜色里,窗口射出点点昏黄色的光线。他不知道她住在那一间,因此,对每一个窗口都觉得怪亲切,又怪刺心的。他就这样站着,直到女生宿舍的灯光纷纷熄灭,他才叹了口气,怏怏不乐的离开了那棵老榆树。
“明天晚上决不到这儿来了!”他想,但,第二天,夜色一来临,他又痴立在榆树下了。
就这样,许多日过去了,许多夜也过去了。他忘了他的书本,忘了天灾人祸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忘了康教授,忘了许许多多东西,他的笔记本里纵纵横横的写满了:“蓝裙子!大眼睛!”“该死的何子平!”“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哟!”最后那一条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里的歌词,他生平不会唱歌,但偏偏对这首歌的每一句,他想把它忘记都忘不了。
这天夜里,他站在榆树下,眼望着何子平把蓝裙子送回女生宿舍。他看看手表,已将近十一点。哼!你居然和这流氓玩到十一点才回来,你怎么如此不自重!他浑身冒火,气得鼻子里冒烟,悻悻然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同寝室的都已入睡,只有何子平还没有回来,他一面打开被褥,一面咬牙切齿。一会儿,何子平吹着口哨进来了,松领带,脱皮鞋,弄得满室声音,一股旁若无人的劲儿。躺在床上,还不肯安静,得意忘形的说:“老孟,你看蓝裙子怎么样?”
“哼!”孟思齐哼了一声,算是答案。
“蓝裙子长得还不错,就是赶不上小玲的丰满……”
你居然拿蓝裙子和舞女相比!孟思齐气得牙齿都磨出了响声。好,何子平,如果你不尊重她,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老子玩女孩子,经验多极了,”何子平仍然在大吹大擂:“像蓝裙子这种小嫩苗似的女娃娃,我只要小施手腕,她就逃不出我的掌心……”一句话没说完,孟思齐跳了起来,冲到何子平的床前,一只手拉起了何子平,另一只手握了拳就对着何子平的鼻子打下去。何子平惊喊了一声,挣扎着站起来,孟思齐的第二拳又当胸打到,何子平大叫:
“老孟,你疯了!”叫着,就跳起身,一头撞向孟思齐,孟思齐向后跌倒,撞翻了书桌。于是,全寝室都震动了,孟思齐打架,这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在大家把他们拉开以前,他们已打了个落花流水,何子平鼻青脸肿,孟思齐的眉毛上给眼镜片划了个大口子,血流了满脸,两人都狼狈不堪。但是,这次打架的原因,却没有一个人了解,包括何子平在内。
打架的第三天,孟思齐在走廊上碰到了康教授,康教授看着他头上扎的绷带,笑笑说:
“孟思齐,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便饭,我有点历史上的问题要和你谈谈。”惭愧!这么久没有和康教授研究学问了。晚上,孟思齐到了康教授家里,和康教授对坐在客厅里,康教授却久久不发一语。最后才笑笑说:“求学问虽然重要,可是,我总觉得人生大事也是应该解决的,思齐,你这份书呆子脾气简直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我以前追求你师母的时候,给她写了三年情书,一天一封,没有间断过,但是,怕她知道信是谁写的,见了面不好意思,我居然不签名,所以,你师母收了我三年情书,还不知道信是谁写的!”孟思齐笑了,正好师母走进来,也噗哧一笑说:
“真是书呆子!我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已经猜到是他的杰作了,他还以为我不知道,真不知道的话,怎么他家一遣人来说媒,我家就马上答应了呢!”
康教授和孟思齐都笑了出来。康师母说:
“来吃饭吧!”孟思齐一跨进饭厅,立即又呆住了!她!蓝裙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康教授和康师母直对他笑,蓝裙子却低俯着头,脸上红红的,眼梢带着一抹娇羞怯怯的微笑。
饭后,又是他和蓝裙子一起告辞出来,走在宽宽的人行道上,两人都默默无言,结果还是她先开口,低声说:
“为什么和人打架?”他讪讪一笑,不知如何回答,她接着说:
“昨晚你没有到榆树下来,我好担心,以为你病了,后来才知道你在前晚和何子平打架。”
原来他到榆树下去痴立的事,她竟然知道!他呆住了,停了脚步愣愣的望着她,她也回视着他,眼睛是热烈的,水汪汪的。他们注视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轻轻说:
“我从没有和何子平怎么样,他只是单相思罢了!”
他一把握住了她的胳臂,微一用力,她的头就靠在他的胸前。她深深的叹息了一声,偎紧了他,问: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
“植物园,怎样?”他说,这是他唯一想得出来的,适宜于谈情说爱的地方,虽然他从来没有试验过,但他知道那儿的浓荫深处,是多么有利于两心的接近。
他们依偎着向植物园走去。
九 斯人独憔悴
第一次见到他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那时,我是个腼腆的小女孩子,他是个腼腆的大男孩子。在大哥的那一群朋友里,就是他最沉默、最安静,总是静静的睁着一对恍恍惚惚的眼睛,若有所思的望着谈话的人群,或是凝视着天际的一朵游移的白云。那次还是我初次参加大哥的朋友们的聚会,拘束得如同见不得阳光的冬蛰的昆虫。大哥和他的朋友们那种豪迈的作风,爽朗的谈笑,以及不羁的追逐取闹,对于我是既陌生又惶恐。私下里,我称他们这一群作“野人团”,而他,却像野人团中唯一的一个文明人。
那天,我们去碧潭玩,大家都叫我小妹,取笑我,捉弄我,也呵护我。只有他,静静的看我,以平等的地位和我说话,好像我是和他们一样的年纪,这使我衷心安慰。因而,对他就生出一种特别的好感来,而且,他那对若有所思的眼睛令我感动,他说话时那种专注的神情也使我喜爱。当我们两人落在一群人的后面,缓缓的向空军公墓走去时,他问我:
“小妹,你将来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我还属于懵懂无知的年纪,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计划未来。因为他问话时的那种诚挚,使我反问了他一句:“你呢?”
“我?”他笑笑:“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过一份平平稳稳宁静无忧的岁月。”他望望天,好像那份岁月正藏在云天深处。“世俗繁华,如过眼云烟,何足羡慕追求?人,如能摆脱庸庸碌碌杂杂沓沓的世事纠缠,就是大解脱了。”
我茫然的注视着他,他的话,对我来说,是太深了些,但他说话的那种深沉的态度让我感动。他对我笑笑,彷佛是笑他自己。然后,他不再谈这个。我们跑上前去,追上了大哥他们,大哥笑着拍拍我的头说:
“哈,小妹,‘诗人’和你谈了些什么?”
“他有没有跟你谈人生的大道理呀?”另一个绰号叫“瘦子”的人嘲弄的问。“他告诉了你云和天的美吗?花和草的香吗?”再一个说。
于是,他们爆发了一阵哄笑。听到他们如此嘲弄他,我暗暗的为他不平,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值得笑的地方,虽然他有点与众不同。我不高兴大家这种态度,于是,我走近他,他看我,笑笑,似乎对那些嘲弄毫不在意。看他脸上那种神情,倒好像被嘲弄的不是他,而是大哥他们。他的满不在乎和遗世独立的劲儿,使我为之心折。
那时,我才刚满十五岁。
然后,有一段时间,他这个文明人杂在野人团里面,经常出入我的家,我也常常和他们一起出游。不过,那段时间很短暂,没两年,野人团就随着大哥的大学毕业,随着他们要受预备军官训练而宣告解散。大哥受完军训后,野人团中的一些人虽然又恢复到我家走动,他却始终没有再露面过。有时,我想,他或者已找到了他的境界,而隐居在什么深山幽谷之中,度那与世无争的宁静岁月。不过,在我那稚弱懵懂的年龄,还确曾为他耗费过不少精神,徒劳的浪费了不少的怀念。最后,在我逐渐的成长和时光如水的流逝中,我终于埋葬了对他的这段不成形的、朦胧的、幼稚的感情。
此后,一年一年的过去,他在我记忆中逐渐模糊,终至消失。到底十五、六岁还是个幼小的年龄,而接踵而来的生活中又充满了太多绚丽的色彩,我度过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少女时期,然后,和野人团中一个虽平凡,却稳重的青年结了婚,人人都满意这个婚姻,包括我自己。
再和他见面,距离初次见到他,已经是整整十年了。十年,给每一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大哥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也不但已为人妻,且将为人母了。
当外子带我出席他们的校友会时,我是再也想不到会和他见面的。校友会在外子母校的大礼堂举行,人很多很乱,主要就是大家聚聚,联络联络感情。有个规模不小的聚餐,聚餐之后是舞会。我因为正害喜,对于室内那混浊的空气和嘈杂的音乐感到不耐。而外子与几个旧日的好友碰到了头,立即聚在窗边,高谈阔论了起来。听他们谈了一些彼此的事业,年纪轻轻的就唏嘘着年华的老大,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了。但外子正谈得高兴,看样子并没有告辞的意思,我只得悄悄的溜出了大礼堂,到外面清新的夜色中去透透气。
礼堂外面几步之遥,有个小小的喷水池。我踏着月色,向喷水池走去,站在池边,看着那喷出的水珠在月光下闪烁,看着平静的水面被粒粒落下的水珠击破,别有一种幽静的美。我不知不觉的在池边坐下,凝视着自己的影子在水波中荡漾。我是那样出神,竟没有发觉有人走到我的身边,直到一个声音突如其来的吓了我一跳:“小妹,你好?”我迅速的抬起头来,面前站着的男人使我不能辨识,一袭破旧的夹克,敞着拉炼,里面是件肮脏的衬衫,和一条灰色卡其布的裤子。乱蓬蓬的头发下有张被胡须掩埋的脸,只看得见在夜色中闪烁着异样神采的一对眼睛。衣领敞开,翻起的夹克领子半遮着下巴。瘦瘦长长的身子挺立在月光下,像个幽灵。我迟疑着,比迟疑更多的,是胆怯。
“不认得我了?”他的声音平平静静的,没有高低之分。“以前你大哥他们叫我诗人,记得吗?”
“诗人?”我一惊,实在没料到当年那个沉默腼腆的大男孩子竟是面前这个落拓潦倒的中年人,难道十年的光阴竟能把一个人改变得如此之大!我正错愕之间,他已自自然然的在我身边坐下,从夹克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问我:
“抽烟吗?”我摇摇头,他自顾自的燃起了烟,然后静静审视着我。现在距离近了,我更可以看出时间在他身上所刻下的痕迹,他双颊下陷,颞骨突出,憔悴得几无人形。再加上那奕奕有神的眼睛,显得十分怪异。这突然的见面使我口拙,尤其是他那惊人的改变,令我简直不知说些什么好。
“这些年好吧?你长大了。”他说,声音依然那样平板,没有带出一丝情感来。“我已经结了婚……”我说。“我知道。”他打断了我:“很幸福吧?”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恢复了平静,望着他说:
“你呢?这些年躲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你希望的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凝视我,双眼灼灼逼人的燃着异样的光,但我直觉的感到他并没有看见我,他的眼光透过了我的身子,望着的是虚无缥缈的夜色,和虚无缥缈的世界。
“我几乎找到了,”他说,嗒然若失的。“可是,我又失去了。”“怎么回事?”他深深的抽了一口烟,再把烟喷出来,烟雾在寒夜里很快的扩散了。他注视烟蒂上的火光,沉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轻轻的问:“要听故事吗?”我没有说话,只用手抱着膝,做出准备倾听的姿态来。他望着我,这次他是真的在看我,好半天,他说:
“你好像还和以前一样,喜欢听而不喜欢说。好久以前,我觉得你和我是同类的,现在也这么觉得。那么,你真的幸福吗?你的丈夫能使你获得宁静和快乐吗?”
我皱皱眉,我不想去分析,于是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说了,用那种平板而没有高低的声调。
“我一直渴望着一种境界,你知道。”他说,微仰着头,注视着寒空里的星光。“我想找一个安静而幽美的所在,我厌倦都市的繁华和一般人追逐名利的生活。因而,当我受完了预备军官的训练,而凑巧知道东部山区中出了一个国校教员的缺时,我竟毫不考虑的接受了这个工作。”他看了我一眼:“你会奇怪吗?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山地里去教小学?”
“不。”我说。“可是,我的家人却觉得很奇怪,在这儿,我必须先告诉你我的家庭。我父亲是早年留德的学生,学工程,然后一直在大学中执教。我母亲出自名门望族,毕业于杭州艺专,是个薄负微名的女画家。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我父亲学的既是科学,受的又是新式教育,所以,总力言他是个男女一视同仁的父亲,但是,他却是个最重男轻女的父亲,他宠爱我,优待我视我如同瑰宝。母亲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家里的地位一直高高在上。父亲让我受最好的教育,期望我能出国留学,然后出人头地。他那望子成龙的苦心,为人子者,也真当感激了。所以,当我决定到山地去教书时,他如同挨了一记闷棍,整整三天三夜,他和我母亲,还有我的姐妹,苦口婆心的劝我放弃我这荒谬得‘不可思议’的计划。母亲和我的姐妹甚至泪下。但是,我终于不顾一切,提着一口小皮箱,走入了山区。
“那学校坐落在半山的一个村落里,简陋到极点,那地区荒凉贫瘠,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有人愿意定居在这儿。所有的居民,都贫苦到衣不蔽体,六七岁的孩童,赤身露体都是常事。学校中一共只有五个人管理,一个是校长,一个算术教员,一个常识教员,加我这个国语教员,另外还有个管理洒扫的校工。校长姓林,年约四十几岁,是本省人,能说一口很好的日语。对于我的来到,他表现了适度的欢迎,然后将我安插在一间半新旧的屋中。
“我负担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国语课程,事实上,每年级只有一班,班级越高,人数就越少,因为一般十二、三岁的孩子,都要帮家里做事,家长就不肯放他们出来读书了。功课看起来忙,事实上并不太忙,只是,学生程度之低,和天资的愚鲁,使我一上来就大失所望。我置身于一群破破烂烂,毫无天份的孩子之中,看着的只是山脊和梯田,竟有种被欺骗似的感觉,这与我幻想中那宁静幽美的神仙境地,简直相差得太远太远了。可是,逐渐的,





![[综琼瑶]生若夏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