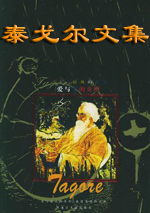琼瑶文集-第129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者──是的。”他不能用谎言欺骗自己,或欺骗她。自己是骗不了的,骗她就太残忍了。拉住她的手,他说:“我们走吧!这里的范围太小了。”
重新上了车,他发动了车子,他们没有往回去的路上走,而是一直向前,沿着海岸的公路疾驰。
“现在去什么地方?”姸青问。
“金山。”他头也不回的说,把车行的速度加到时速八十公里。他内心的情绪也和车速一般狂猛。
金山距离石门很近,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已经到了青年育乐中心的广场上。把车子开到海滨的桥边,停下车来,他们在辽阔的沙滩上踱着步子。她穿着高跟鞋,鞋跟不住的陷进沙里去。
“脱下鞋来吧!”他怂恿着。
她真的脱了下来,把鞋子放在车里,她赤着脚走在柔软的沙子上。他们沿着海边走,两组脚印在沙滩上留了下来,她的脚细小而白暂,在海浪里显得特别单薄。这是深秋,海边只有海浪的喧嚣和秋风的呼号,周遭辽阔的海岸,找不到一个人影。他的手挽着她的腰,她的长发在海风中飘飞。
“你怎么嫁给他的?”他问,不愿提起伯南的名字。
“不知道。”她迷惘的说:“那时爷爷刚死。”
“你原来和你祖父在一起的吗?”
“是的,我六岁的时候,爸爸离家出走了,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九岁的时候妈妈改嫁了,我跟爷爷一直在一起,我们相依为命,他带我来台湾,然后,五年前,他也去了。”
“哦!”他握紧她的手,站住了,注视她的眼睛,喊着:“你是那样一个小小的女人,你怎么接受这些事情呢?”
她微笑,但是泪珠在眼里打着转转。
“爷爷死了,我觉得我也死了,他帮我办丧事,丧事完了,我就嫁给他了,我觉得都一样,反正,我就好像是死了。”
“这个家并不温暖,是不是?”
“一个很精致的坟墓,我埋了五年。”
“却拒绝被救?”
“怕救不出来,再毁了别人。”
“但愿与你一起烧死!”他冲动的说,突然揽住了她,他的唇灼热的压住她的唇,手臂箍紧了她,不容许她挣扎。事实上,她并没有挣扎。那压迫的炙热使她晕眩,她从没有这样被人吻过。他的唇贴紧了她的,颤栗的、烧灼的吮吸转动,那股强劲的热力从她唇上奔窜到她的四肢、肌肉、血管,使她全身都紧张起来。终于,他抬起头来,捧住她的脸凝视她,然后,他把她的头揽在胸前,温柔的抱着她。她的耳朵贴着他的胸口,那心脏正疯狂的擂击着。
“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知道我完了。”他低语:“我从来没有动过这样强烈的感情。”
“包括你的她?”她问,感到那层薄薄的妒意,和海浪一般的淹了过来。
“和她的爱情是平静的、稳定的、顺理成章的。”他说。
“你们的感情好吗?幸福吗?愉快吗?”
“看──从那一方面讲。”
“你在回避我,”她敏感的说,叹息了一声。“但是,我已经了解了。”
“了解什么了?”
“你们是幸福的。”她低语。“她很可爱吗?”
“何必谈她呢!”梦轩打断了她。“我们往前走走吧!”
他们继续往前面走去,他的手依然挽着她的腰,两组脚印在沙滩上蜿蜒的伸展着。姸青低着头,望着自己的脚,那样缓慢的一步步的踩在那柔软的沙子上。等到涨潮的时候,那些足迹全会被浪潮所带走了。一股怆恻的情绪涌了上来,酸酸楚楚的压在她的心上,喜悦和激情都跟着浪潮流逝。人生不是每件事都能公平,有的人生来为了享福,有的人却生来为了受苦。
“你不高兴了。”他低徊的说,叹了口气。
她有些吃惊,吃惊于他那份敏锐的感应能力。
“我一向生活得非常拘谨,”她说,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我不习惯于──犯罪。”
“你用了两个奇怪的字,”他不安的说:“爱情不是犯罪。”
“看你用哪一种眼光来看,”她说:“许多东西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你也知道,对吗?”
是的,他也知道,知道得比她更清楚。来找她的时候,所凭的只是一股激情,而不是理智。他没有权利搅乱她的生活,甚至伤害她。低下头,他沉默了。有只寄居蟹背着一个丑陋的壳从潮湿的沙子里爬了出来,蹒跚的在沙子上踱着步子。姸青弯腰把它拾了起来,放在掌心中,那青绿色的壳扭曲而不正,长着薄薄的青苔。那只胆怯的生物已经缩回了壳里,躲在里面再也不肯出来。
“看到了吗?”姸青不胜感伤:“我就像一只寄居蟹,不管那壳是多么丑陋和狭小,我却离不开那个壳,我需要保护,需要安全。”
“这壳是安全的?”梦轩问,“你不觉得它脆弱得敌不住任何打击,轻易就会粉碎吗?”
“可能,”姸青抬起眼睛来:“但是,总比没有好,是不是?而且,你不该做这个敲碎壳的人哪!”
他为之结舌,是的,尽管这壳脆弱、狭小、丑陋,他有什么权利去敲碎它?除非他为她准备好了另外一个美丽而安全的新壳,他准备了吗?注视着姸青悲哀的眼睛,他懂了,懂得她的意思了。握住她的双手,他诚挚的、无奈的、而凄楚的说:“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会很小心,不去敲碎你的壳,除非……”他咽住了,他没有资格许诺什么,甚至给她任何保证和希望。她是一只寄居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他同样没有权利去敲碎另外一个壳!
她把她纤细的小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微笑的注视着他的脸。
“我们都没有防备到这件事的发生,是不是?我丝毫都不责备你,在我这一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过,我还求什么呢?我终于认识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你聪明,你智慧,你热情,所以你要受苦。我是生来注定就要受苦的,因为我属于一个遗失的年代,却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让我们一起受苦吧,如果可以免得了……别人受苦的话。”
他望着她,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他就这样子望着她。那不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她有见识,有度量,有勇气!在她而前,他变得渺小了。他们对视良久,然后手牵着手站了起来,今天,虽然没有很好的阳光,但总是他们的,至于明天……他们都知道,所有的明天都是破碎的、阴暗的,他们没有明天。
离开了沙滩,他们走向草地和松林,在一棵松树下坐了下来。她被海水所浸过的脚冰冰冷,他脱下西装上衣,裹住了她的脚(他多么想永远这样裹住她,给她保护和温暖!)他们依偎着,谈云,谈树,谈天空,谈海浪,只是不再谈彼此和感情,当他们什么都不谈的时候,他们就长长久久的对视着,他们的眼睛谈尽了他们所不谈的东西:彼此和感情。
黄昏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台北。在一家小小的餐厅里,他们共进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时间越到最后就越沉重,他们对视着,彼此都无法掩饰那浓重的怆恻之情。“刚刚找到的,就又要失去了。”他说,喝了一点儿酒,竟然薄有醉意。
“或者没有失去,”姸青说,牙齿轻咬着杯子的边缘:“最起码,在内心深处的某一个地方,我们还保有着得到的东西。”
她对他举了举杯:“祝福你!”
他饮干了杯子里的酒。
离开了餐厅,他送她回到家门口,停下了车子,他拉住她的衣角。
“在你走以前,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的全名叫什么?姓什么?”
“许。”她说,他们认识得多深刻,而又多陌生!“许姸青。爷爷在世的时候,叫我姸姸,也叫我青青。有的时候,他叫我紫娃儿和小菱角花。”
“许姸青。”他低低的念着,一朵飘浮在雾里的、紫色的睡莲!
她走了,紫色的影子消失在夜雾里,他坐在那儿,没有把车子开走。燃起一支烟,他在每一个烟圈中看到那抹淡淡的紫。附近人家的收音机里,飘出了迷离的歌声:“……如今咫尺天涯,一别竟成陌路……”
是他们的写照吗?何尝不是?
永远是这样的日子,千篇一律的,金钱、数字、表格、进口、出口……以及那些百般乏味的应酬,国宾、统一、中央酒店……日子就这样流过去了,这是生活,不是艺术。一天的末尾,拖着满身的疲倦(岂止满身?还有满心!)回到家里,孩子的笑容却再也填不满内心的寂寞。那蠢动的感情,一旦出了轨,彷佛千军万马也拉不回来,整日脑子里飘浮的,只是那一抹浅紫,在海边的,在松林里的,在餐厅中的,那亭亭玉立的一抹浅紫!
手放在驾驶盘上,他的眼光定定的望着前面的街道,他看着的不是行人和马路,而是一团紫色的光与影,胸中焚烧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欲望,她怎样了?
车子到了家门口,时间还算早,不到十点钟,美婵和孩子们不知睡了没有?但愿他们是睡了!把车子倒进车库,他只想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用钥匙开了大门,满屋的喧哗声已溢出门外,一个女高音似的声调压倒了许多声音,在夜色里传送得好远好远:“美婵,你不管紧一点啊,将来吃亏的是你,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吧!”
梦轩站在花园里,下意识的皱紧了眉头,他知道这是谁来了,美婵的姐姐雅婵,而且,从那闹成一团的孩子声中,他猜定他们是全家出动了,那三个有过剩的精力而没有良好管束的孩子一定已经在翻天覆地了。走进客厅的门,果然,陶思贤夫妇正高踞在客厅中最好的两张沙发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溜排下来,成等差级数,是十二岁的男孩贤贤,十岁的女孩雅雅,和八岁的男孩彬彬,现在正把小枫小竹的玩具箱整个倒翻在地上,祸害得一塌糊涂。即将考中学的贤贤,还拿着把玩具手枪,在和他的弟弟展开警匪大格斗。雅雅酷肖她的母亲,有张喜欢搬弄是非的嘴巴和迟钝的大脑。这时正坐在地毯上,把小枫的三个洋娃娃全脱得一丝不挂,说是组织天体营,小枫则张着一对完全莫名其妙的大眼睛,好奇的望着她。小竹是孩子们中最小的,满地爬着在帮那两个表哥捡子弹和手榴弹。全房间闹得连天花板都快要塌下来了,而美婵安之若素的坐着,好脾气的听着雅婵的训斥,思贤则心不在焉的翘着二郎腿,把烟灰随便的弹在茶几上、花瓶里和地毯上。
梦轩的出现,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小枫,丢下了她的表姐,她直奔了过来,跳到梦轩的身上,用她的小胳膊搂紧了梦轩的脖子,在他的面颊上响响的亲了亲。
“爸爸,你这么晚才回来!”软软的童音里,带着甜甜的抱怨。
“今天还晚吗?你看,你们还没睡呢!”梦轩说,放下了小枫,转向陶思贤夫妇,笑着说:“什么时候来的?叫美婵把谁管紧一点?”
“你呀!”美婵嘴快的说,满脸的笑,完全心无城府而又天真得近乎头脑简单。“姐姐说,你这样常常晚回家是不好的,一定跟那些商人去酒家谈生意,谈着谈着就会谈出问题来了,会不会?梦轩?”
“美婵,你……哎呀呀,谁叫你跟他说嘛!”雅婵不好意思的红了脸,再没料到美婵会兜着底抖出来,心里暗暗的咒骂着美婵的无用,在梦轩面前又怪尴尬的不是滋味,梦轩心中了然,只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无聊,奇怪她知道来指导美婵,怎么会管出一个花天酒地的陶思贤来?笑了笑,他不介意似的说:“美婵,别傻了,你姐姐跟你开玩笑呢!”
“是呀!”雅婵立即堆了一脸的笑:“我和你开玩笑说说吗,你可别就认真了,像梦轩这样的标准丈夫呀,你不知道是那一辈子修来的呢!”
梦轩在肚子里暗暗发笑,奇怪有些女人的脑筋真简单得不可思议,在椅子中坐了下来,陶思贤立即递上了一支烟,并且打燃了打火机。梦轩燃着了烟,望望陶思贤说:“你的情况怎么样?”
“还不是要你帮忙,”陶思贤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在瑞芳那边开一个煤矿,这是十拿九稳可以赚钱的事情,台湾的人工便宜,你知道。现在,什么都有了,就短少一点头寸,大家希望你能投资一些,怎样?”
“思贤,”梦轩慢吞吞的说:“你知道如今混事并不容易,我那个贸易行是随时需要现款周转的,那样大一个办公厅,十几二十个人的薪水要发,虽然行里是很赚钱,但是,赚的又要用出去,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发达,我根本就没办法剩下钱来……”
“得了,得了,梦轩,你在我面前哭穷,岂不是等于在嘲笑我吗?”思贤打断了他,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情来:“谁不知道你那个贸易行现在是台北数一数二的?我们从大陆到台湾来,亲戚们也没有几个,大家总得彼此照应照应,是吧?梦轩,无论如何,你多少总要投资一点吧?”
梦轩深深的抽了一口烟,心里烦恼得厉害。
“你希望我投资多少?”
“二十万,怎样?”陶思贤干脆来个狮子大开口。
“二十万?”梦轩笑了:“思贤,不是我不帮你,这样大的数目,你要我从何帮你呀?”
“哎哟,妹夫呀,”雅婵插了进来:“只要你肯帮忙,还有什么帮不了呢?就怕你大贵人看不起我们呀!”
“姐姐,”美婵不好意思的说:“你怎么这样说呢?梦轩,你就投资一点吧,反正是投资吗,又不是借出去……”
“是呀,”雅婵接了口:“说不定还会大赚特赚呢,人总有个时来运转的呀,难道我们陶家会倒楣一辈子吗,何况,沾了你们夏家的光,也沾点你们的运气……”
“这样吧!”梦轩不耐的打断了她:“这件事让我想一想,如何?思贤,你明天把这煤矿的一切资料拿到我办公室去,我们研究研究,怎样?”
“资料?”思贤愣了一下:“你指的是什么?”
“总得有一点资料的呀,”梦轩开始烦躁了起来:这一切是多么多么让人厌倦!“这煤矿的确定地点、地契、矿藏产量、已开采过的还是尚未开采、合伙人是谁、手续是否清楚……这种种种种的资料,我不能做个糊里糊涂的投资人呀!”
“我懂了,”陶思贤慢条斯理的说:“你不信任我,你以为我在骗你……”
“妹夫呀,你也太精明了,”雅婵尖锐的嗓子又插了进来:“想当初,美婵还跟着我们住了好多年呢,你家小枫的尿布还是我家破被单撕的,我们现在环境不好,妹夫不帮忙谁帮我们……”
“好了,好了,”梦轩竭力的按捺着自己,“如果你们缺钱用,先在我这儿挪用吧,我不投资做任何事情,我的钱全要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我们不是来化缘的,”思贤一脸怒气:“梦轩,你似乎也不必对自己亲戚拿出这副脸孔来呀!”
“是呀!”雅婵夫唱妇随:“打狗也还要看看主人是谁呢!”
“梦轩,”美婵一脸的尴尬:“你今天是怎么了?谁给你气受了吗?”
梦轩深吸了一口烟,烦躁得想爆炸,孩子们又吵成了一团,在一声尖叫里,小竹被彬彬的手枪打到了眼睛,突然哭了起来,小枫的一个洋娃娃被折断了手臂,抽抽噎噎的向父亲求救。梦轩一个劲儿的抽烟,只听到孩子的叫声、哭声、吵声





![[综琼瑶]生若夏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