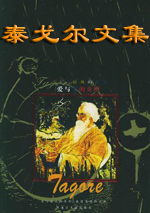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ļ�-��31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ļӴ��ˡ��ſ����죬�����������ĸ�������������������ҹĻ���ţ���Ÿ���裬ȥȥȥ��η����������ѣ������ᳪ��ȥȥȥ��η���������ˣ�������˹��ȥȥȥ��η���������ˣ�������˹��ȥȥȥ��η�����
������������ͣ�ˣ�����Ҳͣ�ˣ��������˼����ӣ��۹ⶨ�������Ŵ��ӡ�Ȼ�������˸����������²�Ū�ż�������������������ǧɽ��ˮ�������˾��κ��ˣ���Ÿ���ϵ�Ѱ����Ÿ���ϵ�ϣ��������Ǩ�ţ�������������Ÿ��Ȼ����Ѱ�����ķ���
�������������ٶ�ͣ�ˣ������ż�����һ��Ҳ���������ţ�����Ѿ��붨�˵���ɮ�����ţ�����Ȼ����������ļ�����һ�����˵��ڴ��ϣ���ͷ����������ͷ�����ʼ���еġ���ʹ�������������
������������Ѹ�ٵĴ��ˣ���̫̫���˽������غ÷��ţ�����ֱ�ߵ�Ů���Ĵ�ǰ��ҡ�������ļ������˵���������ˣ������ˣ������ˣ���
����������Ŷ�����裬�������ѵ���������ͷ��ѹ�ֵ�Ʈ�˳�����
�����������Ҿ�����Ҫ���ˡ���
������������˵������̫̫�º͵���߳�ţ���ת�������ѵ����ӣ������������˹���������ͷ�����ң���������ǽ壬���������۾�ȴ���������������������ţ���������������ĸ�ס�
������������ģ���������˵������Ҫ���ˡ���Ϊ�Ҷ��κ��¶�û����Ȥ�ˡ����������裬��ʫ�������ѣ����У���������Ц��Ū�ˡ���û��һ�������Ҹ���Ȥ�ģ��Ҿ����һ��������ˡ���
����������̫̫������Ů������һ������Լ��������˽�������ӣ���֪��������Ը����֪������˼�룬Ҳ��֪������������
�����������ǣ����ڣ��������������ġ������ġ�������������ӣ�����Ȼ�����Լ������˽������˽�ü������Կ�����������ȥ��
�������������ѣ���������˵����Ů���Ĵ��������������������ŷ������һ�����𣿡�
��������������ŷ��������ŷ��������ϵ����������Щ�����˵�������Ѿ��þ����������ҵĻ����ˡ���
�������������ۣ�����̫̫�����̵�˵������Ϊ����Ľ���ˣ������������IJ����ˡ���
�������������Ѿ����������ţ���������������ĸ�ס�����û����Ϊĸ���³�����Ľ�����������ֶ����棬Ҳû�з�ŭ���������ó��棬�����ò������յ������ˡ�
�����������ǵģ���Ľ�����������ϵ�˵�������벻����ʲ�۷�������ɱ��������
���������������������𣿡���̫̫�ʡ�
�����������ǵģ��Һ�����������ɱ��������
������������Ϊ��û����ŷ�������������㻶������Ϊ��û����һ���к����������������������Ϊ��û�����С���������IJ�Ū�𣿻�����Ϊ����������һ����ǿ��һ�����ԣ�һ���Ը��������������κΣ���
����������Ŷ�����裡�������Ѿ�����������Ϊ��ϣ�����ĸ��飿����Ϊ�Ұ�����������
�����������㲻���𣿡���̫̫�����ķ��ʣ�Ŀ������Ķ���Ů����
�������������ѣ�����̾Ϣ��˵����������߲��Ǹ������裬������߲���������˽��㣬�����㣬ʹ����֡����ǣ�����Ͼ������������۶��꣬�������۶ྭ�飬���룬���˽Ⱞ�飡���ѣ�����Ҳ�ǹ������ģ���
�������������ѵɴ����۾���ע����ĸ�ס�
��������������Ȼ��̫���������Ľ��֮�䣬������һ���ʣ�����̫̫����˵�������ǣ������������ģ�����֪���������ۣ������㲻�ã����ѡ�������������ϷŪ��������������Ǹ������ˣ����������ԵĽ����������ģ���
�������������裡����������ŭ�ĺ�������ֻ֪����ϷŪ�����㲻֪����ҲϷŪ�����������ϣ���Լ�ҳ�ȥɢ�����Ҷ�������������ģ���֪��������˵Щʲ�ۣ�������
�������������ø����ң�����̫̫˵�����ҿ��Բµ������ѣ�����Ū�������ٱ����㡣��������ֻ����Ĵ�⫣��뿪�˶������䣬����һ����ֱ˴˴̵��ۡ���ʵ�ϣ������మ������ʹ�࣬ȴ˭Ҳ������һ������
�������������裡�������Ѿ�㵵Ĺֽ��š����㾹Ȼ��Ϊ�Һ����మ�𣿡�
���������������𣿡���̫̫�ٷ�����һ�䡣������������㣬�������ϾͲ��ᵽ���Ǽ��������ˡ���
���������������������������ң��������Ѵ�У����������Ǵ����������ҵģ���
�������������ѣ�����Ҫƽ��һЩ����һЩ����������������ʱ����֦˵�������³��ģ�һ���ž����㣬���ԣ�����Ϊ�����ġ������ڿ�����������ŷ����������������㣬�ͻ�֪����м����IJ����ڡ������ֱ��ֳ�һ�������첻�����̬���������ѹ�������ˣ����㻹ƫƫ��װ�����ĺ�ŷ�����ܳ����������룬���ѣ��������������������أ���
�������������Ѵ��ˣ��Ӵ�������������������ϥ�����°ͷ���ϥ�ϣ�����ͷ����˼�Ŀ���ĸ�ס������ϵ�����Ѿ����ˣ��۾���������һ�������Ĺ������
������������˵�����ѣ�����������㣬�����ۻ�������������أ���֪�������ѣ��������ϵ����Σ��κ�һ�����˶���������ŷ�����Ѿ��õò������ˣ���
���������������������أ��������ѷ��յĽУ����ѵ�Ҫ�Ҵ����ĵĸ��������Һ�ŷ����ֻ����ͨ���ѣ�����û���κι�ϵ�𣿡�
�����������㲻�ش����ģ�����̫̫Ц������������ֻҪѹ��һ����Ľ�������Ļ�������ֻҪ��������ȥ�������ĸ��顣���ѣ�����̫̫�Ȱ��ĸ���������������ͷ�ҷ�������һ�����ӱ��һ��Ů�˰ɣ��������Ե�ʱ��Ӧ���Ѿ���ȥ�ˡ�Ů�˸���Ů�Ե����ᡣ��
�������������ѳ�Ĭ�ˡ����Σ���̧���۾������������ã��ע����ĸ�ס�
�����������裬��Ϊʲ�۰���Ľ��˵������ϲ����Ľ��ʤ��ŷ�����𣿡�
����������̫̫Ц�ˡ�
���������������������Ǻú��ӣ������г�����Ҳ���ж̴�������˵������������ϲ��˭����û�й�ϵ����������ϲ��˭���㵽��ϲ��˭�أ����ѣ���
��������������ĬȻ���
�������������Ǹ��ܿ�����ĸ�ף�һֱ��̫�����ˣ��Ҵ�û�и����������顣����̫̫������������˵����������Ҳ�������㡣��ֻ�������㣬��������ע�ⲻ�����£��������������˵��£�Ȼ��һ�ж������Լ�������������ƽ������ͷ����
�����������㵱Ȼ֪����ŷ���Ѿ���ʽ��̸����ϣ�����ŷ������Щ��顣��
������������˵����Ҫ�����𣿡����������յ�˵��
������������˵���ģ����ӡ������ǵ��źܶ��˵��棬������Ľ�����棬�������������δ���
����������Ŷ���죡�������ѷ��˷��۾�����ֻ��ɵ�ϲŻ�����ֻ����棡��
����������ֻ��ŷ��������Ľ����������ɵ���أ�����̫̫��Ц��˵���Ӵ���վ��������������ϸ����һ��ɣ����ѡ����ڣ�Ӧ�úúõ�˯һ���ˣ������Ѿ���������������������ѽ��������ˣ���������ݵ��⸱���ӣ��°Ͷ�Խ��Խ���ˡ�ÿ�����ϲ�˯������Ȧ�������ˡ���������̾����������������������Ľ��Ҳ�ݵ������أ���
��������ת�����ӣ������ĵ��߳��˷��䣬�����˷��š���������һ���������Ƕ���㶡�
���������ܾúܾã������Ѿ��������ţ�����˯�⡣������������Ľ�����õ����飬���������Ǽ����ִ������ͷ�������������ϣ������뵽���賿��ɢ�������뵽��ǰ��Լ�ᣬ�¼��µ���ۣ�����۶����ϵij������ˣ�˭˵�������������������ɺ���ɵġ�˭˵���������Ĺ��¾���һ������żȻ��������Ľ����������ʶ��������������ŵĴ����𣿻��ߣ�ڤڤ���и������ɣ��ڰ��������������ϡ����ǣ����ڣ����ɵĹ����Ѿ������ˣ�ʣ���������ˣ����Dz����Լ�����ġ�
�����������ߣ����������ѵ�һ����������˼����Ҳ���ߣ������������ɺ��ӿ�����˵ĵ�һ������֮���ڹ��˳����İ�Сʱ�Ժ�����Ȼ���������ˡ��������ڿ����ţ������������˷��ţ������������գ���������ָ��ȴ���ʵIJ����š�
�������������˿����������˵绰��Ͳ����������Ͳ��ѹ���ؿڣ������۾�����Ĭ�����өrϣ�����ڼң�ϣ�������ӵ绰��ϣ������û˯��ϣ����Ҳ����������ϣ����ϣ����ϣ���������۾���������������������ҵĵ绰���롣
������������Ͳѹ�ڶ����ϣ���������ð�ź�������ͷ�Ժ���ǻ�ﶼ�Ⱥ��ġ���Ͳ�У�������һ�������˵ڶ��������˵����������ǣ������˵����죬ÿһ�춼�������ص��������������ϡ�
�����������ڣ�����ֹͣ��������������Ͳ����ιι������һλ�����Է�˵��
���������ǣ�������������������лл�죡���ſ��죬��ˮȴ������ۿ���ȥ�������촽������������˿����������
����������ιι����˭ѽ������Ľ�������������˲��ͣ�����Ȼ����ŭ�뻵Ƣ��֮�С���˵��ѽ��ιι����ʲ����Ц����ҹ�����ģ���������
��������������һ�����Է��Ҷ��˵绰��
�����������������ֱ���ȥ�˼��ϵ���ۡ����治�����������Լ�˵�������������ڵ�������û�����أ���һ�������첻�µز��µģ�ȴ�´�һ���绰�����治�����������Ǻ�ų�������ܵĶ�����
������������������ӵ�ʱ������Թ��������������ӵ�ʱ����ƽ���Լ�������������ӵ�ʱ�������¹���������Ȼ�����ٶȲ�����ҵĵ绰��
����������Σ��Է�һ������Ͳ�����ͼ�����˵����Ľ�������������ѡ���
��������������𩤩��ѣ�����Ľ������ţ����������Ũ�صĻ�ҩ��Ϣ�������ۣ��ո��Ǹ��绰��Ҳ����������ˣ���
�����������ǵġ��������ӵ�˵�������IJ����ţ�������ŭ���Լ���������Ϊʲ�������������������ɪ���أ�
������������ѽ������Ľ���߷ߵ�˵����ŷ̫̫��������ʲ���»���Ҫ���ˣ�˵�����ɣ���
��������ʲ�ۣ�������ʲ�ۣ�ŷ̫̫����ŷ̫̫��������Ϊ����ŷ���������ˣ�����Ϊ���Ƕ�����㣬���۲�������Ů����ŷ̫̫����ŷ̫̫�������ĺ�������������������ѪҺ������������������˵���������ˡ�
���������������ˣ�����Ľ���������������˹������������̣������ŷ�������������������į�����𣿻��ߣ�����Լ��ȥɢ���𣿡�
�������������Ѹе������������죬���м�����̹�˳��������������������������е���ʶ����ʹ����ÿһ������Ŭ����ۼ��Լ���ɢ��˼��ͻ��ҵ����ǣ�����ֻ���������ڸΰ��ʹ���ͻ��ư�Ŀ�ŭ����Ľ����Ȼ�ڵ绰��˵�Ż�������������ģ������˿̱��볰������Ϊʲ�۲�˵���أ�ŷ̫̫����û��������̨���𣿻�������ʲ���ƾ磿��������תʲ�ۻ���ͷ���Ҹ����㣬����û����Ȥ�����Բ��ˣ�ȥ�����ŷ�����ɣ���
���������������ܷ����������ˣ��ۼ����Լ����е��������������Լ������������춯�ذ�ض��ŵ绰��Ͳ��У���������������˵�������������ģ������ģ����µ����ġ�����
�����������Ļ�û�к��꣬�Է��֡�����һ�������ߣ�����ס������һ��Ļ���������������Ͳ����������ʯһ�������Ƕ�����̫̫�ּ����ĸ��˹����ˣ��ƿ��ţ������ƶ����ŵĺ��������ѣ����ѣ����������ˣ���
��������һ�ۿ������������ŵ绰��Ͳ���������Ƕ������ϵ����ߣ���ʱ��ס�ˡ������ѵ����ѩ�ף��۾�ֱֱ�ĵ��ţ����ݽ�ҧ���촽��һ���ʺ��Ѫ�������촽������������̫̫�Ŵ��ˣ�����ץס���ļ�ž�����ȫ���ļ��ⶼ�ǽ�Ӳ�ģ���̫̫���Ӿ����ˡ���ס��ҡ����������̫̫���ţ����ţ������ѣ����ѣ����ѣ��������ˣ�������ʲ���£���˵��ѽ��������ң���
����������������Ȼһ��Ҳ���������ţ������˶�ʧ�˻��ˡ���̫̫�ŵ�����ʧ�룬ץ������������ĵ绰��Ͳ����ȡ�������͵��Լ�����ȥ�������Է�ʲ��������û�У���Ȼ�ǹҶ��˵ġ��ѵ绰��Ͳ�Żص绰���ϣ������ڴ��ߣ�˫����ס�����ѵļ磬û����ҡ���������������ѣ����ѣ���Ҫ������ʲ��ί������˵�ɣ�������Ұɣ��������Ż��ң����ѣ����ѣ����ѣ���
������������̫̫����һ����������ҡ�����������ڱ�ҡ���ˡ��ع���������̧���۾������˿���һ�ۿ�����̫̫���Ž��ƶ��������������š���ѽ����һ�������ˡ����˽�����̫̫�Ļ����������˻���γ���ϣ�һ��ޣ�һ��϶������ĽУ�������ѽ������ѽ���ҡ����ҡ��������������ٿ���Ц�ˣ�����ѽ���ҡ����ҡ��������۰죿���۰죿���۰죿����ѽ����
����������̫̫�����ñ��з��ᣬ����סҲ����������������һ�ο����⺢����˱�������������һ���Ƕ����ֹ۶������ģ���ǰ������Ϊ�����������Խ���ǣ�������ȴ����Ҫ�Ǹ��첻�£��ز��µ����������ˣ�
�������������ѣ������������ӣ�����˵����˭��绰�������ˣ�����Ľ���𣿡�
������������������������������������������֣�����Զ��Ҫ���������֣���Զ����Զ����Զ����
����������̫̫���Ŵ��ˡ�
�����������úúã����ᣬ���ᣬ��Ҳ�����ˣ������ĸ������ѵļ磬��ס�ڵİ�ο�ţ������ƣ�����һ��ʱ��ſ�ѧ�أ����dz���ȥ����ò��ã�������ķ��ն�����������ȥ���סס�����������������Ѻ��𣿡�
�����������Ҳ�ȥ��ۣ����������ִ�С�
�����������úã���ȥ��ۣ���ȥ��ۣ���Ҫȥ�Ƕ��أ���
���������������뿪��ĸ�Ļ�������Ȼƽ�������ˡ�����ϥ������ͷ����ϥ�ϣ���������Ӵ���������Զ������һ�������Ҳ��˵�����������������������
�����������裬�����ڣ������˿ڣ��������������ġ�������Ҫ����ˡ���
����������̫̫������һ�¡�
������������˭�������ʡ�
����������ŷ��������
����������̫̫�־�����һ�£��������������Ů����˭��Ů���ᵽ����ʱ�������������е��أ�����������С���������ʣ�������˵����𣿡�
�������������ѿ���ĸ��һ�ۣ�������졣
������������˵�������ٿ���Ц�ˡ��������ĵ�˵��
�������������ǣ�����̫̫������һ�¡����㰮���𣿡�
�������������ѵ���Ť���ˡ���תͷ���Ŵ��⣬��ҹ�磬����û�з�������ҹ�������£���ҹ��һƬģ��������������ʪ���ֱۣ����������ȶ������ġ�
�����������������ˡ�����������˵��ת��ͷ������ĸ�ס�����ȥ����ŷ�ң�Ҫ���Ϳ죬������֮�ڣ��ѻ��°��ˣ��Ҳ�Ը�����ӡ���
����������̫̫�ٶȾ�����
���������������£���ο����ۼ��أ���һ��ͱ�ҵ�ˣ���ҵ֮���ٽ�飬��������
�����������Ҳ������ˡ���
������������˵ʲ�ۣ���
�����������Ҳ��������ˡ��������������ġ��϶���˵��������IJ������ՖX������Ϸ�磬���ՖX�������Ǹ�������ʹ����ҵ�������������أ�����Զ�����Ϊһ�����ң������Ҳ����Ϊ���ּһ�Ϸ���һ������ֻ�������˩r������ͨ���������ɣ��ҳ�����һ����С��֮�⣬��ʲ�۶����ɲģ���
����������̫̫�Ȼ�ĵ�����Ů����
�������������ۺ�Ȼ����





![[������]�����Ļ�����](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