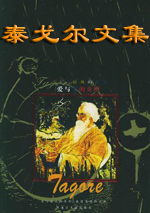琼瑶文集-第7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呵!他的口哨吹得那么好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赶得过他!他的歌声也是。他的手工也是第一流的,他做的风筝比买来的还好,他用泥巴捏的小人都像活的……他什么都会,什么都强,什么都能,他是她的上帝,她的神,她的主人!
九岁,她跟他到溪边玩,这棵老柳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老朋友,看着他们在溪边捉迷藏,看着他们在一点儿一点儿的长大。那是夏天,烈日像火般的烧灼着大地,两个孩子都晒得脸颊红扑扑的,额上的汗珠仍然在不断的沁出来。宝培在老柳树下一坐,呼出一口气来说:“太热了,我要到河里去游泳!”
“你去,我帮你看衣服!”荷仙说,当然,宝培的游泳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宝培脱掉了衣服和鞋子,只剩下一条短裤,走到溪边,他一窜就窜进了溪水中。在水里,他来往穿梭,像一条小小的银鱼。荷仙羡慕而崇拜的看着他,他多能干!他多勇敢!宝培从水中仰起头来,对她叫着说:“这溪水凉极了,好舒服!荷仙,你也下来!”
“可是……可是……”荷仙好犹豫:“可是,我不会游泳哪!”
“你学呀!快下来!”
“很容易学吗?”荷仙有些儿瑟缩。
“怕什么?有我呢!”小男孩挺了挺胸,一个仰游冲了出去,好逍遥,好自在。
真的,怕什么?有他呢!有宝培呢!怕什么?他是神,他是上帝,他是无所不能!怕什么?他在叫她,他在对她招手,他要她下去。她脱掉了裙子,也只穿一条短裤,走到浅水中,她叫着说:“宝培,我来了!”
就“呼”的一声,冲进了水中,那样没头没脑的,对着那溪水一个倒栽葱钻了下去。一股水堵住了她的口鼻,她不能呼吸,她不能看,她不能叫。那溪水的寒冽沁进了她的肺腑,迅速的包裹了她。她张开嘴,水从她口中直冲进去,她不由自主的咽着水,窒息使她的头胀痛昏沉,使她的意识迷离飘浮。但是,她不恐惧,她一点儿也不恐惧,她心里还在想着:“怕什么?有宝培呢!”
然后,她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她躺在老柳树下面的阴影里,头仍然昏昏的,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她张开嘴,吐出好多水来。于是,她发现宝培正在胡乱的扳动着她,呼叫着她,他那张清秀的面庞好白好白。看到她睁开眼睛,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说:“荷仙,你吓坏了我!”
她对他软弱的笑笑,真不该吓坏他的!她好抱歉。
“你没有怎样吧?荷仙?”他脆在她身边,俯身看她。“你好吗?”
她点点头。
“怕吗?”
她摇摇头,勇敢的微笑着。
“怕什么?”她由衷的说:“有你呢!”
十三岁,她从国民小学毕业,他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穿着中学制服的他,好神气,好漂亮。但是她呢,养母说:“女孩子家,念书也没什么用,留在家里帮帮忙吧!也该学着做做家务事了,一年年大起来了,总要结婚生孩子的!”
学校的门不再为她而开,但她并不遗憾。她知道,自己能读到小学毕业,已经是养父母的恩惠了。她开始学着做家务,做针线,她补缀宝培的制服,帮他钉掉了的钮扣,她常把针衔在嘴中,对着他的衣服低低叹息。在老柳树下,他教她唱一支在学校里学会的歌:“井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我曾在树皮上面,刻过宠句无数,欢乐和苦痛的时候,常常走近这树!”他们把头两句歌词窜改了,改成了“溪旁边小镇后面,有一棵老柳树。”他们就在老柳树下唱着,一遍又一遍,乐此而不疲。亚热带的女孩子是早熟的,十三岁的荷仙已经亭亭玉立。两条粗粗的长辫子,宽宽的额,白皙的皮肤,修长的眉,清澈的眸子,揽镜自视,荷仙也知道自己好看。在树下,宝培开始会对着她发愣了,会用一种特殊的眼光,长长久久的注视她。而且,他会提起孩提时养母的戏语来了:“荷仙,妈说过,你长大了要给我做太太的!”
“乱讲!”她说,背过脸去。
“不信?你去问妈去!”
“乱讲!乱讲!乱讲!”她跺着脚,红了脸,绕到树的后面去。
“才不乱讲呢!”他追了过来,笑嘻嘻的。“妈说,等我们长大了,要把我们‘送作堆’,你知道什么叫作‘送作堆’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她一叠连声的喊着,用两只手捂住了耳朵,有七分羞涩,有三分矫情。然后,她一溜烟的跑掉了,两条长长的辫子在脑后一抛一抛的,那扭动着的小腰身已经是一个少女的身段了,成长,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一下子,你就会发现自己长大了。
四
是的,一下子,你就会发现自己长大了。
荷仙十六岁的时候,宝培高中毕业了。
那是个月亮很好的夏夜,老柳树在溪边的草地上投下了婆娑的树影,成群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闪烁穿梭,明明灭灭,掩掩映映,像许许多多盏小小的灯。河水潺oe□,星光璀璨,穿过原野的夜风,从树梢上奏出了无数低柔恬静的音符。夜,好安详。夜,好静谧。
荷仙在老柳树下缓慢的踱着步子,时而静立,时而仰首向天,时而弯下身去拨弄着草丛,又时而轻轻的旋转身子,让那长辫子在空中划上一道弧线。宝培站在河边,望着她。出神的望着她。那款摆着的小腰肢,那轻盈的行动,那爱娇的回眸微笑……这就是那个和他一同长大的小荷仙吗?他不由自主的看呆了,看傻了,看得忘形了。荷仙又弯下腰去了,一会儿,她站直了身子,双手像蚌壳一样阖着,嘴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喜悦的低呼,抬头对他望着,高兴的说:“你来看!”
“什么?”他惊讶的。
“一只萤火虫,我捉住了一只萤火虫!”她说,孩子气的微笑着。
他走了过来。她把阖着的双手举起来,露开一点指缝,让他看进去。那萤火虫在她的手中一明一灭,那白皙的,丰腴的小手。指缝处,被萤火虫的光芒照耀着,是淡淡的粉红色。
他看着,捧起了那双手,他眯着眼睛往里看,然后,他的唇盖了下去,盖在那柔软的,白皙的,握着光明的那双手上。
她惊呼,乍惊乍喜,欲笑还颦。手一松,萤火虫飞掉了,飞向了水面,飞向了原野深处,飞向了黑暗的穹苍。她跺跺脚,噘起了嘴,低低的说:“你瞧!你瞧!飞了,飞掉了。都是你闹的!你瞧!你瞧!”
“让它飞吧!”他说,握紧了她的双手,嘴唇在她的手背上紧压着。“只要你不飞就好!”
她害羞了,用力的抽出自己的手来,她再跺跺脚,装出一份生气的样子来,但是,笑意却不受控制的流露在她的眼底唇边。
“你坏!”她说,转过身子,向树后面跑去。
“别跑!”他追过来:“有话对你说!”
“不听!”她继续跑着,发出一串轻笑。
“抓住了你,我要呵你痒!”他威胁着。
“你抓不住我!”
“试试看!”
于是,她跑,他追。绕着那棵大柳树。这就是爱情的游戏,人类的游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从亚当夏娃开始,这游戏就盛行不衰了。绕了好几圈之后,荷仙的头昏了,而且喘不过气来了。他抓住了她,她跌倒在草地上,仍然笑着,又喘气又笑。他跪在她的身边,把她按在地下,他不住的呵着她的痒,一面笑着说:“看你还跑不跑?看你怕不怕了?”
荷仙扭动着身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乱七八糟的嚷着:“我不跑了,我怕了,饶了我吧!你是好人!饶了我吧!你是好人嘛!”
听她喊得那么甜,宝培不由自主的停了手,但他仍然下意识的按着她。她也没有企图站起来,躺在那儿,她依旧笑意盎然。月光涂抹在她的脸上,发上,身上。两颗星星在她的眼底闪亮。那小小的鼻头,那丰润的,红滟滟的嘴唇,那细腻的,吹弹得破的肌肤……他盯着她看,目不转睛的,迷惑的,惊奇的……然后,他的嘴唇压了下来,一下子就紧盖在她的唇上。
她轻轻的呻吟,又轻轻的叹息。他紧拥住她,吻得她心跳,吻得她脸红,吻得她透不过气来。
“哦!”她终于推开了他,坐起身来,一个辫子松了,披泻了一肩长发,她拂了拂头发,开始重新编结着那个发辫。
“瞧你!瞧你!”她爱娇的说:“你弄乱了我的头发,你坏,你欺侮人!”
“不欺侮人。”他说,郑重的。“你知道,你从小就是我的人。”
“不害臊!”她斜睨了他一眼。
“这有什么可害臊的?”他望着她。“我们都要长大,从孩子变成大人。你,也将成为我的妻子,这是件严肃的事,不需要害羞,也不需要逃避。”
她俯下了头,把脸埋在弓起的膝上。
“你在说些什么呀?”她一半儿欢喜,一半儿矫情。
“我在说,要和你结婚。”
她的头俯得更低了。
“我们结婚好吗?”他问,拉住她的手。“等我满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结婚,好吗?好吗?”
她轻笑不答,把头转向一边。
“好吗?好吗?”
他追问着,把她的脸扳过来,然后,他的唇又盖了上去,她倚进了他的怀里,紧紧的,紧紧的,紧紧的。那个刚结好的发辫又松了。
五
然后,有一长段时间,老柳树底下失去了两个人的影子,而变得只有荷仙一个人了。宝培去了台北,读大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荷仙经常一个人徘徊在老柳树底下,拾掇一些过去的片片段段,计划一些未来的点点滴滴。她做梦,她幻想,她回忆。她笑,她流泪,她叹息……对着老柳树说话的习惯,也就是这个时候养成的。老柳树开始分担着她的喜悦与哀愁了。
她常常就那样站在树底下,用手指在树干上划着,一面絮絮叨叨的数落:“他有一个星期没来信了,你想他会忘了我吗?台北地方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还会记得我吗?他一定不会像我想他那样想我的,要不然他会多写几封信给我!呵呵!他是个没心肝的东西,没心肝的东西……”话没说完,她猛的捂住了自己的嘴,睁大了一对惊惶的眼睛:“天啦!原谅我!我怎能骂他呢?我怎能?”用手抱住树干,她把面颊贴在那老柳树粗糙的树皮上。“呵,老柳树,老柳树,你知道我不是真心想骂他的,我那么爱他,怎能骂他呢?怎忍心骂他呢?不过,天哪,让他早点给我写信吧!只要一个字就好了!一个字!”
下一天,她会跑到老柳树下,疯狂的抱住树干转圈子,她手中高擎着信纸信封,像个得胜的,凯旋归来的武士!她把信纸张开,给老柳树看,嘴里胡乱的说着:“你瞧!你瞧哪!他来信了!他没有忘记我,他没有忘记我呢!他写了那么多,不止一个字呢!我数过了,六百三十一个字!你信吗?不过……”她悄悄的垂下了头,羞红了脸,低低的说:“我希望我能看懂他写了些什么,我希望我不要这样笨就好了!”她叹息,把信纸压在唇上,好低好低的说:“我爱他!呵!我爱他!”
许多个月夜,她呆呆的坐在柳树下,用手抱着膝,把面颊倚在膝上,静静的看着河里的月亮说:“月亮呵,你照着我也照着他,你告诉他我有多爱他,求你告诉他吧!因为我不会写信哪!因为我说不出来哪!求你告诉他吧!”
也有许多个黄昏,她坐在那儿,静悄悄的垂着泪,低低的,埋怨的轻语:“他怎么还不回来呢?这样一天天等下去,我一定会死掉!呵呵,不!我不能死掉,我要为他活着,为他好好的活着!”
对着溪流,她在水中照着自己的影子,顾前盼后,仔细的打量自己,然后对水中的影子说:“你不许瘦呵!你不许变难看呵!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你一定要漂亮呵!”
老柳树听够了她那爱情呓语,看多了她那思慕的泪痕。于是,在一天晚上,这树下的影子又变成了两个。那高高大大的男孩子在树底下捉住了她的手,叫着说:“让我看看你!荷仙,让我好好的看看你!一回家,人那么多,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看你!”
“看吧!宝培,随你怎么看!看吧!看吧!看吧!”她仰着头,旋转着身子。他看着她,惊奇的,迷惑的。那短袄,那长裤,那成熟的胴体;那刘海,那发辫,那毫无装饰的面庞;那眉线,那嘴唇,那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他张开了手臂,大声的说:“来吧!你是我的葛莱齐拉!”
“葛莱齐拉?那是什么东西?”她扬着眉,天真地。
“那是拉马丁笔下的人物。”
“拉马丁?”她笑嘻嘻的。“是马车夫吗?”
他噗嗤一声笑了。她红了脸。
“我说错话了,是吗?”她问,一阵乌云轻轻的罩在她的脸上,她低低的叹息。
“不,”他说,凝视着她。“你没有说错什么。拉马丁和他的葛莱齐拉距离你太遥远了,那是虚幻的,你是实在的,你不必管什么葛莱齐拉,真的!”
她的大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他,她的面容好忧愁。
“呵!”她轻语。“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的话了?”
他瞅着她,失笑了。
“是我不好,不该和你说这些。”他抬起了眉毛。“现在,让我说一句你懂的话吧:我爱你!”
她发出了一声低喊,扑进了他的怀中。他拥着她,那温暖的小身子紧贴着他,那满是光彩的面庞仰向了他,她喜悦的,不住口的说:“你是真心的吗?宝培?我等你等得好苦!好苦!好苦!噢,宝培!你不会嫌我?我是很笨、很苯、很笨的呢!你不会嫌我?”
“嫌你?为什么呢?”他喃喃的说,吻着她。“我永不会嫌你!荷仙!”
她仰首向天,谢谢天!谢谢月亮!谢谢大柳树!谢谢溪水!呵,谢谢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六
呵!谢谢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真该谢谢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吗?
接着,开学之后,宝培又去了台北,这个假期是那样的短暂,那样的易逝,留给荷仙的,又是等待和等待。朝朝暮暮,暮暮朝朝,魂牵梦萦,梦萦魂牵。她很少写信给宝培,因为提起笔来,她自惭形秽。本来嘛,“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她只是把自己那无尽的思念,都抖落在大柳树下。就这样,她送走了多少个黄昏,多少个清晨,多少个无眠的长夜!
然后,这天早上,当她在菜场上买菜的时候,隔壁家的阿银对她说:“你家的宝培回来了呢!我刚刚看到他!”
一阵呼吸停顿,一阵思想冻结。然后,顾不得菜只买了一半,拎起菜篮子,向家中就跑。呵,宝培!呵!宝培!呵,宝培!快到家门口,她又猛的收住了步子,看看自己,衣衫上挂着菜叶子,带着汗渍,带着菜场上的鱼腥味,摸摸头发,两鬓微乱,发脚蓬松。呵,不行!自己不能这样子出现在他面前,她得先换件衣服,洗净手脸,他喜欢女孩子清清爽爽的。
不敢走前门,怕被宝培撞见。她从后门溜回家,把菜篮放到厨房里,就迅速的回到卧房。换了件白底子小红花的衫裤,对着镜子,打开头发,重新结着发辫。呵,心那样猛烈的跳着,手竟





![[综琼瑶]生若夏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