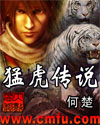鲁迅传-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6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他现在全都蚣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复旧话。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对社会的攻击的文字中,他叹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指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请仔细体味这段话罢,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无用的悲愤之情,如此强烈,如此不掩饰,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现过的吧。他初到广州时固然说过,文学是最无用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但他这样说的主要情绪,还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激愤,那种文明人遇见野蛮人的悲哀,虽将文人贬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恒先生》中的话,优越感几乎全部消失,从字里行间一股股冒出来的,分明是另一层自觉多余的沮丧,一种深感无聊的冷气。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还是那个局外人的处境给他的馈赠。我在前面说过,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五四”时代,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那一群启蒙者,正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们自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大责任,这构成了他们的自信的基本理由。这也自然,既然是知识阶级充当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显得格外重要。鲁迅既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就同样有这份精神上的优越感,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经历,似乎又都证实着他的价值。新文学的创造自不用说,就是与章士钊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也从另一面证实了,他并非无足轻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他受到青年人那样热烈的欢迎,这就更容易使他确信,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那样谈及他的“地位”,他“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7就说明了他的自负。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对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从《新生》流产和“三·一八”惨案之类的事情中,他已经敏感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无价值,他在理智上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那样用力压制虚无感的“鬼气”,主要也就是要压制对自己无价值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总要全力稳住它。
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的种种体验,尤其是“四·五”事变后的时局的发展,却逼得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上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来是想发挥作用的,所以才那样召开紧急会议,力主管救被捕的学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个紧急会议等于白开;他迁出中山大学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广州更似乎将他遗忘,几乎没有人去招呼他。局势一天天变化,与他却毫无关系。那些人自己杀来杀去,你争我夺,犹如上大群鳄鱼在河中厮杀争抢,搅得浊浪滔天,血腥气弥漫两岸。整个社会则像一条破船,就看它们厮杀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躲得远一点,不被它们顺手掳卞河去,吞进腹中,就算是万幸了,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愿意听他的指引吗?可是,他对青年却不再相信,正派老实的青年自然有,他们的命运是作“醉虾”;别样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们多半会龇出利牙,跃入河中一也变成小鳄鱼!《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觉多余的沮丧和冷气:就正是从类似上面这样的思绪中,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来的吧。
鲁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9一个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会这样对人详述著作的销售情况的,越是深信读者对自己的崇拜,他有时候反而要挑剔这种崇拜。你看在北京时,鲁迅不赞成小学课本选收《狂人日记》,说是怕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对慕名来访的青年人说,倘若有谁“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10就正以一种特别的自我挑剔的方式,显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广州这样向人报告读者如何喜欢他的书,“我实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会对自己的态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会的冷淡,一旦敏感到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社会对自己依然热情。遭受一点“落伍”的批评,都会如此动摇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局外人,就更会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间闷热的西屋内,他一面编《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写道:“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11四个月之后他又说:“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上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12这时候,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正开得鲜艳;就是编《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文集,从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对个人也应该是极富情趣的乐事。可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从笔底流泻出来的,竟是那样痛觉到生命的无用和无聊,饱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许广平当初读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也许她能够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鲁迅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无所谓呢?
他势必要在心底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后该怎么办?……”在他滞留广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迁进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绪大概都很难离开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自对人说过,他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连去几所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单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这琢磨的思路和轮廓,大致是怎样的了。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13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14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15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6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7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18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19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