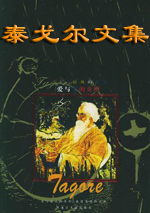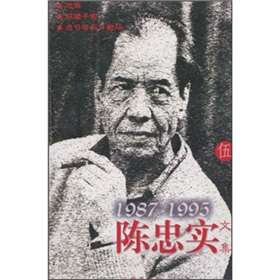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10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央走道的两侧。公园的中心点,则是耸入天际的名作——“生命之柱”。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大群旅客,围在一个不过三尺高的小铜像前。
那是一个跺脚捶胸、嚎陶大哭的娃娃,公园里最著名的“怒婴像”。
高举着双手,提起一只脚,仿佛正要狠狠踢下去。虽然只是个铜像,却生动得好象能听
到他的声音、感觉他的颤抖。
他是在发怒啊!为什么还这么可爱呢?
大概因为他是个小娃娃吧!被激动了本能;点燃了人类最原始的怒火。
谁能说自己绝不会发怒?只是谁在发怒的时候,能像这个娃娃,既宣泄了自己的情绪,
又不造成伤害?
有原则的发怒
最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两部电影都好极了,
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却都是发怒的情节。
在《霸王别姬》里,两个不成名的徒弟去看师父,师父很客气地招呼。但是当二人请师
父教诲的时候,那原来笑容满面的老先生,居然立刻发怒,拿出“家法”,好好修理了两个
听话的徒弟。
“在《活着》这部电影中,当葛优饰演的败家子,把家产输光,债主找上门,要葛优的
老父签字,把房子让出来抵债时。
老先生很冷静地看着借据说“本来嘛!欠债还钱。”然后冷静地签了字,把偌大的产业
让给了债主。事情办完,一转身,脸色突然变了,浑身颤抖地:追打自己的不肖子。
两部电影里表现的老人,都发了怒。但都是在该发怒的时候动怒,也没有对外人发怒。
那种克制与冷静;让人感觉到“剧力万钧”。
只是,这世上有几人,能把发怒的原则、对象和时间,分得如此清楚呢?
有理性的发怒
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在联合国会议里,苏俄的赫鲁晓夫,会用皮鞋敲桌子。
后来,我跟精干外交的一位朋友谈到。他一笑,说:“有没有脱鞋,我是不知道。只知
道作外交虽然可以发怒,但一定是先想好,决定发怒,再发怒。也可以发表愤怒的文告,但
是哪一篇文告不是在冷静的情况下写成的呢?所以办外交,正如古人所说,君子有所为,有
所不为;君子有所怒,有所不怒。”
这倒使我想起,一篇有关本世纪最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报道。
托斯卡尼尼脾气非常大,经常为一点点小毛病,而暴跳咆哮,甚至把乐谱丢进垃圾桶。
但是,报道中说,有一次他指挥乐团演奏一位意大利作曲家的新作,乐队表现不好。托
斯卡尼尼气得暴跳如雷,脸孔胀成猪肝色,举起乐谱要扔出去。
只是,手举起,又放下了。他知道那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份“总谱”,如果毁损,麻烦就
大了。托斯卡尼尼居然把乐谱好好地放回谱架,再继续咆哮。
请问,托斯卡尼尼真在发怒吗?还是以“理性的怒”作了“表示”?
学习发怒与不发怒
想起一位刚自军中退伍的学生,对我说的笑话。
一位团长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营长发脾气;营长回去,又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
连长冒火;连长回到连上,再满脸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排长训话……
说到这儿,学生一笑:“我不知道他们的怒火,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也是假的;当怒则怒,当服则服。”我说。
每次想到他说的画面,也让我想起电视上对日本企业的报道:
职员们进入公司之后,不论才气多高,都由基层做起,也先学习服从上面的领导。当公
司出了大庇漏,一层层训下来,正像是军中一样。
报导中,也有企业界人士冬天去“打禅七”,和“在街头呼喊”的画面。在冰寒的天
气,一群人端正的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狠狠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异的眼光,大声呼喊各种“老
师”规定的句子。
他们在学习忍耐,忍耐清苦与干扰,把个性磨平,将脸皮磨厚,然后——
他们在可发怒的时候,以严厉的声音训部属,也以不断鞠躬的方式听训话。怪不得美国
人常说:
“在谈判桌上,你无法激怒他们,所以很难占日本人的便宜。”
既会发怒,又难以被激怒。适时发怒,又适可而止。这发怒的学问有多大!最重要的
是,在学习用发怒表示立场之前,先应该学会,在人人都认为我们会发怒的时候,能稳住自
己,不发怒。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
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康,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挤不进去呢?
你可以……
联考大餐馆
大学联考距离我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当时发生的两件
事:
考场上有两名枪手被抓了,一个是某著名大学的学生,另一名早已毕业。他们都有超人
的功力,连着几年为别人代考,每次都考取名校。
枪手考大学,外国拿博士
被抓之后,他们的学籍被开除了,曾由他们代考的学生,也失去学籍,问题是,其中有
两位不但已经在台湾念完大学,而且出洋留学,在外国拿到了研究所的学位。
看到这个新闻,我想,那请“枪手”代考的人,功课一定不怎么样,既然功课不好,进
入名校一定跟不上,就算台湾的名校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出洋也必然要出丑。可
是,为什么他们不但拿到硕士,甚至有的马上可以拿博士了呢?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是进入师大美术系的那天,系主任致欢迎辞时说。
“你们真幸运,今年有近两千人来考,我们只取二十五位,想必你们在进来之前,已经
找很好的老师,磨练了许多年,所以,你们已经都很棒了!”
第一堂素描课下来,我环顾同学的作品,果然,大家都画得好极了。诚如素描教授当天
的评语——“看得出你们都受过学院派老师的指导。”笑了一下,他歪歪头:“说实在的,
没受过学院派的训练,也考不进我们美术系。…
我问了几位同学,也想想自己:
“可不是吗?我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名师!”
只是,从那以后,我常想:“如果一个有才气,也立志做艺术家的人,因为找不到学院
派的老师,或请不起名师指导,是不是就永远跟我们美术系绝缘了呢?如果这样,未免太不
公平了!”
哈佛大学:不看过去,看未来!
我总记得,美国的安克志的儿子对我说,他高中的成绩不是多么好,但是哈佛大学在口
试之后收了他,原因是:
“哈佛大学不只问你过去学到多少,更重视你的潜力,看你未来能学多少。”
问题是,我们的联考制度,怎么发掘那些有潜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在僵化的考试方法
下,会不会有太多张大千、黄君壁和林玉山,在第一关就被打了回票?
只是,想到这儿,我又自问,前面那几位,又有哪个曾是考场的战胜者?靠着一纸金榜
而伟大呢?
中国是那么重视科举,由科举出来的人才多得不可胜数,只是,如果我们好好算算,只
怕不是科举出身的人,远比前者对中国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早在从事革命之前,就曾经上书李鸿章,还亲自送去天津。幸亏李鸿章没理
睬,相反的,如果李重用了孙,只怕孙中山就当不了国父。也只怕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跟英
国或日本一样,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室。
也使我想起在师大时,听说系里想聘江兆申先生执教,后来因为江先生学历不合而未达
成,使系里同学失望了好一阵子。后来则知道江先生去了文化大学执教,又做到故宫博物院
的副院长,而今则成为一代宗师。
当年师大僵化的用人方法,不但没伤到江先生丝毫,只怕还促使他更上层楼,更伟大了
起来。
一时成败不重要
这又让我想到已故的名音乐家邓昌国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可以试着去角逐几个大
奖。得个奖,对你一定有帮助。”隔一阵,看我毫无角逐的意思,他又说:“有些人才,不
屑于跟人竞争。只是,不屑于竞争,是好的!不敢去竞争,就糟了!前者自己朝认定的方
向,不断努力,总会出头。后者,一逃再逃,虽然有才气,到头来,也要落在人后。”
又隔了两年,再遇到,他拍拍我:
“何必去争那几个大奖呢?去争着做那几个大奖的评审委员吧!”
邓昌国先生逝世好多年了,他的话还如在耳边。我觉得他是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指出
一条路,激励我走上去。又找出第二条路,给我再一次的鼓励。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
人不论去不去跟人竞争,也不论竞争的一时成败,总要认定自己的方向,默默地奋斗。
非常侥幸,我在联考时过关了。许多当年失败的同学,隔了一年再考,还有服完兵役之
后又考上的。那些落榜的,则早早进入了社会。
我开画展时,好几位当年落榜的同学,收藏了我的作品。他们起步早,在社会上也成功
得早,好几位成了大老板,下面有一堆博士、硕士为他们工作。
你不可能被考试打败
我发现,自己当年想错了!
一个人不可能被考试打倒,只可能被考试打得自暴自弃,如果他因为没考取,而在未来
的人生失败了,绝不是被考试淘汰,而是被他自己“沮丧的心”所淘汰。
我们可以不跟别人争,但不能不跟自己争。只有“超越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地成功。
三十年后,回顾大学联考,我发现一个巧妙的比喻: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
康、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挤不进去呢?
你可以改天再去,也可以不再光顾,毕竟这世界太大了,处处有餐馆、处处有美食。
只有那死心眼的人,才会说:
“我挤不进联考大餐馆,我要一辈子挨饿了!”
你可以不准我写、不准我说、甚至不准我哭、不准我笑,
只是你没办法不准我想。
于是,我在心里想我的音乐,还是活得很美。
多好啊!活得很美!
“我最近好为难。”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学生对我说“我有两个女朋友,都很爱我,我也
很喜欢她们,不知该选哪一个。”
“表示两个条件差不多。”我说。
“不!条件差满多的。”学生瞪着我说,“一个很有钱,家里放了史坦威的大演奏。另
一个很穷,我常给她打电话,打一半,就没法说了。因为她的卧室正靠着铁道,火车过,整
个房子都震动,什么也听不见,只好拿着电话发呆。”
隔了半年,遇到那学生,他已经结婚了。
“娶了有史坦威钢琴的?”我笑道。
“娶了铁道旁边贫民区的。”
“噢!”我点了点头:“不简单哪!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一天,我到她家去,坐在她卧室聊天,突然火车过,好响!带起一阵风,把窗帘都
吹起来了,那是一块很便宜的薄棉布的窗帘,她自己用手缝的。这时候,阳光射进来,我看
见窗台上放了一个宝特瓶切一半作成的花盆,里面开着一丛不知名的小黄花。我问她那是什
么花。她很不好意思,挡在前面说,是不值钱的花。我又问,很漂亮啊!是什么花嘛?她吞
吞吐吐半天,才说,是野地里挖出来的小草花,不值钱!”学生脸上露出一种好特殊的光
彩:“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突然产生一种感动,冲上去抱住她,叫她不要那么说,不要说不
值钱,美的感觉是不能用钱衡量的!就在那一刻,我发觉,我深深爱上了她。”
触动心灵的美,不见得华丽
学生的话,常浮过我的脑海,我常想象那个浴着午后阳光,被风拂起的窗帘,和窗台上
逆光看去的那丛野草花。多么平凡,多么美!
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去花店订花,花店老板随后拿了一支玫瑰送我。
回家,我把那支玫瑰插在细细的小瓶子里。隔两天,情人节的花也送到了,是二十四朵
玫瑰。我又找了一个大大的水晶花瓶,放进去。
奇怪的是,那二十四朵端丽馥郁的玫瑰,和旁边孤零的一小枝比起来,我却对那一技,
有种特别的感动。觉得好精巧,好细致,好有慧心。
也想到有一次到前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先生家去。布置很清简,案上没花,只有一盆
番薯冒出的青苗。淡红色的番薯皮,翠绿弯转的藤叶,却给人一种特特别的雅致。让我回到
童年,记忆中父亲用小水皿养的蒜苗,在冬天的窗前,盎出一片新绿。
真正会心的美,常像是简简单单的禅宗不墨画,不必华丽的色彩,也无需复杂的构图,
却能在那“空灵”处引人遐想,给人美。
美,帮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
自从女儿上幼稚园,也常常给我这种美。
她有个放劳作的篮子,乍看好象垃圾桶。里面有用超级市场牛皮纸袋作的帽子。用衣服
夹子和纽扣组成的小人。用纸盘作的面具,和用黄豆组成的图画。
学校动不动就发通知,要家长给孩子准备空的鲜奶盒子,或卫生纸用完剩下的“纸
轴”。跟着就让孩子从学校带回,用那些废物组成的玩具。
问题是,在大人眼中的废物,却成为孩子的宝贝。他们不在乎世俗的价值,只在乎自己
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想象。
于是,常看见小丫头举着她的劳作炫耀。先觉得她傻。想想,才发觉是自己俗。她让我
又想起那个学生的女朋友,窗台上放的宝特瓶花盆,和里面的小草花。更让我想起以前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的一段话:
“你们将来教美术,目的不应该是造就几个专业的艺术家。而是培养一批有美感的国
民。让他们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上见到美,也懂得利用身边平凡的东西,创造美。使他们对生
活有一种积极快乐的态度;而不只是现实的价值。更使他们能以美的感觉;面对人生的苦难。”
人,就是一种美
记得初到纽约的时候,去苏活区看一位艺术界的老朋友。进入他的工作室,我差点窒
息。
只见一片烟尘飞扬,四处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他正埋头修理古董。
他把顾客送来的瓷器碎片,慢慢拼起来。先用胶水粘合,再用瓷粉填补、打光。然后把
断缺的花纹,照原来的样子画好。再用喷飞机的罐装油漆,将表面喷成釉彩的光亮。
朋友摘下口罩,陪我走出工作室。小心跨过残雪的泥泞,步上曼哈顿昏暗的街头。
“多美啊!”他一面呵着手,吐着白烟,一面抬着头,看那四周围过来的高楼,近乎咏
叹他说:“纽约!一个真正看到人的城市。”指指高楼,又指指蹲在街角的浪人:“都是人
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人,多美!”
我看着他的脸,看那脸上的感动。也从心底产生一种感动——他,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在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他依然快乐,依然生活得很美。心里有美,眼里就有美。也让我想起
东京现代美术馆收藏,川端龙子画的《金阁炎上》,和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三条殿之
火》。熊熊的火苗向上腾升,带起浓浓的黑烟,日本的国宝建筑“金阁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