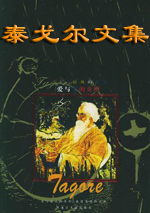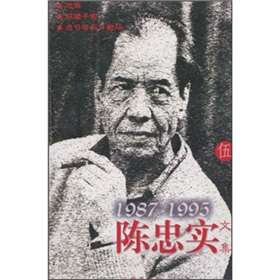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风筝,只要一只手,迎着风,轻轻地松线,自己就能展翅而去。
但我还是捡回了那只不会飞的风筝,重新绑,重新糊纸,又重新在苍茫的暮色里,冲出
门去,加入那群犹未散去的小朋友中,请一个孩子抓住风筝的下端,在高喊松手时,抓着线
圈猛跑。
只是依然掉了下来。
渐渐地,我做的风筝有了进步,虽然还飞不高,且猛打转,但总是飞了起来。
我把风筝拆开,将小竹条削得更平均,又拿另一支竹子撑着,量度出重心,画上记号,
再把垂的那根绑上去,且斜着加上两支小竹片。由于左右力量非常平均,相信绝不会再打转
了。
只是放上天,它虽不转,却仍左右摇摆个不停,我又丢了脸,直到有一天,为它装上了
好几条长长的尾巴,那风筝才真正平稳地飞起来。
“原以为不装尾巴可以飞得轻快些,岂知道反而不稳了!难道那看来像是累赘的东西,
反倒有这许多用处?
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放风筝成为孩子间最热门的课外活动,尤其是初秋的日子,整
个台湾大学操场的天空,都飘着远远近近的风筝,电线上、树梢上,甚至房顶上,常看见坠
落的风筝,但尽管有些还非常完好,除了物主,却不见有人去捡现成,大概是因为,每个人
都希望做自己的风筝。
放风筝的美,岂只是风筝在飞,而且是自己在飞,从自己的手上,扎出来一片方方圆圆
的小东西,为它装上尾巴,绑上线绳,再加上五颜六色,这——就是我的代表、我的孩子、
我的化身,且看今日,谁的能飞最高!且看谁是绞了线、断了丝、栽了跟斗,垂头回家的
人!
飞扬!这是我的想像,飞得愈高、离我愈远,愈是不容易看见,这手上的线愈是脆弱而
不可依靠,愈是我的骄做!
在俄亥俄州,一片广阔的原野上,看风筝大赛,有立休几何形,看来像个大方盒子的风
筝;有灌了气,看来像块面包的塑胶风筝,有日本人画着罗汉脸的长方形大风筝,也有成百
节中国式的大蜈蚣。
至于线,从细得看不清的钓丝,到比笔芯还粗的尼龙绳,更在特别表演中,展示了可以
暗杀别人风筝的玻璃丝线。
参加斗风筝的人,不见得都有特大号的本钱,却怀着一大卷,先浸胶水,再蘸过玻璃碎
粉的“杀筝线”。那风筝似乎也经过特别设计,可以突然做快速的飘摆,倏地横穿到别人风
筝的下方、再猛然上升,只见放风筝的手向回抖那么一下,另一个风筝,就无声无息地翻滚
而去。
人群发出一阵阵的惊叹,带着幸灾乐祸的呼喊,也有着些许同情的惋唱,还有那随着断
线风筝抖动、挣扎、飘滚、滑落、消逝,一种说不出的凄美,所发出的……
那是一首一首的挽歌。美丽的凋零、英雄的殒落,所必当伴随而来的咏唱:
云的归于云
雾的归于雾
飞飓的归于飞飓
天空的归于天空
两支竹、一张纸、一根线、平凡地被塑造——一种偶然。
一阵风,一只手,双目相送中,昂昂然地被举起——一种机缘。
既是风赐予的飞翔,就飞成风的样子吧!那么地飘摆,那么地睡倒,成为一悠然滑落、
一优美的死亡!
既然回到地面,便立刻回复了平凡,且可能被永久地深藏、无情地折损。
就尽情地飞远,激烈地战斗,且在地面那只手的错误发生时,选择属于你的自由吧!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一个怎样的树梢、怎么的枝头,或是一片平野之
上,你竟然带着一些亲人的梦想,一段流浪的经验……
睡成一永恒的姿态!
荒山逆旅待新年
在海外过的第一个中国年,是壮阔的、荒凉的,却又有着一些诗意,带着几分惊险。
趁着寒假,万里来美寻夫的妻,害怕纽约的冰雪,而跟我约定在旧金山碰面,却没想到
一路玩到大峡谷,仍然赶上了她生命中最大、最冷的一场雪。
雪中的大峡谷更壮观了,但是比起玉山、阿里山,甚或只是大屯山,总觉得少了那么一
分优美与悠闲。由于天寒地冻,载人下到溪谷的小骡子早已敛足,只有几个导游,引着不识
时节的零星旅客,叩访印第安人的古迹。
临时才计划到大峡谷的我们,原本就没有准备厚的衣服,再加上谷中挟雪的寒风,除了
一眼看到大峡谷时,还有几分兴奋,跟着游兴就冻到了冰点。
“我们还是回洛杉矾,去狄斯尼乐园吧!”妻建议,于是早早就搭上由大峡谷到Flag
Staff的巴士,准备赶乘晚上9点钟的火车。
巴士抵达F1ag Staff,已是7点过后,饥肠辘辘的我们,在这亚利桑那荒凉的小城
里,提着行李,顶着寒凤前行,原以为大峡谷旁该有着富丽的酒店和热闹的市集,怎料竟是
这种家家店深锁,只有远处几声狼嗥犬吠的景象。
好不容易挨到火车站,卧车的座位虽然订到了,却说由芝加哥开出的火车,因为大雪,
而将延迟7小时到站。别的旅客似乎全是当地的居民,也像是早就料到车子会延迟,纷纷搭
上门口亲人的汽车驰去,顿时偌大的车站里,连管理员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对来自远
东的旅人。
“这里挺荒凉的,不太保险,还是先出去找点东西吃吧!”我把颓然坐在椅子上的妻拉
起来,
出了车站,风雪是更急了,呼啸着仿佛不断牵引着的白色的帘子挡在眼前,却隐隐约约
地发现对街右侧一百码外,有一家餐馆,仍然亮着灯火。
走迸餐馆,令人惊讶的,老板居然是中国人,在这种荒凉的小城?也有中国人?
“中国人嘛!吃苦耐劳,别人不开,我还是开。”老板很热络地过来招呼。且主动地介
绍了葱爆牛肉、蕃茄炒蛋几个简单的菜,他的脸布满风霜,国语也很差,但是笑容很暖。
“您从哪儿来?”我问。
“中国!”
那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在地球的另一边,我原想问是从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的哪省?
却发觉只是一个“中国”,便闪闪亮亮地在心里灿然起来。仿佛最初飞离大气层的太空人的
感觉:“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球,生活在上面的人们却为什么要有这许多纷争?”
于是我们这都来自那小小的“中国”的人,便坐下来谈笑了。
都快吃完了,老板突然一拍腿:“忘了一件事!”跟着进去端出酒来,倒满三杯:“过
年好!”
“过年?”妻屈指算了算:“今儿是除夕那!”
“我太太是墨西哥人,早不过中国年了!今天你们来,又正巧上礼拜收到国内寄来的一
份月历,才想起。”老板一饮而尽:“是你们来美国的第几个新年?”
“第一个!”辛辣的酒,呛得我直掉眼泪,哑了嗓子。
吃罢除夕大餐,再顶着北风走口车站,依然是那么悄元一人;算算时间,还有六个钟头
火车才会到,隔着车站的后窗,远远看见一家汽车旅馆的霓虹灯。
“与其待在这儿受冻或被抢,还是破点财吧!”于是我们又拎着行李从车站大门出来,
再转过街角的平交道,住进那个简陋的旅馆。
已经16个钟头不曾磕眼,虽然在一片霉涅味中,居然倒头就睡着了,但是才过不久,
12点多,突然被一阵吼声惊醒。
“有人在外面打架。”我对妻说:“不要动!”
可是吵声一直不停,而且似乎只是一个人在吼叫,夹着叮叮当当金属相击的声音。我轻
轻溜下床,从窗帘间向外窥视,微光中,只见一个高大的黑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
刀,正一面吼叫,一面攻击着檐下垂挂的冰柱,每一攻击都发出常常的声音,随着冰花开
绽,纷纷坠落。
我想通报柜台,却发现屋里居然没有电话,问题是再过三个钟头,我们就得离开,如果
那黑人一直不走,怎么办?”
“或是喝醉酒了,一下子就会离开。”我安慰妻。只是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人在模模糊
糊中,一会儿醒来过去看看,一会儿侧耳听听,槽的是,那黑人后来居然坐在我们的门前,
只怕连门都推不开了,时间已经是两点钟。
“把闹钟关掉免得警动了他!”我不敢再睡,穿好了衣服想那脱身之计。
“如果他实在不走,而我推开门时,他发了凶,你就先往柜台跑。”我开始做最坏的打
算。
不知是不是妻的祷告蒙了上帝垂听,三点多,就在我们动身之前,门外的黑人居然起身
走了。
我们悄悄地溜出门,冲出旅馆。雪已停,风好冷,却感觉空气无比清新。
火车上黑人管理员有着沉厚的嗓音,热情地把上车垫脚的木梯放下来,扶着我们上去,
又拉下床铺,告诉我们使用裕室的方法,才满脸笑容地退出去。
夜里的白雪在窗外闪着蓝光,车子很平稳,我却迟迟不能人睡。明天,明天又是一个新
的旅站,是狄斯尼,而后将是夏咸夷,再就是又一次的离别;妻回台,而我留在美国继续奋
斗。
“你没睡吗?”妻突然从下铺问我。
“是!想到国内的老娘和孩子,不知在做什么。”
“拜年!只是少了一半的家人,会冷清多了……。
着意过今春
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匝春。花影
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着意过今春。——宋·李清
照·小重山
出国九年,从不曾在这个季节归国,算算已是九年十度负东君,更数倍于易安了!考虑
再三,我终于下了决定。
归来也:着意过今春!过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春天。
离开纽约时,正是雨雪霏霏的深夜,到达台北时,恰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故乡以一脸和
煦的春天欢迎我。
两道的山峦,已经是碧绿的,且摇曳着千万点芦花。芦花在朝阳里闪烁,泛出一缕缕蕴
藉的银白,我家后山的溪谷之间,就有着一大片比人还高的芦荡,却怎么看,也觉得不如故
乡的美,或许因为美国的芦花不泛白而呈褐色,已经就少了几分轻柔,加上它不似故乡的芦
花,能迎风飘散,化为点点飞絮,就更缺乏了许多飘逸。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北投洗温泉,路上总会驻足,欣赏远处大屯、七星山的景色,而我
那时不懂得看山,惟一的印象,就是满山满谷,摇摆着的,柔柔软软的芒草。
车子也经过了田野,早春的作物犹未开始,闲逸的鸳鸯正成群地翩然飞舞。那是田野中
的高士,不掠夺,却带来许多飘逸。他们也是田园山水的点景,在相思林间,在吁陌吠亩
间,留下那瘦长的衫影。
常爱读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常爱看高剑父画的柳荫白鹭,那深色的长啄,弯转的颈子,轻柔的冠羽,和细细的双
足。画起来,既有着长啄和双足的强硬笔触,又有颈背的弧转,加上装饰羽的飘柔,无怪
乎,她们能成为画家最爱描绘的对象。
我看见一只白鹭,正翩然地滑过田野,眼睛盯着那个白点看,山川就都融成一幅深色的
水墨画了!
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朋友说,白鹭是我认为最美的一种鸟。也不止一次地,换来笑声和诧
异的眼光。人们岂知道,对我这个在纽约居住的游子来说,“漠漠水田飞白鹭”,正是一再
重复映现的,童年的梦。
车近台北,映服是十里红尘。早起的人们,在街道上疾驶而过的摩托车和汽车喷出的浓
烟间,正企图吸取最后一口较新鲜的空气。
我只能说那是较新鲜的空气,因为即使在这晨光羲微中,台北的空气,已经受到相当的
污染。所幸人们是最有适应力的,好比在水果摊挑水果,即使整篮中,已经被别人挑剩到后
两个,继续挑的人,还是会自我安慰地说:“我现在所挑的是两个当中,最好的一个!”
于是尽管环保专家们,曾经一再表示,台北的污染已多次超过警戒线,甚至到达危险的
地步……。
人们还是说:“所幸早上的空气还算新鲜,我家附近的空气也算不坏!”
当车子在我住的英伦大楼停妥时,几个老邻居,正从国父纪念馆晨操归来,热络地打着
招呼:“趁早上的空气新鲜,运动运动!”
而当我下楼拿最后一件行李时,他们正登车驰去,留下一团浓浓的,含铅汽油特有的黑
烟。
这就是我的台北,一个晨起的台北。但实在说,台北是不睡的,譬如现在,有些人仍未
眠,有些人才苏醒,有些人永远不曾真正觉醒过。
但她永远是我的台北,那使我生于斯、长于斯,在和平东路师大旁边小河钓鱼,在水源
地抓暇,在家中院子里种番茄、香瓜和小草花,在邻居树上捕蝉,摘波罗蜜的台北。对于
她,如同孩子对母亲,不论她多么苍老或有着多么不佳的生活习惯,我仍然爱她!
“只怕你记忆中的一切都变色了!今天的台北,早已不同于以前!”朋友对我说。
“不!”我抬起头来,从车窗间,看松江路北边对着的一片迷雾:“在那片烟尘的后
面,正有着一群不变的——青山。”
何止如此,在台北的四周,都是不变的青山,我童年时,她们是那样地站着;今我白发
归来,它们依然如此地守候。
山,是执着的,如同我对她的爱慕与怀想。
所以,站在这污染的台北,毕竟知道四周仍然有着清明的爱恋,即或我因污染而昏迷,
仍有许多安慰,因为自己正被拥在一片青山之间。
向北看,七星山、大屯山静静地坐着。我曾经就在这个季节,到七星山上寻找丹枫,路
旁的野草莓依然可见,月桃花的种子,变成了娇艳的丹红色。我曾经从阳明后山瀑布上的自
来水收集站,进入通往七星山的小径,穿过浓雾和偶尔飘零的冷雨,坐在顶北投上面的瀑布
边涤足。
向西北看,观音山正静静地卧着,从百年前看渔帆的归航,到而今看货柜轮的油烟,在
海平面出现。
童年时,小学老师曾领着全三年级的学生,去远征硬汉岭。回程时,或是带错了路,几
百个孩子从陡陡的黄土坡上,近于滚般地下来,居然一个也没受伤——中国孩子就是这么可
爱,他们有的是韧性;中国的家长也是这么可爱,他们信任老师。
向南看,有一条溪流,蜿蜒过台北的下缘,河边有着大片的草地,水滨开满姜花。
我早逝的父亲,曾领着初记事的我,站在河滨听说书和大鼓。也曾经将我抱在怀里,点
着电石灯,蹲在溪边彻夜钓鱼,我们还曾经坐摆渡,到河的另一岸,在暴雨中穿过竹林,避
入一所尼姑庵,吃她们种的大芭乐,听瀑瀑的雨声和轻轻的梵唱。
向东看,我已经离去整整30年的父亲,正从六张犁的山头,俯视着我。
小学三年级,他离开之后,我常站在龙安国小的搂上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