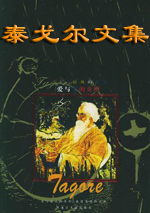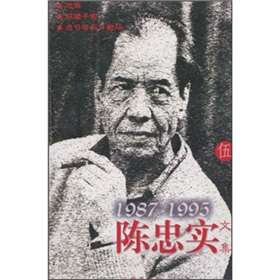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年、这又难道不是子女的耻辱吗?
过去穷,我们没话讲!
今天富,我们该多么庆幸!?可是在我们庆幸的时候,是否该想想自己有没有真尽孝,
抑或又是创造了一种假象!?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抱着一碗鱼翅汤当粉丝喝,我很不高兴地说:“那是留给奶奶
的!”
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讲:“奶奶说她不爱吃,叫我吃光算了!?
奶奶是真不爱吃吗?还是因为“爱他”,才特意留下来?
每年冬天,我的窗台上都排列着一大堆柿子。
为什么柿子一买就是十几个?因为我发现只买几个的时候,母亲知道我爱吃,总是先抢
着吃香蕉,等我叫她吃柿子时,则推说自己早吃过了水果。
只有当她发现柿子多到不吃就坏的时候,才会自己主动去拿。
当我为老母夹菜,她总是拒绝,说不要吃,我就把筷子停在空中,直到夹不稳而掉在桌
上,她才不得不把碗伸过来。
问题是,她哪次不是高兴地吃完呢?
相反地,当菜做咸了,大家不吃,她却抢着夹,我只好用筷子压住她的筷子,以强制的
方式,不准她吃,因为血压高的人,最不能吃咸!
“瞧!有这样的儿子,不准老娘夹菜!”她对着一家人“高兴地”抱怨。
我认为:当我们小时候,长辈常用强制的方法对待我们,叫我们一定吃什么,又一定不
准吃什么!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爱护我们!
而在他们年老,成为需要照顾的“老小孩儿”时,我们则要反过来模仿他们以前的作法
用强力的爱!
这不是强迫,而是看穿老人家装出来的客气,坚持希望他们接受晚辈的孝敬!
如此,当有一天他们逝去,我们才可以减少许多遣憾!因为我们为天地创造了一种公平
回馈,以及——
无怨、无悔的爱!
**********************
阶边一棵白茶花,下面有丛小小的棕榈,我常将
那弯弯的叶子摘下,
送到小河里逐波。
黄昏时,晚天托出瘦瘦的摈榔,门前不远处的芙蓉都醉了,
成群的麻雀在屋脊上聒噪。虫声渐起、蛙鸣渐
萤火虫一闪一闪地费人猜,
它们都是我的邻居,叫我出去玩呢!
星星坠落的地方
我记忆中住过的第一栋房子,在现今台北的大同中学附近。虽然三岁多就搬离了,仍依
稀有些印象。
记得那房子的前面,有一排七里香的树墙,里面飞出来的蜜蜂,曾在我头上叮出一个大
包。
记得那房子的后院,有许多浓郁的芭蕉,每次我骑着小脚踏车到树下,仰头都看见一大
片逆光透出的翠绿。
记得那房子不远处,有一片稻田,不知多大,只记得稻熟时,满眼的金黄。
记得一个房间,总有着漂亮的日光,那是我常玩耍的地方。但实在,我也想不起房间的
样子,只有一片模糊的印象——阳光照着我,母亲则在身边唱着一首好美好美的歌:热烘烘
的太阳,往上爬啊,往上爬,爬到了山顶,照进我们的家。
我发觉,我多少还能记得些幼儿时的居处,不是因为那房子有多可爱,而是因为蜜蜂的
叮、芭蕉的绿、稻浪的黄和母亲的歌。
幼儿的记忆就是这么纯,这么简单,又这么真!
真正让我有生于斯、长于斯,足以容纳我整个童年记忆的房子,要算是云和街的故居
了。我甚至觉得那房子拥有我的大半生,我在那里经历了生离、死别与兴衰。想着想着,竟
觉得那房子装得下一部历史,最起码,也像黄梁一梦。
不知是否对于每个孩子都一样,那房子里面的记忆,远不如它周遭的清晰。譬如明亮的
客厅,总不如地板底下,我那“藏身的密穴”来得有诱惑力;父亲养的五、六缸热带鱼,也
永远比不上我从小溪里,用眷箕捕来的“大肚鱼”。而母亲从市场买回的玫瑰,更怎及得上
我的小草花!”
童年的房子,根本就是童年的梦!
我记得那老旧的日式的房子,玄关前,有着一个宽大的平台,我曾在上面摔碎母亲珍贵
的翡翠别针,更在台风涨水时,站在那儿“望洋兴叹”!
平台边一棵茶花,单瓣、白色,并有着黄黄的花蕊,和一股茶叶的幽香,不知是否为了
童年对它的爱,是如此执着,我至今只爱白茶花,尤其醉心单瓣山茶的美。
茶花树的下面,有一丛小棕榈,那种细长叶柄,叶片弯弯仿佛一条条小船的树。记忆那
么深刻,是因为我常把叶子剪下,放到小河里逐波……。
小河是我故居的一部分,小鱼是那里抓的、小鸡尾巴花是那里移的、红蜻蜒是雨后在河
边捕的,连我今天画中所描绘的翠鸟,都来自童年小河边的柳荫。
还有那散着幽香的野姜花、攀在溪边篱落的牵牛……,甚至成群顺流而下,五色斑斓的
水蛇,和又丑又笨的癞蛤蟆,在记忆中,都是那么有趣。
做为一个独子,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要好的伴侣,竟然多半是昆虫!
小小貌不惊人的土蚱锰:尖尖头,抓着后脚,就会不断鞠躬的冬斯;长长发,身上像是
暗夜星空,黑底白斑的天牛:拗脾气、会装死的甲虫;不自量力、仿佛拳击手的螳螂;还有
那各色的蝴蝶和蛾子,都是我的故园的常客。
当然,黄昏时爱在屋脊上聒噪的麻雀,筑巢在厕所通风口上的斑鸠,以及各种其他的小
鸟,更带给我许多惊喜。最起码,我常能捡到它们的羽毛,用书本夹着,“一面读,一面
想,神驰成各种飞禽。
我在童年的梦里,常飞!虽然从未上过屋顶,梦中却总见房顶在脚下,渐远、渐小。尤
其是梦中有月时,那一片片灰蓝色的瓦,竟然变成一尾鱼,闪着银亮的鳞片,又一下子化作
星星点点,坠落院中……。
做梦的第二天,我就会去挖宝,挖那前夜坠落的小星星。我确实挖到了不少呢!想必是
日本人遗落的,有带花的碎瓷片、洋铁钉、小玻璃瓶、发簪,和断了柄的梳子,这些都成为
我的收藏,且收藏到记忆的深处。
看候孝贤的“童年往事”,那许多光影迷离的画面、静止的午后巷弄和叫不停的蝉鸣,
简简单单,却又强而有力,想必也源自童年似真非真,却又特别真的记忆。尤其是以低视角
取景的屋内,更表现了孩子在日式房间里的“观点”!
我记忆中的“观点”,虽在室内,却落在屋外。我常凭栏看晚天,看那黄昏“托”出瘦
瘦的摈榔,和窗外一棵如松般劲挺的小树。前门不远处的芙蓉,晨起时是白色,此刻已转为
嫣红。窗前的桂花,则变得更为浓郁。
虫声渐起、蛙鸣渐密。萤火虫一闪一闪地费人猜。它们都是我的邻居,叫我出去玩呢!
我常想,能对儿时故居,有如此深而美的记忆,或许正由于它们。因为房子是死的,虫
啊、鸟啊、小河、小树才是活的。活生生的记忆,要有活生生的人物。
我也常想,是不是自己天生就该走艺术的路线,否则为什么那样幼小。就学会了欣赏树
的苍劲、花的娟细、土的缠绵,乃至断瓦、碎瓷、衰草、和夕照的残破?
抑或我天生有着一种悲悯、甚至欣赏悲剧的性格,所以即使在一场大火,把房舍变为废
墟之后,还能用那断垣中的黄土,种出香瓜和番茄,自得滋味地品尝。且在寂寥的深夜,看
一轮月,移过烧得焦黑的梁柱,而感觉几分战后的悲怆与凄美。
失火的那晚,我没有落半滴泪。腾空的火龙,在我记忆中,反而光华如一首英雄的挽
歌。我的房子何尝随那烟尘消逝?它只是化为记忆中的永恒。
有一天,我偷偷把童年故居画了出来,并请八十三岁的老母看。
“这是什么地方?”我试着考她。
“一栋日本房子!”老人家说。
“谁的房子呢?”
老人家沉吟,一笑;“看不出来!”
“咱们云和街的老房子啊!”我叫了起来:“你不认得了吗?”
“哦!听你这么一说,倒是像了!可不是吗……。”老人家一一指着。却回过头:“不
是烧了吗?”
“每个故居,有一天都会消失的!”我拍拍老人家:“但也永远不会消逝!”
第六章 大地
据说从水底看海面
明亮
如同蔚蓝的穹苍
便想:
从大地看到的天空
会是另外一片海洋
想着想着
竟轻飘了起来
觉得自己是条漂泊的鱼……。
莲的沉思
在西湖,三潭印月的莲池边,凭栏站着一群人,大家争先恐后往水里抛东西,原以为是
喂鱼,走近看,才知道居然在扔钱。
仲春的莲叶还小,稀稀疏疏点缀着水面,而那幼小的莲叶竟成为人们游戏,甚或赌赌运
气的工具——看自己抛出的钱币,能不能准确地落在莲叶上!
或是由罗马传来的吧!而在罗马呢?则八成是想敛财的人想出点子,教大家丢个钱币、
许个愿,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再游那“七山之城”!
岂知这“点子”就一下传开了,不论维吉尼亚州的钟乳岩洞,或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埃
及神殿,只要在那风景胜处、古迹面前,能有一盈水,便见水中有千百点闪亮——千百个游
客的愿望。
曾几何时,西方迷信竟传入东方的古国,生性俭朴的中国人,又不知起地一下大方起
来,当然也可能是赌性吧!小气的人上了赌桌,也便不小气了。
就像此刻满天的钱币飞向池中,是为许愿?还是为了看看自己能不能正中莲心?
多数的钱,都落在了水中,毕竟池子大,莲叶小啊!
但是小小的莲叶,目标再不显明,又岂禁得住如此的“钱雨”?
一枚中了!
四周爆发出欢呼!
又一枚中了!
有人甚至同时丢出整把钱币:“看你中不中!?”
果然有些莲叶瞬间连中数元,在阳光下点点闪动,像一颗颗浑圆的露珠。
群众们愈得意了,钱币非但未停,且有更多人加入了抛掷的行列……。
小小的莲叶,多有钱哪!尤其是在这个并不富有的国家,只怕孩子们都要嫉妒了呢!
小小的莲叶,真是愈来愈富有了,不但钱靠着钱,而且钱叠着钱……。
突然——
默不作声地,那莲叶的边缘,向水中一垂,载满的钱币全溜了下去。
折下的叶边立刻又回了水面,干干净净、空空荡荡,一如未曾发生过什么事。
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有人骂出粗口,有人扭头便走。
只有那一池澹泊的君子,依然静静地浮在水面沉思……。
我心相印亭
柳,初展宫眉,春草已经蔓上了石阶,且不止于此地,在青瓦间放肆起来。是有那么多
的尘土堆积,使草能在上面滋生?抑或青瓦烧得不够透,日晒雨淋,又回归为尘土?
无论如何,“黑瓦绿苔”便有了些“白发红颜”的感触;黑瓦是愈黑了,绿苔也对比得
愈翠了。它更使人想起长恨歌里的“落叶满阶红不扫”,只是红叶萧条,描写西宫南内的凄
清。这“滋苔盈瓦绿生情”,写的是西湖堤岸挡不住的春色。
先是被亭瓦的景色吸引,游目向下,竟还有个惊人的名字,说她撩人,倒也不似,只是
引人遐思。
“我心相印亭”,多罗曼帝克的名字啊!令人直觉地想到情侣,便步人其中,看看会是
何等隐蔽的处所。
“不隐密嘛!”看到那不过几道栏干,且伸向水面,四望毫无遮掩的亭内,我失望地
说。
“您未免想多了!”一位正凭栏的老先生回头笑道:“坐!坐!坐!坐下来看这湖水,
看这水中的倒影!看看水中的你,你眼中的水,看你的心、湖的心,心心相印!”
如伽叶的拈花,我笑:
***********************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西湖人去尽,我心相印亭!”
云泥
你追过云吗?我追过!
你洗过云吗?我洗过!
少年时,我爱极了登山,而且是登那人迹罕至的高山,在不得不归时才离开山。
云就在那时与我结了缘。
晴朗的天气,山里的浓云,必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会出现,午间直射谷底的阳光,将
山林的水气逐渐蒸发,缓缓上升。这时由于日光已斜,山背光和向光面的寒暖差异,造成气
压变化,而引起山风,将那谷中的淡烟拢成迷雾、攒为浓云,且在群山的挤压下迅速腾升。
云就在那时与我追逐。
我知道被浓云笼罩的山路是危险且难以呼吸的,所以总盼望在云朵与云朵之间的空白处
行走。远看一团浓云,即将涌上前面的山道,我们就奔跑着,趁云未上的时刻通过。
尤其记得有一回穿过山洞,身后正有浓云滚滚而来,我们一行人拼命地在洞里跑,那云
居然也钻入了洞中,在我们的身后追逐,回头只说得原本清晰的景像逐渐模糊,所幸眼前山
洞另一侧的景物依然清明。正高兴赢得这一场,肆情喧笑着跑出洞口,却又顿时陷入了十里
雾中,原来那在洞外的云跑得更快,竞偷偷掩至我们的身边。
至于洗云,你是难懂的,但若你真真洗过云,必会发现那云竟是淡淡的一抹蓝。
有一年秋天,我由龟山脚,过鸬鹚潭,直上北宜之间的小格头,由于在潭里盘桓过久,
而山色已寒,使我们不得不赶路,否则一入夜,就寸步难行了。
正值霪雨之后,那时到小格头的山路仍是黄土道,出奇陡斜而湿滑的路面,使我们常不
得不手脚并用地攀爬,一直到将近小格头,才喘口气地回头看一眼。
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哪!千层云竟然就在脚下不远处,涌成一片浩渺的云海,我们
则是从那海中游出来的一尾尾的鱼!
等公路局的客车,同行的女孩子对我说:看你脚上都是云泥,让我帮你冲一下吧!
云泥?可不是吗?那是云凝成的泥,泥里夹着的云!
灰暗的晚天下,我确实看见她用水冲下的,不是黄土,而是深深宝蓝色的——云泥!
*******************
雾白
曾看过一部恐怖电影,片名是“雾(The…fog)”,描写由海上来的鬼船和厉鬼们,随
着浓雾侵入小镇。
事隔多年,已经记不得片中的细节,倒是那由海上瞬息掩至的浓雾,在灯塔强光照射
下,所发生的深不可测的光彩,总在脑海里映现。
那是当光线照上去,表面反射一部分,穿透一部份,又经过层层云雾,再三反射与穿透
之后,所产生的神秘之光。它不像逆光看去的云母屏风那么平,也不似月光石折射出来的那
样晶晶亭亭,而是一种柔软均匀,又能流动的东西。
每当乘坐飞机,穿越云层的时候,我都极力想从窗外捕捉这种映象,只是日光下的云
雾,光洁有余,却总是少了几分神秘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