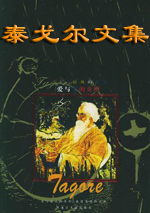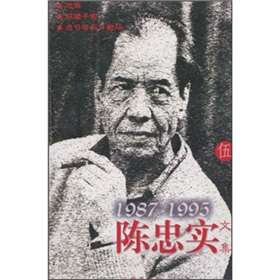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开始早晨“拜”镜子,花几十分钟梳头,也不再吃营养午餐,因为在学校餐厅吃饭
“不酷”。有一天,我也发现老爸的皮夹克太逊了。
女生也一样,忙着找高年级的男朋友。“眼袋”是她们最大的敌人,最棒的话柄则是谁
在胸罩里垫卫生纸,或是谁的迷你裙,短得露出三角裤。
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些都不够。“酷”的真正定义,是“做自己想做的!”而自己想做
的,常是家长、老师不要我们做的。愈不要我们做,我们愈要做。我们进入了叛逆的年代!
问题是,史岱文森的家长偏偏都很严,使我们在叛逆中加上了矛盾。在家里死命K书,
到学校则说:“我才不念那讨厌的课本!”女生们白天指别人化妆好浓:“简直像荡妇!”
晚上参加舞会却都穿着再紧不过的衣服。看到她们踩着高跟鞋,站着都快跌倒时,我真不晓
得,大家如此叛逆,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讨好别人?
有一次马克指着远处一个抽着烟、叉着腰、头发作成Mohawk的庞克:“知道他吗?我
跟他一齐上过小学。去年,他还是每个扣子都扣、裤子拉得高高的乖孩子。想不到吧!一年
间,竟换了个人!”
这就是寻找“酷”。你要想尽办法,找最叛逆的朋友、穿最叛逆的衣服、做最叛逆的
事。只是,当我们把自信穿在衣襟上,心里却是个大问号。
刚进高中时,别人的认同,就是自己的酷。偏偏有些人因此失去自己。那群整天坐公园
里喝酒的同学,彼此总是在说:“哈哈!我们太酷了!”但是当哪个人不及格的时候,却被
那群很“酷”的人,认为不够酷。连这么一点简单的功课都弄不好,在史岱文森,你还有什
么资格谈“酷”?
跟“酷”相反的,当然是“不酷”——有些父母在门后挂上家法,不准儿女出去一步。
有些甚至连流行歌曲都不让听,夜里还偷偷到孩子房间,看他们在读书或真睡着了,才能安
心,生怕自己的小龙、小凤,有一天也会叛逆,被“酷”的魔力吸走,不当医生、律师了。
在史岱文森,小龙小凤第一节背着霸气书库到,第八节背着霸气书库离开,没有课外活动,也不
敢交异性朋友。问“你的热爱是什么?”他们只会茫然地看着你。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在
毕业册上,他在自己的照片下写:“我虽然离开学校,但离开得太安静、太安静了!”
叛逆的年代,是无法找替身的。它甚至今你难以理性来分析。有一次,我被很“酷”的
同学邀请去他的Party。我们在餐馆用食物打闹,坐在大楼屋顶上死命灌酒,深夜时大家脱
了衣服在马路上裸奔。
又脏又累地到家,发现家人在门口点了一盏灯。上楼倒在床上,叛逆是够了,可是为什
么觉得一点都不酷?
※ ※ ※
美国的名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Erikson)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他说,每个人在青
年期都会面临“寻找自己角色”的总理。换句话说,就是自问:“我到底是谁?”
在高中四年,我常躺在床上,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痛恨自己老是跟着人家走,听着流行
使唤。奇怪的是,当我怀疑永远找不到“酷”时,答案已在眼前。
有一天,那位曾经头发竖起来的庞克,竟改回老实的发型、背着霸气书库走进教室。大家差
点不认得他。我们问他,为什么一下子“变了”?他说:
“老子酷!但老子不笨!”
叛逆,只是寻找“酷”的过程。真正的“酷”,就是找到自己!
********************
我躺在黑暗里,瞪着天花板,
听着她的呼吸,心中却在大叫:
“惨哪!惨哪!”
恋爱新鲜人
不晓得从什么年龄开始,男生和女生好象成了仇敌,小学的舞会总是一样——“我们”
男生站在一边,“她们”女生坐在一边,中间空着一个大舞池,每次都必须由老师扮小丑,
把我们一一拖下水。
那时候如果有女生喜欢某人,只要放出一句话,便立刻有一群朋友连蹦带跳地到那男生
面前一齐叫:“某某人觉得你可爱!”然后嘻嘻哈哈地跑掉。
只见那男生脸一红,踢着地上的沙子说:“真无聊!”第二天却听说有人在电影院看到
他们两个。
我常跟同学说自己很幸运,从来没被“媒婆们”缠住,但每次笑朋友被女妖精抓走时,
心中却有点怪怪的。
八年级时有一天,肯尼告诉我:“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班上新转来一位韩国女生。她的名字叫Sunny-小太阳。
“你不是想要个女朋友吗?太阳出来了,快去啊!”同学们笑着说。
我气死了!只因为两个都是东方人,大家就认为我们一定会坠人爱河?难道我不能喜欢
别人?
大家愈想把我和小太阳凑在一块儿,我愈火大。有一次在舞会上,不晓得哪个混蛋给我
们点了一首情歌,害我躲进厕所里。到最后,我和小太阳非但没成情侣,反而彼此恨之入
骨。
有个女生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Sunny?”
“因为她丑!”
”我觉得她很漂亮啊!她哪里丑?”
“她是小眼睛。塌鼻子!”回答。
“可是,”那女生笑着说:“你也一样啊!”
我愣住了。
爱情入门时
到了九年级,才交第一个女友。
她名字叫丽艾,比我大一年,竟会看上我这个“新鲜人”,真是新鲜事。
我没告诉她,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友,怕她看不起我。第一次约会的前一天晚上,我紧张
得睡不着觉,爬起来查百科全书,“接吻”应该怎么做?
外行人想装内行,是件痛苦的事。她跟我谈天时,我猛点头,脑子里却在死命想下一个
动作应该是什么;她拍我一下,我也拍她一下。她大笑,我也大笑。
到最后,她还是把我甩了——她找到了“上路”的男生。
电话里,她问我:“你不生气吗?”
“没什么!”我说:“这种事发生多了!但我想知道的是,你碰到别人,为什么要告诉
我?”
“你是我的朋友,当然要告诉你!”她说:“跟你说真话,是对你的尊重!”
爱情看不到颜色
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叫拉娜。她有修长的脚,可爱的笑容和活泼开朗的个性,是全校公认
的最美的黑人。
同学们恭喜我,能够追到那么漂亮的女朋友。我高兴地把拉娜带回家,老爸、老妈客气
地和她寒暄,但拉娜一走,他们的脸便挂了下来。
从此,我常为了拉娜和奶奶、老爸、老妈吵架。有时我气得冲出去,在高速公路旁边哭
着打电话给她。
老爸说,人生而平等,他们绝不歧视拉娜,但必须考虑的是:亚洲人的社会能不能接
受、认同她?
我记得在马克匪让牛∕ark…Salzman)的小说“铁与丝(Iron…and…Silk)”里,一
位到中国大陆的非洲留学生说:“身为个非洲人,却住在中国,噢!实在难受!中国人看不
起我们,好象我们不是人,是野兽!”
我实在不懂。打开中文杂志,模特儿都是白人,我们能够欣赏白人的美,却为什么那么
排斥黑人?日本人的纽约观光手册上写:“小心被黑人抢!”难道白人不会当抢匪?当年白
人的八国联军到中国烧杀抢劫,黑人可曾对我们不好吗?我们曾被白人歧视,而今却又彼此
歧视。
黑人确实也不能认同我。和拉娜坐地铁时,当听到黑人少年说:“你看她跟李小龙在一
起!”有一次,拉娜在临下巴士时亲了我一下,后来居然有一个黑人,在他下车前走向我,
一拳挥到我脸上。
他们想告诉我什么?
说拉娜是“他们的”?抑或“你瞧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起你?”
现在纽约街,常看到白男生和东方女孩,或黑男生和白女孩的情侣,也常见他们穿的T
恤上写:“爱情看不到颜色!”使我很高兴。
但回想洛杉矶暴动时,韩国人拿着长枪坐在商店前的画面,和我咬着嘴唇跟拉娜分手的
那一刻,我实在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惨哪!惨哪!
有一次久安娜Joanna跟她当时的男朋友吹了,气冲冲地对我说:“我觉得男生都用第
三只眼睛看世界,用第二个头想大事!”
但她也承认,若女人的性颠峰期不在三十岁,而跟男生一样在十八岁的话,少女们可能
就不那么贤淑了。
在性贺尔蒙使唤下的日子不好过。记得天主教初中的性教育老师曾说:“若有感动,必
须好好祷告。”但以我的经验,多少个“我们天父”或“阿弥陀佛”都没用。更痛苦的是,
我们从来不晓得女生们心里想什么。这造成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少女强暴案中有一半是
熟人所做;有时是女生自己的男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约会强暴”(Date…rape)。有些大
学现在甚至发印好的“合约”,“男女生在上床前先签字,证明双方同意,免得以后吃官
司。
十八岁时,我认为女生比较道德,很怕她们。
有一年,史岱文森的法文老师带我们去加拿大,一到旅馆,跟我同房的几个男生便掏出
大麻开始抽。我无处躲,便搬到女同学伊凡娜Ivona的房间。另有一个女生和她共一张床,
但是很大方,让我跟她们一起睡。
几天下来,我认识了那女孩。她学舞蹈,一举一动都很美。伊凡娜跟我说她曾有过许多
男朋友。我们一块儿去跳舞、观光,不久便很亲近了。
最后一天,伊凡娜对我说:“玛丽安好象想要你。”
“真的吗?”我非常兴奋。
“嗯……但你必须走第一步。”
我的老师很开放。我去跟他要“袜子”,他丢给我十个。“用完再来拿!”他笑。
那天晚上,伊凡娜故意没回来。我紧张死了,早早便躺在床上。马丽安穿着睡衣,斜躺
在我身边,用手托着下巴。
“嗨!”她说。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这几天很有意思。”
“嗯!”
这样僵持了许久。终于她笑起来:
“OK,晚安!”说完,便翻过身去,睡了。
我躺在黑暗里,瞪着未花板,听着她的呼吸,心中却在大叫:“惨哪!惨哪!”
当沙莉不要哈利
美国有部有名的电影,叫“当哈利遇上莎莉”(When…Harry…Met…Sally)。电影开始,
少年哈利带着嘲讽的口气对莎莉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性总是会在中间插一
脚。”
我曾很同意哈利的这句话,但有了玛丽安这次的经验,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当君子。
有一天,我和女友吹了,本来要回家好好弹一首抒情曲,但心里愈想愈不是滋味,便拿
起电话,打给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前任女友的伊莉莎白。
她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心中的痛苦都吐出来。最后她说:“我有个主意,到城里来!我
请你去跳舞。”
“可是我才从城里回来啊!”
“那又怎么样?坐下一班火车嘛!”
正好那天老爸、老妈不在家,于是我便毫无顾忌地又冲出门。伊莉莎白带着我去跳舞、
喝咖啡,陪着我聊天,使我心里舒服多了。
“已经太晚了,今天就住在我家吧!”她说。
多么绝的举动了!坐在沙发上,我心想:“只怕她是想趁火打劫。”只是当我贴近她,
她却移开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问。
“你记得曾经告诉过我,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吗?”她拍拍我的头:“你错了!”
爱情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搞懂了,才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
**************
你宁愿天天打仗、
考一个又一个“会考”、“能力测验”,
再写一大堆文章、填一大落表格、寄一大包东西
还是愿意一战定江山?
天天考大学
每次回台湾,总有年轻朋友对我说:
“真羡慕你们没有大专联考!”
言下之意,似乎只要废除联考,就可以海阔天空、不必K书。
言外之意,似乎国内的联考制度一无是处,只会扼杀年轻人的青春和才华。
连我的老爸都说,一直到前两年,他还会半夜突然满身冷汗地惊醒——“要考联考
了!”然后,才发觉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问题是,老爸也讲,幸亏台湾有联考,他才能靠最后两个月死拼,进了大学。假使台湾
是用美国入学审核的制度,只怕他不可能有今天。
可不是吗?国内的联考固然是“一考定终身”,但也在此一举。换成美国,除了“会
考”SAT的成绩之外,每个学期的在校成绩,甚至课外活动的表现,都列进“入学考虑”,
等于是“天天在考”,平时也是战时。
我才进高中,学校就发给每人一份统计报告——过去本校毕业生,被各大学录取的最高
和最低平均分数。意思是:你如果想进好大学,就从现在开始拼命!
高二,学校又把大家聚在礼堂,讲台上坐了一堆学长,都是当年得到西屋科学奖的“学
者”。然后,校长致词:
“你们要向他们看齐,现在就开始做西屋科学奖的研究,过一、两年之后去参加。”
致词结尾,少不得加上这么一句:
“如果你得了大奖,进好学校就不成问题了!”
于是,许多同学暑假都不回家,跑到大学实验室,跟着教授做研究。
至于学业成绩稍弱的,也各自找“生路”!
两位有洁癖的同学跑到医院,专门照顾垂危的爱滋病患。然后疑神疑鬼,怕自己被感
染。
几个瘦得像排骨的同学,居然参加了篮球和排球队,每天累得快要散掉似地。
他们为的恐怕只是有些课外活动或社会服务的纪录,将来帮助自己进大学。(当然也可
能出于爱心和兴趣!)
※ ※ ※
申请大学!天哪!何尝不是一场噩梦?
厚厚一叠资料,挂号寄出!里面可能包括了你小学比赛的奖状、初中参加游泳训练营的
泳装照片、某年在社区小报发表的短文剪报、某年在同学会中表演歌唱的录音带、帮助某作
家校对的“版权页证明”、老人院义工证明、万言自传一篇……
此外,还得答覆每所大学稀奇古怪的总题。
譬如我那一年——
哈佛大学(Harved):
“列出你一年来读过的书,和最近看过的杂志!”
宾州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A)“假如你有机会和一个现存的、已死的或传说中的人物,共聚一晚,你要选谁?
为什么?”
(B)“你刚写完一份三百页的自传,请送来第二一七页!”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A)“简答以下问题。别紧张睡不着觉。
最喜欢的书?最喜欢的音乐?最喜欢的活动?最喜欢的电影?最喜欢的报纸版面?最喜
欢的句子?最珍惜的事物?一天中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