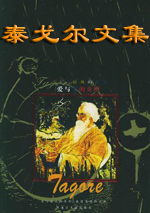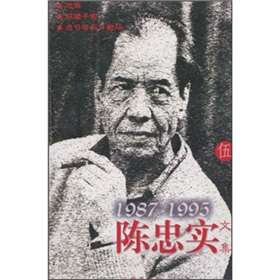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9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的死角。于是抓着这里,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门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门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让杀手垂直攀在墙上,采取最佳的“刺
杀位置”。
然后,我掩上了玻璃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杀手不会放弃任务逃跑。每个雇用杀手的人
都应该懂,先要防杀手变成杀自己人的道理。
我由玻璃门的上面往下偷窥,可惜因为位置太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听到那逃亡蛐
蛐的叫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渐渐,声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里暗念:“派蒂啊!你可千万别离开。”
突然,叫声停止了。我慢慢拉开门,派蒂还站在原来的位置,手里多了个不断跳动的东
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发声器,怪不得没了声音。
我不能不为派蒂欢呼,也为我自己欢呼。
多棒啊!手到擒来。蛐蛐原来一定自鸣得意,以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鸣大放。没想
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虫类的杀手,早已掩至它的门外、卧了底。
我的杀手多聪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声音”。
割掉舌头的囚犯,就连死前喊冤的权利也没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边,看着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这是异议分子的下场。”我对母蛐蛐说:“他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
只是替大行道!”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下来了。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
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
喜欢在窗外种芭蕉。连我的空气清净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
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
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
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
“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就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
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
安。”那不安来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
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多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
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
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爱斯基摩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
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
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
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
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余风细雨,重
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
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
子、才女,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
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我想不该用“克”这个字,因为太大男人沙文主义。我应该说赵明诚要是没有李清照,
早就成为历史沉沙的一小颗,不会被人记得。甚至李易安后来改嫁的张汝舟,也要感谢这个
二嫁的老婆,多亏她,张汝舟才能进入历史,而且被后代的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一直吵
到今天。
可不是么?有一回我在广播电台上谈李清照,说她后来改嫁给张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
生狠狠骂了,说李易安这样才华高旷、冰清玉洁的奇女子,怎么可能改嫁。
我回说,就因为她才华高旷,所以欲望也过人;也正因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
俗挑战,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细数数,历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
为?我们总说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实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
给甩了。老公活着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么顾忌?配偶!配偶!有一边发了,或有
一边死了,既然不再“配”,还怎么成为“偶”?
我这玻璃瓶里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后夫合伙吃了,后夫逃
亡之后又被刺杀。剩下一个“她”,居然一会儿吃葡萄,一会吃尸肉,过得十分快意,我是
不是应该再为她找个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这家伙自从“出差”之后,就特别不安。总是扒着罐口的纱布,想往外
跑。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当然觉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为到了“发情期”。外面螳螂的寿命,顶多撑到十一月下旬,到时
候算不饿死,也得冻死。加上它们还要怀胎一段时间才能产卵,现在当然该“成婚”了。前
几天的那个“客人”,虽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触中,也会激起她性的联想,尽
管后来把对方杀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却再也难以平息。
没有错,即使不是同性恋,看到同性的裸体,也会动情,甚至看自己的裸体,都能产生
联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时,都要穿一件特别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体,而产生
遐思吗?
性的不能满足,最会造成不平静。我想,说不定派蒂把朋友杀死,就是因为性的焦躁,
而不是为了“猎食”。否则她为什么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连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产生很大的问题。幸亏派蒂先在出任务的时
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后来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喂她。尽管如此,算下来,她
在过去六天,只吃了两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从在“病”中喂她喝过水,现在只要我把“鸭嘴笔”递下去,她就会
伸着脖子喝,一次总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虫,更造成我没有机会为她找丈夫,眼看天气愈来愈冷,杀手的脾气
愈来愈躁,她的寿命愈来愈短,我自己也开始烦躁了。
突然想到台湾著名的昆虫学家陈维帮。他应该算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
功高中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后来去母校教课,更见识了他的“昆虫馆”。以那时候台湾
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
胶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为什么不装在一个盒子里?”我问他。
“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他说。
“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我说。
“对!对!对!”他笑着,作出很奇怪的表情:“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
“头被咬掉才会快乐?”我叫了起来。
“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我诘问他。
“我看得出来!”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
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
“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
螂,连盒子,一起送给了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
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
第九章 苍凉时代的刀客
趁火打劫
十月十九日
霪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一下子变得明艳照眼。
秋天有时候比夏天还亮,因为深绿色的叶子都变成黄红色,再不然凋落了,阳光更容易
在叶子间反射、穿透。
秋天的光影特别美。尤其在北国,太阳向南移,过了赤道,所以即在正午,阳光也是斜
的。斜斜的阳光从林木间洒过,造成一长条、一长条的阴影,和亮丽的阳光对比,就益发黑
白鲜明了。这时候如果有小鸟、小虫和毛绒绒的种子飞过来,飞进“阳光带”,造成反射,
加上后面是黑暗的树影,就变得格外清晰。
也幸亏有阳光的特殊效果,使我能在这萧条的季节,连续捉到两只大黄蜂,我想它们都
是饿了好几天,急着出来找死蝉吃的。“噤若寒蝉”,天一寒、一雨,那些蝉就不但不叫,
而且纷纷冻死了。一只只仰着面,躺在草地上。蝉的肚子是白色的,在绿草的衬托下尤其明
显。那些找死蝉的黄蜂都飞得特别低,小小的虫在草地上飞,从高处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也
采取低姿势,甚至趴在地上看。
趴在地上真是绝妙的方法,我可以把几十英尺的地面,看成一小片。在这一小片的天空
中,任何虫子飞过去,都逃不出我的法眼。
草地上积了水,潮湿的草皮很脆弱,稍稍用力踩,或者跑得快一点,就可能整块破掉。
霪雨前种的草籽都萌发得好极了,何必说“春草如碧丝”?其实秋草也可以像是“碧
丝”,《诗经》上用“美”,也就是初生的小草,形容女人的手,真是“观物精微”。贴近
地面,看风里摇摆的新新小草,像是千万双小手挥来挥去。
一般城市里的人,都以为植物该在春天下种,岂知大自然是在秋天种的。想想,秋天不
是结实的季节吗?那果实掉在地上,不就是播种的时候?
许多庄稼,也都是在秋天下种的。譬如麦子,秋天播了种,开始萌发,跟着来了冬天的
风雪,等到来年再发,反而能长得更好。
秋天不也是移植的好时候吗?被移植的树木,一定受了伤,如果春天移,跟着天气热、
消耗大,容易死。秋天移,下面是生机较弱的冬天,偷偷长下面的根,也偷偷适应,接受被
移植的命运,等到第二年春天,就又是个“新人”了。许多人需要冬眠,尤其碰到打击的时
候,要躲起来、安安静静地承受,再平平静静地接受,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场雨真是帮了我不少忙,我发现世界上多么好的“花园喷水系统”,也不如老天爷的
这一个。花园喷水是平均照顾每个角落,老天爷则不一样。这大概与一般人想的恰恰相反,
大家总想着老天爷是最公平的。其实错了!老天爷并不公平。你看!在大树底下的草地,雨
水被大树遮了,当然水会少些。至于上面毫无遮荫的草地,则有百分之百的雨水。老天爷的
待遇怎么会是公平的呢?它反不如人工喷水,算好位置设“喷头”,一片片水幕,使每棵小
草都能得到一样的水分。
但是你再想想,树荫底下和空旷地方的小草比起来,谁受的阳光强?容易被晒伤、晒
干,而需较多的水分补给?当然是后者。相反地,如果树下的小草,水太多了,又没有足够
的阳光,还生霉而死。
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最聪明?它看来不公平,其实公平。它的“雨露均沾”,不是一律
给一样多,而是看你天生的才具和后天的环境,该给多少给多少。少拿一点不见得是倒楣,
有时反而是福不是祸。
在草地上爬,我的“手”告诉了我这个天机。
两只黄蜂,一进派蒂的房间,还在门口,就被抓走了。我发现这杀手的记性很好,它似
乎已经知道,当我抖动塑胶袋的时刻,就表示有东西吃。这时候,虽然罐子上的纱布已经拉
开了,它也不往外冲,它是知道优先顺序的,在这个时节,吃饱大概比逃跑来得更重要。
我也真不了解,为什么这两只黄蜂好像去投怀送抱,统统才进“玄关”的位置,就被派
蒂请进了肚子,连一点挣扎的声音都没有。
或许因为派蒂的猎杀功力,是更上层楼了。最高级的杀手是让目标自己过来接受死亡,
而不是去追杀。如同最高明的摄影记者,看来不是抢镜头,而像是把镜头及时地举起,那新
闻人物就自然把最好的角度送过来。
无论抓什么虫,也无论那虫是以何种角度进人派蒂的攻击范围。我发现,当派蒂抓到它
们的时候,它们都是面朝下的。就像通过产道的娃娃,似乎老天规定,多半要面朝母亲肛门
的位置。
也可以说派蒂必定选好“背”的位置下手。两只钳子,一只钳着颈子、一只钳着腹部,
第一口先咬去翅膀,然后顺着吃最有肉,又最能致死的上身。吃完上身看看头好不好吃。不
好吃就扔掉,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吃肚子。
多半的昆虫跟人一样,所有的口器、六肢都是向前的。可以抱着咬,咬着踢,更可以弯
起屁股,用上面的毒针向前刺。所以当它被派蒂从后面抓住的时候,这一切攻击的工具就都
不管用了。
我也想这两只黄蜂,在“别人”都因为天寒,而躲在巢里不出来的时候,它们为什么还
要出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那些在半夜三更,最不安全时刻受害的
人,常是最可怜,或最勤快的人。可能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的女生,也可能是为了给孩子
多存点钱的父母。
落魄的强盗抢落魄的人;苍凉的时代向苍凉的人下手;可怜人欺侮可怜人。不知道这些
“施害”的人,是不是都发展出他们的“存在主义”。
记得以前在仁爱路的中视上班,紧邻的违章建筑区失火,我们站在中视的楼顶,看到有
人抱着电视机从火场跑出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电视是我同事的,他住在里面,急着救
火,没想到电视被人先“救”走了。
也记得我母亲说,当年逃难的时候,专有人出来抢。“这时候抢最好了!平常没人往人
烟稀少的地方走,逃难时就有了。平常身上不带太多值钱的东西,逃难时宝贝全带在了身
上。平常有警察,这时候警察不但管不了,只怕自己有家伙,先变成了强盗。”
说完,我的老母还笑笑,仿佛那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想到这个,我傍晚又出门,抓了一只大黑蜂进来。
时局已经乱了,再不抢就没得抢了。赶快抓两只给我的宠物吃,改天没得吃,只好饿肚
子了。
在这时局动荡的秋暮居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