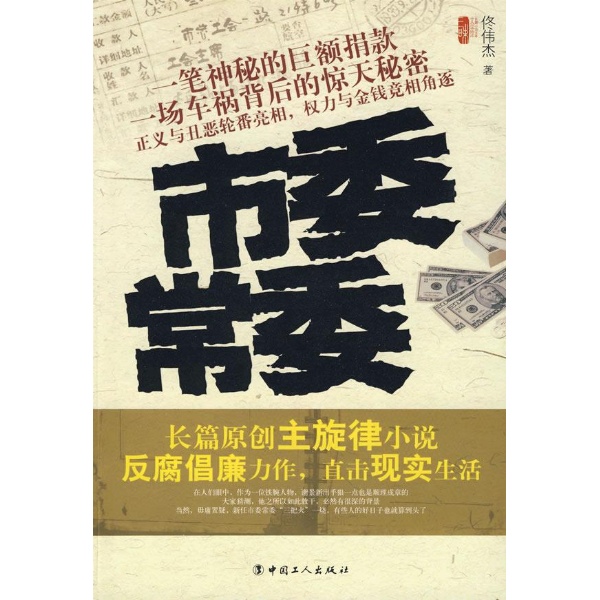市委常委-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午,他终于接到市委副书记武乃群的电话,得知这次市委组织部考核,他在机关得票数第一。乖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天润滑的各方面关系,终究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常务副主席这个职位基本也就十拿九稳了。
他翻了翻工作计划表,心想,今天干什么呢?干什么好呢?
该做的事情太多了。配合省(‘文’)里工作组(‘人’)调查城建二(‘书’)公司的资产流(‘屋’)失问题,尽管那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工作,甚至很难有什么确切的结果,但表面上还是不能放松,有些姿态还是要做的;送温暖工程有待研究,年初上级工会有部署;氧气厂有个工人从铁架子上掉下来了,应该就这件事再抓一下群众性安全生产;河东区的新企建会进入第二阶段,应该去鼓鼓劲儿;市总工会成立50周年纪念画册的事,还得过问一下,设计的那个封面有点“那个”,必须调整过来;宣传部长笔头子不行,配合工会十大的系列宣传,怎么至今才见报两篇;十大报告该定稿了,已经写了五稿,昨天晚上他又认真在文字上作了一遍润色,自认为已经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但他不明白,每次给谢景新看完后,这个一把手都不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市工会十大的会期已经推迟了两次了,还要推迟到什么时候呢?对此,谢景新似乎并不着急,近些天来很少过问报告的事,一直热衷于在下边跑,不知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方军每想起一件事,便反射出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兴奋,真正该做的事无法列入工作计划,上级也根本不会按你的工作计划表来评价你的工作。该做的事情如此之多,足够三个副主席受的,以至于一闲下来,方军就担心会出什么闪失,这样的紧要关口无疑要稳,只要市工会十大一切顺利,市委组织部把确定的人选一推荐,自己就肯定能当选。他提醒自己:学会放松,泰山崩于前而不失悠然之心。干吗我老去找事,也该让事来找找我。于是,他想,今天就坐这儿不动了。
刚上任的法律部长冯勇进来请示:“矿务局打来电话问,方副主席今天下午去不去参加他们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会议?”
方军正色道:“不去了。你们法律部也别去人。让他们自己搞。我倒要看看市里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会不会塌台。”
“那好。”冯勇进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离去。
物业公司的服务员进来送报纸,方军叫住她,翻了翻她怀里的一堆信,看有没有和自己有关的,再示意她离去。
方军粗略地浏览《工人日报》和省市的报纸,没有S市工会内容的报道。他沮丧地把它们推到一边,只抽出一份《报刊文摘》插在口袋里。从茶几下面拿出卫生纸卷,揪下好长一截,塞进裤兜,有意压慢步子,朝厕所走去。这时候,他感到惬意。
市总机关的厕所清洁安静,全无气味。物业公司每天水洗一次,这是方军督促办公室严格规定的。厕所如同办公楼的收发室,都是一个机关的脸面。想知道这个机关人员素质如何?你走进厕所抽抽鼻子,便能嗅出个大概。
方军曾在班子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教训。他说,去年省里有位副省长到本市一个先进单位检查工作,各方面都还不错。可惜领导临走之前,上了趟院子里的厕所,恰好这个厕所是个旱厕,味不可忍,这位副省长鼓足勇气才蹲下去。噗嗵一声,溅上来的比拉下去的还多,领导差点儿昏过去。兜里的手纸都揩完了,屁股还没揩干净。副省长出来,市长、局长等在门口送行。副省长一言未发,登车走了。一个市、一个单位的工作,就“噗嗵”一声“报销”掉了。省领导留下的“深刻印象”,只有下一次再到这个单位时才有可能改变。可是一个省里领导什么事也不干,光是走一走全省的机关事业单位,也要三四年时间啊。这意味着,这位副省长在任期内不可能再到这个单位来了。这个单位根本就没有改变这位领导印象的机会了。
方军说:“大领导的眼光和我们一般领导不一样,他是察人之未察,言人之不言。我们可不能叫这样的”悲剧“在市总工会重演。我的想法,请大家就这件事作原则领会,不要笑完就算了。”
方军所说的那位副省长,去年确实到过S市,至于领导上厕所“噗嗵”一事,则有杜撰的嫌疑。不过,在座者无人不信服,它听起来那么真实,起了强烈的警钟之效。
方军重视厕所。上大学时,他就喜欢躲在厕所里读书看报思考,那里不受人打扰,解一次手,他能读完两万多字的东西,起身后,决不会头晕目眩。及至当了市总工会副主席,这个习惯仍未断根。久而久之,厕所成了他思考时的据点。他经常带着问题进来,带着办法出去。有一次解手,长达40多分钟,厕所外有人两次敲门。他忽然意识到,有人注意自己这个习惯了,他们会对此做某些杜撰。于是方军开始限制自己,每次上厕所带一两份报纸进去,看完就出来,争取半个小时内解决问题。
唉,领导者的自豪与悲哀,都在于时时刻刻被人注视。他想,把众人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目光从自己这儿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
“方主席,方主席!”外边有人急切地叫他,方军迅速完毕,把每一个纽扣都扣好,再给脸上搁一点儿笑意,大步走出厕所。
十几米开外,办公室主任尹玉半开玩笑地说:“方主席,你听见了,动作挺麻利呀。”
“干吗?这么急?”
“谢主席找你。”
“见鬼。我以为是上级来人了。”方军不满地白了她一眼。
这时谢景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方副主席,你一天比一天让我敬重。怎么着,上厕所也不忘学习?”
方军立即露出笑脸:“哎哟,主席,可别拿咱们开涮啊!据说伟大的马丁路德,一直苦于找不到宗教改革的理论依据,有一天在威登斯堡修道院的厕所里解大手,突然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信及义,从此才得以启动宗教改革的方舟。”
谢景新边走边说:“很深刻。走吧,下午陪我下去转转。听说市焦化厂改制很成功,咱们得好好总结总结。”
“好,本人今天亲自驾车,陪同主席!”方军兴致蛮高。
“那好啊,难得方主席有这么好的兴致!”
36
三个人下楼来到门口,方军先把司机小孙打发走,然后上前一步帮谢景新拉开车门,模拟领导秘书的样子,把手掌搁在门框上。
谢景新坦然地接受了小小的戏弄,坐进前座,尹玉自己拉门钻进后排。
谢景新调侃道:“哦,本主席要配备正县级驾驶员啦。不过,你的驾照是后门办的吧?”
方军一愣,觉得谢景新话里似乎已经认可了他,便也油腔滑调地答道:“主席,这种玩笑不等于陷害吗?我是正经进过班的,只不过最后的时候,上坡起步没弄好,找人了,简单得很,没5分钟就让我过去了。”
“大胆。我随时可以揭发你,这一点你可要知道。”
“我帮你也弄一个吧?我知道你会开车,但你怕影响不好,不敢开。弄一个就合法了。开车是运动,也是休息。你看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发过多少证件!”方军滔滔地数出一大串名目,“顶管用的还是驾照,到时你就知道了。”
谢景新注视着车前路况,承认方军车开得不错。里程表显示,车的时速转眼就从5公里达到60公里,几辆车被瞬间超过。方军的每个动作都撩拨谢景新的驾车欲望。但他抑制着,出于一种坚信:方军那种生存方式终究会倒霉。他也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方军那张保养得很光滑的脸,轮廓的确和方红很相像。如果他们真是姐弟俩,生存在同一城市里,境况天壤之别,相互之间竟然毫不知晓,这可真是有些悲哀了。
“你开车出过事没?你说如果翻车了,咱俩都死了,对工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谢景新调侃道。
方军惊异地看了谢景新一眼。心想,此人的思维可真可怕。
谢景新继续说:“对市总工会当然是坏事,毕竟缺了两人。不过对于干部来说,是个好事,咱俩一下倒出两个官位。”
“你准备安排谁为继任呢?我想你不把继任者安排好是不会安息的。你肯定对善后事宜心中有数。”
“当然喽。某某和某某,顶替咱俩最合适。”
方军听到这,忽然有些不自然起来。倒是尹玉觉得好玩,插话道:“两位主席都是贵人,就是车翻了,我们也会大难不死。”
谢景新又问:“你老家是龙城的吗?父母还在那儿吗?”
“哦……”方军下意识地瞅了一眼谢景新,“老母亲已不在世了,父亲还在,本来我想把他接过来,但他说啥也舍不得老家那小院,可以种花草,还能自己种菜,自己消费,其乐无穷。只不过,唉,他一个人太孤单了。”
“你家兄弟姊妹几个?”
“别提了,我就一个姐姐,还……”方军欲言又止。沉吟片刻,才说:“我父亲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我姐姐19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后来一直就找不着了。究竟她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谁都不知道。”
“是吗?”谢景新故意很惊讶的样子。他觉得,方军主动说出姐姐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心里的某个角落还是愿意接纳这个姐姐?不过,谢景新仍然不露声色,考虑到这类事情涉及个人隐私,还是顺其自然为好。作为组织,只能给他创造个机会,事情究竟如何发展,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把握和选择。
于是,谢景新又换了个话题:“哎,对了,方主席,你说,往咱们账户打款的那个微尘,会是谁呢?”
方军看了谢景新一眼,不知对方啥意思,便问:“这您会不晓得?”
“哎,怎么说话呢,我要是知道还用问你吗?”
方军笑了笑:“我派人查了银行录像,那天打款的人,是个大约50多岁的男子,戴着口罩,显然他有意不让人们看清真面目。”
谢景新说:“这人境界确实很高。不愿意张扬,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事情往往比较复杂,我看还是静观其变的好。”方军不以为然道。
“怎么,这事还能是作秀?如果真是,他完全不必采取这种方式。我看你不要什么都怀疑,这不是有点‘文革’遗风了吗?”
方军不置可否地笑了。
谢景新正色道:“你分管生活保障,赶快组织人制定‘微尘扶贫基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规定。这笔钱任何人不准擅自动用,每笔支出,必须由我签字。”
“好吧。”方军又加了一档。
车驶抵丁字路口,这是个马路市场。一种说不清的味道立时扑鼻而来。满街水唧唧。铁笼子里塞着鸡,篷杆上挂着一兜兜的红黄水果,扁担竹筐自行车四棱八叉……车轮前头无穷货色,随时可能轧碎什么。方军连续鸣笛,可笛声在这里根本没用。方军说:“这些农民、下岗工人素质就是差,真恨不能跳下去一顿乱打!你想象一下。每次省总领导到我们市总,都要被一堆臭鱼烂肉堵半天,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与我们洁净气派的市总大楼相比,反差太大了。人家没进门,印象先坏了。”
“怎么办?方主席,把你的理论放一放,先告诉我们怎么办。”谢景新瞪大眼睛看着车前。
“嗐,要快速解决问题,只得把人撞出脑浆。”方军双手狠狠拧了一把方向盘。
尹玉探着头说:“已经到这儿了,只有前进无法后退。”
谢景新淡然一笑:“我告诉你吧,怎么走。你不用鸣笛,非鸣不可时也温柔点,小声来两下。你挂一档照直走,轧不着他们。也别刺激他们。道上原来肯定有白线,虽然被踩没了,但他们心里已经留下分寸感。”
方军依言换档,车笔直地驶进去,无数次险些轧到人群脚面,但都顺利过去了。车身碰到人的肩、臂、背,人家全不在意,倒是方军出了一身大汗。三个人不由哈哈大笑。
开出马路市场,方军骤然提速,转眼间车子停在河西县总工会的办公楼前。
他们刚下车,迎面碰到县总工会副主席曹桂珍。这个女人四十出头,人长得不怎么样,却很乐意打扮,尤其是女人该凸的部位都弄得很到位。
“哟,是谢主席、方主席啊,还有尹主任,快进屋,快进屋。”曹桂珍热情迎上来,一把拉住谢景新的手就往屋里让。
谢景新被她身上香水味熏得皱了皱眉,便故意逗她:“曹主席,你是不是用香水泡过啦?怎么这么香啊!”
“哎哟,谢主席真会说话,才喷了一点点就香啦!”曹桂珍说着愈发笑得迷人了。
进屋坐下后,尹玉问:“你们费主席呢?”
“啊……他在下边忙呢!”曹桂珍说这话时有些迟疑。正说着,门口似刮进一股风,费守乐满面春风地进来了:“哎哟,谢主席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谢景新转过身,跟费守乐草草地握了下手,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来。
“谢主席,市总有什么要求,我们河西区工会指哪儿打哪儿!”费守乐信誓旦旦,说着掏出香烟递过去。
谢景新摆手拒绝:“我不是听你说这个,我想问问你们下去的情况怎么样,非公企业建会进行得怎么样了?”
费守乐显得有些尴尬。但他很快稳住了神,把烟点着,抽了一口说:“还可以,昨天我们开了会后,下边都动了起来。”
谢景新问:“你们县现在有多少职工?工会会员有多少?入会率能达到多少?”
“全县职工有13万,其他……”费守乐翻了翻白眼,“这个……现在会员与非会员也没啥区别呀,早取消了入会与退会手续,入厂就等于入会,调出就相当于退会。派来一个工会主席就算建立了工会,确切地说,在基层,工会主席就是工会!《工会章程》虽然规定会员半年不交会费,便被视为自动退会,实际上几年不交会费的,也照样当做会员来统计。”
谢景新说:“我来工会后发现,淡化工会组织观念的现象,可谓俯拾皆是。会员、工人、职工这本来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三个概念混用,有人视此为小事,不屑矫正。其实这正是淡化工会组织观念的表现。不把工会当做组织看,只把工会当做一个部门,把工会干部当做几个做工会工作的个人,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会员做依托,光靠上级的文件是无法改变被撤并的命运。”
尹玉说:“可不是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基层单位撤销了,工会也随之撤销,也自动免去了向上级工会办理批准手续的程序。”
费守乐说:“《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职工,这只是法律规定,实际操作中工会究竟能不能代表职工?职工特别是那些根本就没加入工会的职工需不需要你工会来代表?因为除了工会还有党政及其他群体组织也能代表呀,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谢景新不由皱了一下眉头。他十分讨厌费守乐那种口气,仿佛他不是工会的人!于是就说:“老费,别总用这种口吻说话好不好,你难道不是这个组织的一员?”
方军在一边听得有些幸灾乐祸,所以谢景新话音刚落便立刻接道:“看看,自己小瞧自己吧,连起码的组织荣誉感都没了。中国工会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难道这些你都忘啦?”
费守乐看出方军是有意“加咸盐”,不过毫不在乎,戏谑道:“哈,别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啊!尤其我们县区工会干部,有什么好的?干得比驴都累,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