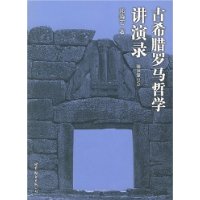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价值尺度的“社会一般必要劳动”;它抽掉了劳动本应具有的感性具体特质(具体劳动),把它归结为平均劳动时间以及维持这种劳动所需的成本(劳动力的价值)。劳动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感性活动,但“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7〕。因此“人是不足道的, 而产品是一切”〔8〕。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正是用科学理性的定量化标准来精确地看待和宰制一切、尤其是精确地看待和宰制人的自然主义偏见,这种将一切自然科学化和物化的倾向,最终导致了胡塞尔惊呼的现代“欧洲科学的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者(即劳动)同他所生产的产品的直接的关系,借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9〕。当然, 国民经济学家都是一些最讲实际、具有实证的经济头脑的学者,但他们所谓的现实、实证就是从“直接的”经济事实出发,特别是从可定量化的科学事实出发,并力图在实际运作中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职分。然而,马克思批评他们其实并没有考察劳动中的直接关系,当他们把人这一复杂的统一体当作一个自然科学所规定的对象(牛马、会劳动的牲畜)来对待时,他们的经验和事实都是片面的、表面的和抽象的,并非真正的实证科学对象。人的完整的、直接的内在体验,他的感觉、他与对象的直接的“意向性”关系,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把握也用不着把握的“黑箱”,他们关注的只是劳动和资本这一系统的外部效应。在这里,劳动者和他的生产对象、产品被看作同样的“自然物”,而劳动者同这些自然物的本应是属人的关系却被忽略了,或被转移为有产者对自然物的间接的、抽象的拥有关系(私有制)了。当然,国民经济学也发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10〕。但国民经济学把这种现象当作国民经济学的必然规律而熟视无睹,甚至作为国民经济学刻意追求的最佳状态,因为它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他们没有看出,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劳动者同他的产品的异化关系所导致的,即他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感性自然界,这个自然界就越是不属于他,他就越是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马克思还指出,劳动产品的这种异化,根源于劳动活动本身的自我异化,它表现在劳动本身对劳动者也成了外在于和强加于他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劳动者在他不劳动时如释重负,而当他劳动时则如坐针毡”〔11〕。马克思的这些描述含有大量心理学的因素,这是另外一种经验、事实,即内在的经验事实,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不属于严密科学的范围,而是由刑法、医院、牧师和社会救济所管的事。国民经济学使科学与人学分离、甚至建立起完全敌视人、敌视人的正常需要的合乎经济学规律的道德(资产阶级道德)。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把人看作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体,并特别关注人在劳动中的“感觉”,尤其是对自由的感觉。“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12〕。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人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在劳动活动中的分离、离异,从而精神力量失去了自己的对象和自然界,成为不幸的意识,肉体力量失去了幸福感,成为被强制、不情愿的活动。这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摧残〔13〕。
但马克思的这些心理描述只有出发点的意义,而决不是心理主义。胡塞尔也说:“原初的问题是主体的心理学的体验和在这体验中被把握的自在现实之间的关系”〔14〕。心理主义却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马克思从心理学出发,是为了从中推出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即哲学上的规定。换言之,他对劳动异化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和心理主义描述都进行了哲学的提升,运用“本质直观”将之归结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活动的异化,又通过“本质还原”而达到了对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现象学层次的规定。
对人的本质的现象学还原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是说,劳动异化在哲学上意味着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或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那么,什么是人的本质或类本质呢?这从劳动异化已有的两个规定中即可以推出或“还原”出来:“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5〕;“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动物、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为了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6〕。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与自然界不可分离,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二者的统一就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社会”。社会并不象人们通常理解的,只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相反,它是整个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7〕。向这种“社会”、即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则称之为“共产主义”〔18〕。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这一还原,与国民经济学和以往一切自然科学使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相分离、相对立的自然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它还原到了人与自然本源地相统一的“事情本身”,具有任何人无法否认、无法回避的直观的明证性。胡塞尔说:“真实的明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的也有多远”〔19〕;马克思也说:“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20〕。
正是以人的这种直观本质为衡量标准,马克思才真正把握到了异化劳动的哲学本质:“人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1 )把自然界异化出去;(2)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 把他的生命活动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把它对人说来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1〕。换言之,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只是对人的本来的、本源的“类本质”即社会本质的一种偏离,一种“变样”;但正是这种偏离或变样本身,恰好直观地显现出了人的本源的普遍性本质;正是人在异化劳动中对自然从自身异化出去这点感到痛苦和不自由,恰好直观地表明人的本质本来应当是与自然界相统一的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2〕。在这里,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很难说马克思在这里有意要用原始社会或人的“原始状态”作为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尺(如同卢梭和自然法派所做的那样),相反,他还批评了这种本质上仍是自然主义的做法,认为这“什么也不能说明”〔23〕。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不是一个表面的、自然主义或心理主义的事实,而是更深层次即现象学层次的、透过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而呈现出来的普遍事实,是在不自由的、盲目的甚至动物式的人类活动(异化劳动)的种种变样中仍然顽强地体现着、并归根到底构成了这些不自由的活动的内在根据和背景的本质事实,它是凭借“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才从“眼前的东西”中发现出来的。
人的本质的意向性结构:对象化和人化自然
通过这种本质直观的方法,马克思进一步确定了人的类本质的意向性结构。他指出: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24〕。因此,“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25〕。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便体现为一个“对象化”的意向结构,即自然界“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6〕。所以,劳动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必然在意识中和在现实中都具有自己的意向物,即目的〔27〕,并且必然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未经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构造”的自然界,与人相对立、相外在的自然界,是抽象的自然界,本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产物,它不具有直观的明证性或“自我确证”性。这种脱离人的活动和抽象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在其抽象的追溯中必将导致上帝、神或金钱拜物教的幻觉。它并不具有表面上那种不可置疑性和被给予的事实性。我们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独断的)存在置于括号之中,而从直接的明证性即人自己的感性活动出发,才能阐明这种存在的真正根基。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界、感性的自然界,是人的感性的意向对象。“感性(参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28〕。人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意思是说它一方面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对象性的”(即作为其他存在物的意向对象的)存在物;换言之,他的对象同样是一个具有自己意向对象的存在物,是一个人化了的自然物或一个对象化了的人,是另一个人(或人—自然)。所以,说人是感性的,也就等于说人是社会性的,从本质上说,人是“主体间”的。
主体间性及对人—自然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所以,人的感性与动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动物的感觉毋宁说是抽象的。异化了的人的感觉也是如此,例如“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29〕。反之,人的感觉具有属人的类的特性,作为主体间的感觉,它是可传达、可沟通、可共享的,而没有“利己主义的性质”。于是“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所有物”,人的感官便成了“社会的器官”〔30〕。这正如罗斯金所说的:“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不能歌唱失去的财产”。人只有作为真正的、感性的人,才能在对象身上、并通过对象而在他人身上确证自己,从而“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1〕。马克思反对象黑格尔那样,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他认为“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32〕。但只有在感性中,在全面、丰富地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33〕中,人才能使自己的个体官能成为社会的器官并直接占有自己的对象,人才是真正的、社会性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人与自然界(对象)的结合就是人与人的结合,因为感性的自然界“真接地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34〕。人在艺术中,在语言中,在自然科学中,更不用说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处处都在使自然界“拟人化”或“人化”,并以这种方式把自然界据为己有。非人化的、非感性的、异己的自然界,以及从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对人说来也是无”,它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没有意义的“非存在物”〔35〕。
感性的这种本质上的主体间性,在共时态(空间上)表现为社会性,在历时态(时间)上则表现为历史性。正是在感性的这种历史性中,包含着对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36〕。换言之,人的对象性的实践存在(通常称之为“实践本体”)是一种在感性中直接给予的明证性,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后真正的、终极的“现象学剩余”,它是不可追溯、不可诘问的,是第一性的。例如我不能再问:人的感性存在(实践)又是从哪里来的、由什么决定的?或者(这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感性对象的自然界“原先”(在感性之先)是怎样的、由什么产生的?这种问题只是作为自然科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但作为哲学问题和存在论(本体论)问题则是无意义的,它将导致无限循环或自相矛盾,因为它抽掉了感性(人—自然)却想证明自然和人的感性存在。马克思说:“如果你抛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抛弃你的问题……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只要你那样想并提问,那么你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就失去了任何意义”〔37〕。
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他对人和自然的存在的“实践本体论”的证明: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8〕;“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亦即现实的,这就等于说,它是感觉之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亦即在自己之外有着感性的对象,有着自己的感性之对象”〔39〕。
当然,马克思对于在有感觉的人之外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