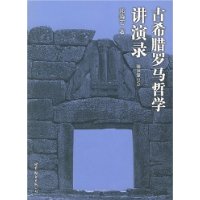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挛脑濉5比徽庋敕ㄊ欠袂〉被箍梢栽僬遄茫抑皇窍胨得飨执河镉屑憷姆⒄箍占洌闯送饫从锖妥钚率贝囊恍┨厥獾男麓驶阒猓ㄕ馐且磺杏镅远家谎模褂幸桓錾畈豢刹獾谋赣每占洌ㄕ馐呛河锒捞氐模圩盼颐枪湃说纳逖椴⒒碓谖颐堑睦芳且渲猩踔裂褐小2还颐窃诶谜庖槐馐币乇鹱⒁饬降悖皇悄芄挥孟执河镆氲拇示霾还室馄鹩霉糯拇驶悖挥性谙执河镏惺翟谡也坏礁既返囊朊辈懦⑹缘焦糯挠锘阒腥パ扒蟀镏欢窃诓捎霉糯拇驶闶币惨⒁馐欠窕嵛扌沃胁羧胛幕尘吧细窀癫蝗肷踔料辔ケ车挠镆濉#ㄗⅲ豪纾镏苄讼壬诜牒5赂穸腅reignis一词时曾一度采用了中国哲学中的“大道”一词,引起了学界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后来他自己似乎也放弃了这一译法。其原因我想可能就是由于“大道”一词中国文化的背景意识太浓,至于字源上找不到根据还在其次。我曾建议将海氏该词译作“成己”,虽也有人(如倪梁康)认为太多佛教味道,但其实儒道佛都有“成己”思想,西方人更不用说,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道”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己”却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译康德著作时其实很少用到古代的词汇,而且我认为一般说来,在译逻辑性很强、概念很讲究清晰的作品(如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和现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时尽量不采用古代词汇,以免造成现代人的理解困难。只有在译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常常诉之于体验和感悟的哲学家的作品时才可以小心地尝试采用古代词汇。
当然,要让哲学说汉语,这不仅是翻译的事,更是哲学思维本身的事,因为翻译(如前所述)一方面是以译者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最终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在今天看来,古代汉语不仅已经不适合于进行哲学翻译(包括对西方古典文献的翻译),而且很不适合于哲学思维。现代汉语则不仅具有翻译上的优势,而且(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具有哲学思维上的优势。我们现在通过欧化了的现代汉语已经在原则上有可能透彻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思想,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深层至今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其实应当说处于高位,正如当年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文化在思想上对欧洲其他文化处于高位一样。如果说,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教哲学说德语”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哲学说汉语”同样将意味着哲学本身在当代的新发展。汉语中不仅也有黑格尔当年对德语备极赞扬的“思辨精神”,即一个词常常会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易者,不易也”,“乱,治也”;又如“亏”字本来指受损失、吃亏,但“多亏”、“幸亏”却是指获得帮助),而且有当今德里达等人所倾慕的“解构”性和“替补”性。最明显的例子是,汉语中连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都是模糊动摇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定的;而且,与西方语言的名词一般都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相反,汉语中动词一般都是从名词变化而来的;(注:恩格斯曾研究过约20种西方语言,发现这些语言中几乎所有名词都来源于动词。汉语则反之,绝大多数动词皆有名词的起源,这只要看看《说文解字》便可明白,所谓“从某,某声”是解释的一般模式,而前一个“某”通常就是名词。这大约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西方语言的任何动词都可以很轻易地名词化(在德语中只须将一个动词的首字母大写即成了名词),汉语的动词要名词化却比较难。尤其是那些原始的单个动词,如种地的“种”,斫树的“斫”,虽然本身出身于名词,但以动词的含义作名词用怎么也觉得别扭,在现代汉语中往往要配成双声词(动宾结构)才能作为一个过程名词看待(如说“农民的斫树造成了水土流失”)。这表明汉语不习惯于将一个动态的活动固定化(实体化),而是倾向于将一个固定名词投入到动作中来展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所以汉语在损失了确定性的同时,却带来了灵活性。(注:当然,有时灵活过了头,也造成了汉语的污染,如时下网上不少文章(“网文”)都有这个毛病,所谓“无哩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任何名词都被消解成其他词性如动词、副词、形容词(如说:“这个女孩很村上春树呕!”)。)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汉语的这种灵活性当我们还未把西方哲学的确定性吸收为我们哲学思想的一种规范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会徒然增加思想的混乱。可以说,我们今天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缺乏学术规范性、缺乏理性思维基本训练的现状正表明了,我们在真正学习西方科学精神方面还很欠缺扎实的工夫。换言之,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处于“前现代”的水平,尽管与“后现代”有某种貌合,但毕竟神离甚远。所以我们的哲学思维对于西方哲学的“高位优势”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我们只有先向西方人学习纯正的哲学思维、“对思维的思维”,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我们的语言文化优势发挥出来。现在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既然西方人都欣赏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混沌性,那么21世纪一定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说法给人带来一种欺骗性的自我陶醉,似乎我们中国人不须花什么力气,就凭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或遗传素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上世界文明的领头羊。其实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从中挖掘出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所习惯、所能理解的语言把古代那些智慧重述出来,用现代汉语去“格”古典汉语的“义”,即一种再创造,而不是现成地搬用古代的词汇。这种搬用只是一种时髦,如果这个词汇并没有得到现代汉语的认可,只是被故作神秘地卖弄一番,那么时过境迁,就会被更新的时髦所取代而遭到抛弃。所以关键在于,当你重述古代的词汇时,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它的意思?你所懂得的那个意思是否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可以取代,你的工作虽然不能说白做了,但意思不大;如果不可取代,那么你要让人意识到这是不可取代的,即通过现代汉语的诠释,让那些研究哲学的人能够发现这确实是不可回避、绕不过去的,非用它不可的。这样,这个词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人家在谈到你所谈的问题时就非用这个词不可,这样你的工作有了推进哲学思维的意义。进一步说,能够用欧化了的现代汉语诠释或翻译的古代词汇,原则上也就能够用外文来诠释或翻译,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成了全大类的财富,哲学就不仅能够说现代汉语,而且能够通过现代汉语来说古代汉语了。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尊重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以现代汉语去打通外语和古代汉语,并通过现代汉语将它们与我们现代人的人生体验及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把现代汉语提升为当代的一种锐利无比的哲学语言,以至于,用已故哲学家陈康先生的话说,要叫西方哲学家以不通中文为恨!(注:参看陈康:《巴曼尼德斯篇》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但并不是不可行的,问题只在于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去做。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本书TXT版本是由久久小说(87book。com)会员整理编辑而成;
久久小说: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
点它……》http://www。87book。com立即入驻久久小说社区。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文偏向的检讨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呢,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我们可以看出,从l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那些有识之士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立国保种的唯一办法。当时面临的危机就是存在危机,中国人、中华民族面临着一种存在危机。西方人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国门,那么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马上就要从地球上被分割、被瓜分,所以向西方学习是当时提出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但是学习什么,向西方人学习什么?以及怎么样地学?这个又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大致上正确的理解,什么样的正确的理解?就是说要原原本本地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林毓生所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从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且是有机整体地来解决问题,单个的零敲碎打那是不行的。你把西方文化的某一个片断割裂下来,支离破碎地、急功近利地从西方文化里面截取一些表面有用的东西,那个是没有效果的。比如说:船坚炮利、简单的工、I2技术、实业这些东西,以及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但是这是表面层次,我们悟出来这样一个层次的学习,不能奏效,实际上它的效果并不如我们原来所想的那么理想,所以要从这样一种表面的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的东西要深入到文化内部、思想文化的里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沉得住气、更加沉下心来考虑和谋划。所以经过这一段,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已经看出来了,中西的差异和优劣归根到底可以归结到人的素质的差异,要归结到这上面来。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国人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思想启蒙,特别是要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这是当时达到的一个共识。所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交界点上,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震撼民族心灵的西学东渐运动,西学东渐应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前面的都不算。前面的办洋务、买西方的技术、买西方的武器,那些都还只能算一个序曲。这个时候进入到思想文化的层面,西学东渐运动才开始发展起来,它的规模、它的声势、它的持久性以及影响力,应该说超过了一千多年前的佛教、超过了佛学,在这一百年的西学的熏陶之中铸造了现代中国不同以往的民族面貌。现代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在民族面貌上已经不同,思想、意识、思维模式都有所改变。当然我们说传统的东西还在,还在起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不一样。百年以来这样的文化熏陶,包括我们的言说方式、书写方式、文化模式这些东西都有所改变,这当然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今天考虑的就是通过一些个案的分析,我下面举一些个案的例子,来检讨我们在这一百年思想进程中的失误之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主要是检讨我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实用主义。其实实用主义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政治实用主义,一个是技术实用主义,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实用主义需要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最终是为了政治实用主义,像“富国强兵”或者是“治国平天下”的这种理想是支配一切的。从里面我想获得一些带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获得一些启示。我们在世纪之交,l9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一种错位,接受西方文化我们发生了一种错位。在百年反思中,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向西方学习没有学到什么好东西,反而把坏的一面学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一个说法:我们没学到好的东西,我们学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被西方人所抛弃了、西方人已经认为是不好的了,我们就把它捡过来了。当然我们要对这种说法进行分析,就是说,这里讲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的“好”和“坏”是从思想文化在社会实践中实际的后果来判定的,好和坏就是看它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那当然就不好了。我们总是说,西方人都说这个东西不好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借l:I,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出这个东西在中国有什么好的效果。如果真的有好的效果,即使这个东西西方人说它不好,我们也不会对它采取其他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看不出它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坏的。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好的效果和坏的效果是由什么东西、按什么标准来评价的呢?如果深入到这一层,我们就发现,其实它的标准是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前已经既定了的,也就是说是传统的。我们评价一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的好坏标准依然是传统的标准,那么你按传统的标准,当然你从西方人那里拿的东西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肯定就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格格不入很可能产生的是一个“不好”的效应,哪怕仅仅是“看不惯”的效应,我们就对它有“不好”的评价。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说把任何学说和理论都放到眼前的实际后果中,并且用以往的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其好坏。这种思维模式、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例如在先秦,就有墨子提出的三表法,所谓“三表法”就是三个标准,我们看待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或一种政策有三个标准: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先王的圣人之言;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当下的经验;再一种呢是看老百姓怎么说,这个对人民能不能带来利益,按照老百姓的评价,带来利益它就是好的。这还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实践中用传统的标准、固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传统历来讲究的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样一种对待理论的态度,思想学说和理论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别的用途,而只能用来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唯一的标准。这个原则一般来说呢也不能说它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一个理论的好坏、成功不成功、正确和错误,我们要看它的实践效果,在实践中达到了好的效果,我们就说它是正确的理论。当然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务实精神的优点。中国人的长处就在于排斥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着边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