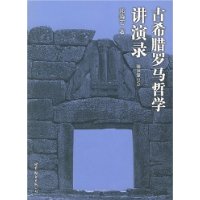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帝王出谋划策,但是他是为全中国人民在出谋划策,在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所以都具有一黧强烈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的色彩。包括鲁迅在这方面也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这一点。他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他自己认为脱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从他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他们双方的“问题和主义”之争,这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胡适讲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批判某些人的理论空谈。“主义”嘛,谈那么多主义干什么,不解决问题嘛。你应该多解决些问题,多解决些现实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倾向。有些人认为有的作家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作品,应该劝他们多研究些现实问题,多解决一些底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痛苦、老百姓的疾苦你要关心。在当时更是这样,胡适就是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奋起反击。但是他们奋起反击、他们的辩护理由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地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辩护理由主要是辩护自己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是本着“主义”来做一种实际的运动,这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辩护。你说我们不涉及问题,你恰好说反了,我们就是要从主义出发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的争论并不是什么实用主义和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是实用主义内部的争论。都是实用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是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只有胡适是实用主义者,其他人就不是。所以批判胡适的人对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狭隘性并没有根本澄清,哪怕他们在反驳胡适的这种实用主义原理的时候,也没有对它进行学理上的批判,而只是进行同样是实用主义的辩护。所以这是一场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什么样的实用主义对什么样的实用主义的争论呢?是一场狭隘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技术性的实用主义对比较高超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政治实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争议。李大钊和陈独秀代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他们比较有远见,所以他们谈主义,谈主义并不妨碍他们谈问题。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你那个东西不解决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哪个地方遭了水灾,能解决么?你谈主义,你不研究中国农村的状况你能解决问题么?你要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嘛。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改革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实用主义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代表思维的更高层次,它是比较有远见的实用主义,你要批判实用主义,但是你自己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并没有得到反省,而且在今天依然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理所当然。问题与主义之争,真理显然在主义一方,不在胡适这方,这是今天通常的评价。但实际上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那么实用主义影响当然还是以杜威、以胡适为代表。杜威来华,然后引起了一波实用主义的热潮,以胡适、陶行知这样一些信徒为典型。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还是有不同的,在我的《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里面也提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呢,是一种技术,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甚至没有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看作一种哲学,这恐怕是中西实用主义的一大区别。西方的实用主义再怎么实用,它是一种哲学,它有形而上学的支持。杜威的哲学是很形而上的。西方人讲实用,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注重形而上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实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主义”。它是一种主义,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当然这种“主义”本身是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但它是一种主义而不是技术。要说主义和问题之争,恰好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主义,所以它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它在理论上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系统。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系统,它面面俱到、无所不通,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它有一个哲学体系。那么到了中国人这里,哪怕最为高深的“主义”,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宝、技术、工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用啊,他们自己说的嘛,马克思主义是“本着主义来做实际的运动”,它能够发动群众,最后能够真的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最高深的主义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法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革命制胜的法宝。“法宝”这个词很有意思,有中国特色。姜子牙有一把神剑,那是他的法宝,其他的妖魔鬼怪也都有自己的法宝。《西游记》里面也是,每个妖魔鬼怪也都有一两件法宝。那么我们也有法宝,我们的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陶行知,陶行知现在我们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他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很有影响,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的一种体现。陶行知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但是呢也有他的问题。他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所谓“试验的方法”,试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呢?他认为,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问题”了,问题是放在前面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种种方法来解决。要针对问题去设想种种方法来解决它。比如说有个人生病了,有的人画符放在辫子里面,有的人请巫婆,有的人到庙里烧香祷告,有的人请医生,有的人吃金鸡纳霜。金鸡纳霜是一种西药了,是治疟疾的。到最后,如果说吃金鸡纳霜好了,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是吃金鸡纳霜好了,如果不分中外、男女老幼吃了都是灵的,那么金鸡纳霜能够治疟疾就不会错了。这当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他称作“试验主义”,做试验嘛,遇到问题你就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不行那一种,那个方法不行这一种,这种试验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不妨多试一试。但是这种试验主义呢,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来不及找到好办法的,乡下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庙拜佛不行了,我换一个庙,换一个师公来做法赶鬼。师公来了不行,我再去画符烧香、烧纸灰等,办法试尽了都没有希望的话,那最后就只有等死了。很多乡下人生了病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你说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么?这叫盲目乱动的试验主义,什么法子都试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等死。但是碰巧现在有了金鸡纳霜,有了西医,当然你可以去选一选、去试一试。乡下人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的愚昧,有人说西医是挖小孩子心肝的,有了病不敢去看西医。不敢去看西医,当然是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了,你不妨去试一试嘛。在这方面呢,试验主义可能有一种开拓性。就是哪怕别人传闻是罪恶的西医,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试一试,大胆假设,试了不行再说,不是还有个小心求证嘛,要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这是很狭隘的,有了有效办法以后你才能碰得上,而且代价很大。如果你开始就碰上了,那么很好,如果你是晚了、快死了才去碰上,那代价就很大了。所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呢,实际上跟传统的巫术没有什么区别。它还是一种巫术,要寻求一种法宝,当然巫术就是这样干的。原始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病了请一个部落里面的巫师来,做法搞了半天,没办法救,死了;又一个人病了,又请他来,又死了,然后这巫师不行,把他废了,再换一个,可能到别的部落里面去请一个来。就是这样不断地试。连野蛮人、原始人都知道这个,不断地去试。所以胡适的理论将导致这样一种盲目乱碰的心理。实用主义完全忽视理论的话就会导致这样。那么陶行知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论,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教育即生活,你把教育当生活,在学校里面就是在生活,你不要从学校到学校,不接触社会,你要把社会上的生活知识都教给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学校即社会,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会怎么样去适应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拿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来,效果不一定好。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不重视理论思维,在学校里面更加如此,尤其是现在重理轻文,不重视理论性、理论思维,只重视技术。工科大学现在是最吃香的,理科现在已经不再吃香了,文科更加是走在边缘。所以不重视理论思维、只重视生活技巧,这在学校教育里面留下了祸根。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是陶行知造成的,不过陶行知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呢,显然跟后来的发展趋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都被撤销、都被下放,工农兵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这里有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要理论思维。凡是你学的东西马上就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我们当时的那个时代,“文革”期间、“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连中学、小学里面都没有什么数理化了,只有两门课,一门是“工业基础知识”,一门是“农业基础知识”。我的弟弟他们就是学了这两门课,名为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就知道怎么样用用滑轮啊,怎么样插秧啊,怎么样施肥啊,就知道这些。这就是中国的实用主义的典型,它实际上最不实用。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反对实用主义的那一方,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依然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说他们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从认识论、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证实,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实用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是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靠后,政治实用主义首当其冲,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一切才谈得上。当然你真的要提实用主义的话,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了;你要讲问题和主义,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它本身也是问题之一。但是我们的争论,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讨论这些问题,它恰好不讨论实用主义的问题。实用主义是什么?拿来主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探讨。他们不是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策略上的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哪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死争。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介绍的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精细的咀嚼。所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迷信和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等这样一些口号,都是在理论上极不彻底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提出来的。其他的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好,我们下面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这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当然跟中国革命实践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占了上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优势。那么在这里,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被看作一种方法论了,跟我们“法宝”意识可以最直接地结合在一起。那么由于唯物辩证法,我们在哲学领域里面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标准,所以在当时研究哲学的很多。比如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里面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标准。比如说,李石岑、郭大力等人,他们在考察希腊哲学的时候,就对希腊哲学的三大哲学家进行批判、加以贬低。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大哲学家,在他们看来都是属于唯心主义的。那么抬高的呢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这些反唯心主义的。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智者学派,在他们看来是属于怀疑论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属于唯物论的。所以这里头已经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了,当然还没有后来那么明确。但是对希腊哲学原著加以客观认真地解读的很少,只有严群在那里搞一些认真地解读,而且被人们所批判。他解读那些东西,人们都嘲笑他,认为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习惯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里面一直保存下来,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完整地、历史地领会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神,而是喜欢在一大堆哲学家里面挑挑拣拣,美之名日“去粗取精”。去粗取精,西方哲学几千年,我们能取出来的有几个算精华的呢?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唯物主义者算精华了,其他的算糟粕,其他多数人都算糟粕。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在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还是同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表现。
康德、黑格尔两者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以前我们对康德批得太狠了,被黑格尔统得太死了,一讲就是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列宁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最厉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黑格尔,其实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提这个问题本身是有它的思想解放的作用的。但是思维模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西方那么多哲学家我们选哪一个?我们立足于自己的标准、立足于我们目前的实际问题我们选哪一个?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到中国以后,人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适合于中国的,于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历史上的哲学家。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的关注,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也形成了一个热点,在20世纪30年代,比如说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当时有张颐、贺麟、朱谦之、郭本道等人,他们做了一些理论工作。尤其是贺先生,他为了弄通黑格尔,预先学习了斯宾诺莎、康德,尤其是斯宾诺莎,贺先生是斯宾诺莎专家,而且也是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斯宾诺莎专家。这个在中国学术界里面也是很罕见的,为了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达到如此高度,是很罕见的。但是呢,也仅此而已,他为了研究黑格尔仅仅去研究了斯宾诺莎,其他的人他没管,他也是从中间挑挑拣拣的。所以他的学术活动最初的目的还是在于经世致用,当然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提供论证。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贺麟先生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研究黑格尔,他也是认为黑格尔对中国很有用。因为黑格尔跟理学、跟朱熹的思想很接近,他认为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来宣扬朱熹的思想,而且比朱熹更先进。朱熹当然很粗糙了,黑格尔讲得很细致,应该来说比朱熹更有用。朱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比朱熹更有用的黑格尔哲学,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它,贺麟先生当时是这个思想。也可以说,那一代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在这样一种经世致用的政治实用主义之上的,几乎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