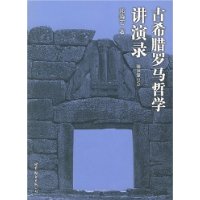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械揭恢治廾摹巴纯唷保饪峙戮褪墙说囊恢植虏饬恕N业咕醯盟坪醪⒉桓械接惺裁赐纯啵炊幸恢值靡猓恢挚梢运嫘乃髑泊视铩⒃诖驶愕拇蠛V杏斡镜拟蛔缘谩U獠皇且桓稣也徽业玫饺非械拇驶愕奈侍猓撬覆辉敢飧秤枰桓龃实ヒ坏娜范ㄒ庖宓奈侍猓簿褪窃覆辉敢獬腥稀按省保┚馐汀⒐娑ǎ梢曰竦闷涔逃械母拍钅诤蚨梢猿晌庖荒诤ㄒ庖澹┰谑堤迳系牡燃畚锖腿ù淼奈侍狻N鞣秸苎У闹诙喔拍罹褪怯谜庵址绞叫纬珊腿范ㄏ吕吹模缪抢锸慷嗟碌摹靶问健焙桶乩嫉摹袄砟睢倍际峭桓鲎郑‥idos),但经过亚氏的解释,人们今天也决不会把两者混淆。日常语言中并没有任何现成的哲学名词可以不加解释、拿来就用,而必须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对之加工,使之定形。老子对“道”的种种解释,其实还是大体上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了),但他似乎不愿讲得太死、太确定,并不是因为对象本身之“不可名”才没有给世界本体一个固定名称。一切哲学概念用日常方式来“取实予名”都是“不可名”的,否则就不是哲学概念而是经验事物了。语言是“人化自然”,名词和命名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的规定活动。老子故意逃避语言规定正说明他对“人为”的放弃。他企图使人直接溶化在自然中,与自然同一。他要求人“涤除玄览”,成为不会说话的“婴儿”。他教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消除一切外来干扰和内心冲动,成为一潭平静的死水,以便清澈地反映自然本体。但他认为这还不够。真正的“圣人”应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他自己写了《道德经》五千言,这已经比圣人低了一个层次了,所以他几乎通篇都告诉人们:这里的“言”只是权宜之计,最终是为了“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语言是临时借用的工具,用完就应当扔掉,以免它夹在人和自然当中,妨碍人直接与自然同一。所以“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第三十五章》),道是离开言之外(出言)的东西,或“意在言外”的东西。后来《庄子》将这意思发挥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辩若默,道不可闻……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这对后世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解释和一般哲学概念的理解起了一种定向作用。
至于“道”这一概念本身,尽管它也包含有“言说”、“称道”之意,常被人与西方的“逻各斯”相提并论,但就字源上讲与逻各斯是截然不同的。道的本意是道路,用作动词,是“行走”之意(据吴澄注“道可道”一语);宋代范应元注《老子》日:“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博弈云:‘大也,通也。’韩康伯云:‘无不通也’可见道又是通达万物的规律。正是从这种意义中,“道”引伸出了表达、说出(道说)以至于“言辞”的意思,这与古希腊从“逻各斯”即话语、言辞中引伸出“规律”恰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思路。中国从古到今都没有人将作为本体的“道”从“道说”、“表达”的含义上来理解,因为这种含义只是道的本意(道路)的衍生意义,决不能颠倒错乱的。相反,希腊逻各斯的本义却正是言说、表达,非由此不能理解作为本体和客观规律的逻各斯。所以,道与逻各斯即使都是“规律”,却有很不相同的涵义。“道”这种规律本身是不可言说的,只能凭内心体验和亲身实行而感受到,其规律性体现在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和人的行为方式中,即“一阴一阳”的循环交替,在逻辑层次上未超出“质”的范畴;“逻各斯”作为规律则有尺度、分寸和规定性的含义,是经过毕达哥拉斯的数而概括出来、具有质和量两个维度于自身的规律,它是可以言说、可以精确规定和定义并可以定量分析的、具有科学含义的规律。毫不奇怪,“道”在中国哲学两千余年的发展中没有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分门别类的科学,永远是“形而上”者,“逻各斯”却造就了西方各种各样的“一logy”,即各门实证的、定量的科学。
二、“名”与“言”
中国哲学中,与“逻各斯”更为接近的是“名”。“如果从‘名’或‘名言’的字源方面看,先秦所谓‘名’,确实有如古希腊‘逻各斯’这个字”(2)“名”在先秦儒、道、法、墨、名诸家都是一个极重要的讨论课题,但很明显,任何一派也都没有赋予它本体论的或“客观规律”的含义,因此不能用“名”来译西方的“逻各斯”。道家对名、言的忽视上面已说过了,我们再看看儒家。众所周知,儒家“名教”肇始于孔子。孔子认为“为政必先正名”(《鲁论》),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这段话包含两重意思:1.“名”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2.作为政治实用的重要工具,名具有核心作用,一切礼乐刑罚均以它为前提、为标准。由这两方面,后来就发展出了法家的“刑名法术”,“名”就成了“法”。也正由于这种政治含义,名也被直接等同于“礼”,即“名分”(3)。中国古代很多术语都有种越来越伦理化、政治化的倾向。如果说西方语言中隐含着某种“逻辑本能”(如克罗齐、伽达默尔所云),则中国语言中包含的是“伦理本能”或“政治本能”。
由此观之,真正与西方“逻各斯”的本义接近的还不是“名”,而是“言”。“言”没有伦理政治含义;但正因为如此,它就处于比“名”更卑微的地位。“名”的重要性本来只是作为政治实用工具的重要性;“言”被夹在“名”与“事”(实)或“行”之间,即没有名的工具作用,又没有事或行的目的性质,就更只是一种外表呈现的可疑现象了。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公治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并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方面,儒家与道家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孔子的“名”与“言”有这样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孔子那里便产生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一方面,他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名分”要确定、分明,不得含糊混淆,另一方面,他连自己核心范畴“仁”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没有确切的定义,而是随不同的提问者和问题、场合予以不同的解释。但这种矛盾只要懂得了孔子“名”与“言”的区分也就消除了。“名”是确定的,“言”则是灵活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李氏》),“名”是外部形式、礼节和“面子”,“言”则是对“名”的解释或体会;名是严肃刻板的,言则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古代伦理制度等级森严,思想文化诗意盎然,唯逻辑的确定性被冷落窒息,于此已可见其根由。以诗为喻的表达方式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般都被限制在文艺宗教范围之内。当然也有用来讲哲学的(如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秘主义及近代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但并不干犯逻辑的事务。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一直将诗喻、类比和“能近取譬”视为一条最重要的证明手段。这诚然避免了如亚里士多德那种使语言抽象化、形式化的毛病,保持了语言本身与人生体验的丰富关系,但同时也使语言一直停留在朴素的无定形阶段,成为“气”一般捉摸不定的东西。往往对一个概念名词注者纷起,莫衷一是,往复辩难时常陷入言辞之争,无法交流,难以发现真正的矛盾和互相促进。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那极其丰富的人生体验也由于没有确定的文字记载下来、传之后人,许多都白白地流失了。
对于“名”与“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言”与“意”的关系),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这就是认为“名”要符合于“实”(“名副其实”),“言”要不损害“意”。主张名要符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1.当“实”因为某种原因(或因其大,或因其玄,或因其无常、易变)而不可名、或不可定名时,则宁可去名而存实,这是道家的态度;2.当“名”‘实”相错甚至相反,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时,则必须“正名”。正名也有两种:一是针对实而建立与之相当的名,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特别是孔孟的态度;二是“制名”或“定名”,然后以之作为法度来衡量实,这是苟子的态度。“名乜者,所以期累实也”,“制名以指实”,“名定而实辩”(《苟子?正名》)。法家则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修(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生于实”(《管子?九守》),“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不论“正名”的含义如何,上述各派在名必须最终以实为根据、为鹄的这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哲学中没有谁认为名比实更重要、更实在乃至于倒名为实(如西方柏拉图、中世纪唯实论和近代唯理论),就连“以名为首”的韩非,也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其实以名为首和以实为归是一回事:正因为看重名的实效,才会强调名的重要性。
最直接阐明实乃名之根本的还是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取实予名”,认为“瞽不知黑白
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他特别强调感性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他分为三个方面,以作为人们言谈的三个标准或“三表”:一是历代过去的经验,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二是当时多数人的经验,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三是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这就是“言必有三表”。后期墨家虽更强调逻辑辨析和论辩的作用(“墨辩”),但在名实、言意关系上与墨子是一致的,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墨经.大取》),“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上》)。《墨经》的逻辑思想与西方(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仅仅是为了给(已知或未知的)事实“取”一个正确的“名”(“名实耦”)、以便“志行”的方法,只是为了使名实相符才要给“言”立“仪”;而正因为名、言脱离不了经验事实的个别性,因此它的证明、推理、归纳、演绎等一系列“辩说”方法的主要根据是“类比”;又正由于类比终究是不可靠的推理形式,后期墨家并未给予推理以逻辑上正确无误的信赖:“是故僻、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小取》)说一种逻辑“不可常用”,这种思想本身很难说有什么逻辑精神。在墨家看来,逻辑只是实用的一种工具,而且只是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工具,即“辩说”,而不是有关认识规律、必然性和真理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普遍性。假如不用逻辑、不讲“名言”也能达到实用目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全都可弃置“不用”的。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逻辑离不开它所反映的对象,但第一,他认为正确的逻辑必然反映客观对象④,不能反映客观对象的原因决不是逻辑本身“远而失,流而离本”,而正是由于逻辑上还不够严密、完善,因而必须更严格地制定逻辑规则、更精确地进行逻辑推理;第二,他认为真正的客观对象不是感性事物本身(质料),而是它的形式或本质、规律。“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的东西就其来源和本质而言,却是属于存在的,逻辑的东西作为事物的
被思维的结构而属于事物的实在结构”⑤,所以“虽然认识现实是从个别的东西开始的,而
且没有个别的东西就不可能有认识,但是没有一般的东西,认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f不仅
如此,认识也是认识那种规定着现实的一般的东西”⑥。这正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
精神,它一直贯穿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逻辑不只是一种“辩说”之辞,而且具有认识论和
本体论意义,它反映着世界的本能结构。至于类比推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证明(必
然知识)的形式,而只是演讲术的说服形式”⑦,并不具有严格逻辑的意义,倒的确是(用墨家的话说)“不可不审,不可常用”的。
先秦在名实问题上,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名家”,他们离开“实”而专门研究“名辩”问题,发展出类似古希腊智者的一派诡辩学说。然而,名家对名实关系的割裂,最终仍是为了政治实用,达到“形名之治”。“古代所谓‘名家’,实在就是‘形名家’,亦即‘刑名家’。”⑧他们之所以割裂名实,只是因为事实上“名实”之相怨久矣”,所以“知其不可两字.,乃取一焉”(《管子.宙合》),以便用滔滔名辩来说服人而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却丝毫也没有以名当实或倒名为实的意思,不象智者派(如普罗塔哥拉)把人的主观当作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名家著名代表惠施主张“合同异”的相对主义,提出过十条似非而是的命题;但这种相对主义也体现在他的“去尊”、“相王”(让齐、魏相互都称王)的政治主张中。他生平的主要活动是任魏相达十五年之久,可见其名辩决不是象古希腊智者要“教人以智慧”,而是一种政治谈判术,具有极为实际的目的。公孙龙子以“离坚白”的绝对主义著称。他自谓“欲推白马非马之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在他对待名称或指谓的态度上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即一方面,他在《指物论》中提出“物莫非指”,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名称来指谓,“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为指?”指是指他物的而非指自身的,但不是指自身,这已经就是对自身的指谓了,何必依赖他物而获得自身的指谓呢?所以指谓作为名称是可以独立于物外而进行指谓的。有人由此把公孙龙定为“唯心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天下无物,谁径谓指?”没有物就不可能指谓,在《名实论》里他也强调:“失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所以要“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另有人就据此把他看作“唯物主义者”⑨。其实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公孙龙将名、指与实、物分离开来,提出指物之指与指本身之指的区别,正是为了更准确地指称实、物,以免混淆指和物、名和实,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尽管他并没有解决名实关系问题,而陷入了逻辑悖论,但他最终注重的显然是实而不是名:“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名实论》),正实才是真正的正名。由于惠施、公孙龙名辩的政治效益并不显著,在理论上也容易将语言引向脱离经验事实的方向,就连与惠施最亲近的好友庄子都批评名辩学派是“垒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骈拇》),说他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所以先秦以后,此派即绝。
魏晋时,大倡“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