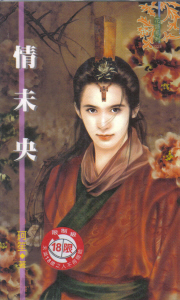清.情未央 十三党-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放下手,瞪着眼睛瞧了弘昌一眼,转身愤然而去。
流转(命运,措手不及)
生米煮成了熟饭,便成了一道单选题,自然的,弘昌娶了玉树。虽然皇上指婚以博尔济吉特氏女为嫡福晋,然而因着弘昌对舒巧的承诺,在府里,玉树坚持只做侧福晋,弘昌也默许。这么着,玉树虽名为嫡福晋,上上下下却只以“侧福晋”唤之。原以为这事定会掀起轩然大波,毕竟玉树和塞布腾已有婚约,况且这塞布腾是一般人么?不是,人家也是王孙公子啊。
可是,当玉树亲口对塞布腾说“对不起”的时候,塞布腾的脸上却漾起一层难以言说的感情,似眷恋亦似不舍,脸上浮起不可捕捉的笑容,轻声的说了句“再见”,之后进了宫成了禁军侍卫——以他这样的身份谋到一个好职位是不难的。
忙完了婚礼,雍正四年拉开了序幕。我看着窗外的烟花满天,屋子里的碳气烤得人脸颊上都染着红晕。孩子们的笑声晕在耳畔,还有他温暖的手与我相握,眼波流转。
婚礼,过年,大大小小的事儿忙得我不得□,而忙完这一切我终于也病倒了。初以为只是小感冒,却不想这病竟越演越烈了。
那夜,我晕晕忽忽的从梦里醒来,只觉得口干舌燥,浑身烤火似的。挣扎的从床上坐起来,眼前一阵阵晕旋,房顶都跟着颠三倒四,脑子里都灌满了浆糊似的,往下沉,往下沉,就要把我拽到谷地了。我一闭眼,把那阵子旋晕忍过去,回头看了下他,正在熟睡,我轻声喊了两下:“胤祥——胤祥——”他却没醒,还是轻轻的鼾声。
我只能自己下床去,好在桌几上还有一壶凉茶,我一步一晃的踱过去,全身却像要散架了似的,上上下下的酸痛。短短几步像是费尽了我全部的力气,我坐到桌边上,大松一口气,微喘着气,心里怪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呢?这么点儿事就累病了?
小小的水壶拎起来像是千斤重,手上的力量难以支撑。水泼了一桌子,才勉强倒了一小杯,我就过去喝,冰冰凉凉的,润得喉咙里极舒服,我直把一壶凉茶都喝光了才算完,摸着黑走到床边,正要迈上去,却踢到了床柱,腿下一软,我“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下,下意识的叫了一声,腿正磕在床柱上,疼得我滋牙裂嘴,手没力气的往腿上乱捶一通。
“馨儿。”他支起身子,往下面一探,语气忽变,“哟,这是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下床倒水喝摔了一跤。”我掩起表情,强作欢笑。黑灯瞎火的他倒也未曾察觉,打趣儿道:“看看你,多大的人了,还能摔着咯。”我原想对付他一句什么,奈何心里烧得发慌,头发昏眼发花的那还有那个精神?他把手递过来,要搀我起来。我把手搭上去,自己又想起来手心已经烫得吓人了,忙不迭的抽回来,又凭空失去了支撑,像是没骨头似的滑坐下去,这次可真是晕得不轻了。
“馨儿,馨儿。”他连唤了两声,迅速下了床来,半蹲半坐的与我平视,“可了不得,怎么烧成这样?”他手探上我的额头,大冬天在被子外面呆久了的缘故,他的手是冰凉的,放在我额上倒能让我觉得很舒服,我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道:“我没事儿,你不要担心,就是发了点儿低烧。瞧你手冰的,快回去躺着。”
他下巴抵在我额上,轻轻吻了吻,而后把我抱起来,小心的放回到床上,给我掖好被子。“等我一会儿,恩?”我眼睛烧得灼灼的疼,把他拉住,“你干什么去呀?你快回来,大晚上的把我一个病人丢下也真是忍心。”
他手在我脸颊上拍拍,“总不能任你这么烧着,我让人去熬点儿药来喂你。”
“快点儿啊。”我听了轻轻松手,视线已经模糊了,眼睛里都像是有火在燃着。胸口堵得慌,我抱着被子,渐渐的又被一种沉重的感觉压下去,压下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以后,隐约什么东西豁然一亮,强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来,我好像呢喃着说了句胡话,然后接着埋着被子睡。
“馨儿,来,起来,喝药。”我听到他说,并且一只手垫到我头下面,要扶我坐起来。我胡乱的挥了挥手,“不要,不要,让我睡觉。哎哟,好疼呃。”我把被子往头上一蒙,浑无知觉了。
然后我睡得昏昏沉沉,沉沉昏昏,他也别法子,只得任我睡得熟了。
“馨儿,你好点儿了么?”他担忧的握住我的手。“唔——”我皱紧了眉头,头疼欲裂。我茫茫然的对四面望了一眼,仍旧是一片漆黑,像一块密密的黑布遮住了所有的视线。“什么时候了?怎么睡了这么久还是大半夜?”我问道。时间仿佛冻结了,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是压不住的颤抖,很冰很凉。
“什么……‘什么’?”我隐约有了些不好的预感,我也莫名其妙的浑身发起抖来,胡乱一抓就逮着了他的手,使劲儿的摇撼。“胤祥,胤祥,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呀。”我哭腔腔的抓着他的手靠在他怀里,另一只攥着被单。
“馨儿不怕,馨儿不怕。不怕,不怕。”他抚弄着我的发丝,与其说这句话是说来安慰我的,还不如说是安慰他自己的。“馨儿,看得到我么?”他小心翼翼的问,生怕我说出来的答案会让他措手不及。我努力的睁大眼睛,却是徒劳,眼前的黑布一样遮在眼前,我下意识的伸手在面前乱挥一气,像是要把那块恼人的黑布扯开,扯开。
可是……我像是陷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所见的永远是茫茫的、沉沉的黑色,不见光明。我胡乱的挥手,挥着挥着,我眼泪流了一脸的,伏着身子仰躺在床上,咬住手指,我低低的哭。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平白无故的失去了一种感官,从此就失去了光明,永远沉溺于黑暗,这种痛苦大概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而惟有此刻,你真切的知道,也许这样一辈子就永永远远的失明了的时候,才会体会那样揪心的痛。
“馨儿。”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我知道他触手可及。我颤颤的伸出手去,被他一把握住,轻轻的放在唇片上,热得发烫。他的胡茬儿在我手心里磨挲,他俯下身来,靠在我身边,我倚过去,把头埋在他颈间,突然的,放声大哭起来……
哭得倦了,他轻轻拍哄我,“我真是没用,昨夜竟没有发现。”他自责的语气叫我心疼,“别这么说,若从此瞎了那也只能怪我自己命运不济。怪不着别人去呀。”他摸上我的脉,沉吟良久。“这病,要好起来也容易,要病着,大概也就……只因高烧不退,才引得失明,不过是暂时的。好好养着,这几天我哪儿也不去,寸步不离的陪着你,你不要怕,恩?”
我听见他说这话的语气,突然就觉得只要他在我身边,我便有一道护身符,什么困难、什么坎儿都是总能跨过去的。“胤祥,如果,如果,这一辈子我真的瞎了呢?”
“胡说什么!有我在,你一定不会有事儿,我保证,保证我绝对不让你有事儿。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只怕我也是了无生趣了。”他轻叹一口气,紧紧的把我搂在了怀里。我病着的日子里,他精心的呵护我,生怕我再出意外。纵然高烧加上失明让我身受病痛折磨,然而处处让他护着、疼着的感觉也让我分外珍惜。
大事小事,他不假手于人。一但又发起烧来,他就一遍遍的给我浸冷帕子,手握着我的手,在床边陪着我守着我。喂饭喂药,也亲自动手。这样待我却让我有时候会撒撒娇,发发嗲,“不要吃,不要吃,这药,实在是太苦了。您也得体凉体谅我呀。”每逢此时,他便和颜悦色的劝说:“馨儿乖,馨儿听话,馨儿把药吃了,身体才能赶紧复原哪。我还等你好起来,陪我走完整个儿人生呢。”身体稍稍好些的时候,他亲手为我披上披风,扶着我到小院里晒太阳,陪我说话。“馨儿,院子里东边那棵腊梅树开花了,可漂亮了。一丛丛的掩映着,密密的挨着,可闻见了花香了。感觉到了吗?花儿飘在你肩上了,头发丝儿上也沾着,我的馨儿这样可真漂亮,和一幅画儿似的。”
这样子半个月,我过着安恬的日子,白天的时候他陪着我,我既没时间也没心思来忧虑我的病。可是夜里总会突兀的醒过来,一醒来就再难睡着,整宿的失眠。有一次实在是难挨,坐起身来唉声叹气,身边一轻,我问道:“吵到你了?真是对不住。我只是,只是有点儿怕,一会儿就睡了。”
他捏着我的手,两只手合住,“到我怀里来,让我搂着睡。管它什么别的呢,只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天塌下来了,也总还有我给你撑着。”
我拱进他怀里,深深的呼吸,全身缠绕的都是他的气息。就这样一夜无梦,睡到天明。
“爷,”小李子小心的探问了一句。“不要打扰福晋,到外面儿说吧。”
“哎,别,别到外面说。就在里面说,还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么?”
“是。鄂泰林大人来了,正在前厅候着呢。”
“你有没有一点儿眼色?难道不知道我脱不开身么。早早就交待过,不论是什么事,不论是谁,一并推掉。”他肃着声说。我扶着桌沿坐到他身边,手轻轻的扣住他的十指,“去吧。别为了我,耽误了正事儿。连着大半个月把所有事儿抛开不管,一心全在我身上,已让我极是过意不去了。”
“什么是正事儿?你现在就是我头一件大事儿。”他放柔了声音,带着宠溺的靠在我脸上,浅浅的轻触。
触动(前尘种种今冰封)
在我人生的数十年里,每每遇到波折,我或是患得患失,或是数不尽的哀伤、哭不尽的愁,然而却从没有像这次这样的安之若素。不是不怕的,只是为了他,无论怕也好,愁也好,绝不能在脸上透出一星半点,我知道我绝不能让他为了我再食不甘味,在深夜里辗转难眠。而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轻视我的一切,却不能让他为我再添心愁。
“姐姐,”托娅的手拉住我的,我循着那声音转过头,茫然的睁了睁眼睛,虚无的一笑。“诶。”我听到她微乎其微的叹气,轻轻拍了两下她的手。“托娅,好好儿的怎么能叹气呢?都不像你了。我以为我的妹妹最是个坚强乐观的女孩儿,一张脸上永远都是笑容,叫人见了心里都暖融融的。我的病……托娅啊,这话我也只能和你说,我真的一点儿底也没有。若是就此瞎了呢?恐怕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不怕别的,可是我要你们,都好好的活。”
“姐姐别说这样的话。十三爷不是说吗,这病总能治好。哎,对了,姐姐呀,我倒是忘了和你说了来着,今儿十三爷一大早就出门去落花胡同请大夫去了。这不是那天十七爷上咱们府提了句,说是‘落花胡同的王大夫最善治眼疾’。十三爷听了就上了心,立马儿跑去了。您瞧瞧,十三爷对您多好。就是冲着十三爷的这片心,您也不能够自己先放弃了希望,不是吗?”
“是。说得正有理呢,好妹妹,我肚子也饿了,帮我去弄些吃的来,成不?”
“呀,瞧我都糊涂了,这要让十三爷知道,还不得骂我一句不懂事儿哟。那姐姐,你先坐着,我一会儿就来。”
“诶,去吧。呃,是了,还有件事儿,托娅,弘昌房里春凝最近身子像是不大好,我最近又得了这病,不能时时去了。唉,她现在也是双身子的人,怎么也得注意些着。这事儿还是得托你我才放心啊。”
“姐姐,您就是心重,这府里大小的事儿您一个人盘在心里能不生病吗?得,我明白了。”说着听到“哗”的一声帘响,屋子里又归于沉寂。
我手摸索这床沿,细细的触碰边角上那熟悉的花纹。我记得,这里,雕得是一条蟠龙,这里是一条舞凤,上面是朵朵的祥云,栩栩如生。还记得从前夜里起来就睡不着了,那时候夜里就爱静静的看着这些静夜里的花纹,别有意趣。而看得久了,背后就会伸出一双手来,轻轻的在我不经意间,揽上我的腰身,略带了偷袭成功的孩子气的笑意,“呵,看什么呢?”
……
而现在呢,没有蟠龙,没有舞凤,没有祥云,没有静夜里他熟悉的背影,只有我手指所触的一片冰凉。我躺倒在床上,伸手扯下床帐,自从失明以后,别的感官变得特别灵敏。就像是现在,我清楚的听到了床帐“沙沙”的磨裟着床沿和被角,些微的拂在我脸上,这是一种可爱的感觉。我依稀还能明白的“看见”那粉色的梦幻的轻纱帐,还有帐子里曾经有过的无数美丽的故事。
粉色的轻纱帐啊,笼着蒙胧而不真切的月光,像是绸缎似的洒在我的脸上,那是我从前的日子。打从以后,便永远是一块儿严严实实的黑布,将我尘封,与我世界里一切可亲可爱的事物隔绝。
“额娘,您睡了?”弘皎轻声的问,我忙不迭的收起感伤,还有欲落未落的眼泪,掀起被子,笑道,“没呢,大白天的睡什么觉?不过是你阿玛不在我一个人闲得慌在床上躺躺呗。”
脚步声由远而近的传来,我对着正前方伸出双手,“皎儿?”
一双小手轻轻的握住了我的,我笑了,一个母亲的满足的笑。我凭着我日渐敏锐的触觉,向这双手上摸索,这还是一双孩子的手,还没有发育完全,可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双手给人的温暖与力量。在拇指和手掌上,微微的有些茧,虽然知道孩子天天儿的写字、骑马、射箭总免不了的,可是心里还是揪了一下。
“疼么?”我喃喃,“额娘,儿子不疼。儿子是个男子汉,以后还要保护额娘呢,怎么能这点点小苦都吃不得?”皎儿的语气那样坚定,让我恍忽。从前我的兄长站在我的身后,给我最有力的依靠,是我神一样的保护者。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他,依旧是我这棵微弱的小草的庇护。现在我的儿子,站在我的身边,用他稚气的童声给我坚定的承诺。
“我的儿子啊,”我轻轻的喊了一句,没有了下文。“额娘额娘,您怪惠惠吗?”弘皎急切的向我询问。呃,我的惠儿,想起我可怜的女儿,我心里蓦然一阵揪痛,我的惠儿,我从此再不能,再不能看见我美丽可爱的女儿,再不能看见她明媚的笑眼,再不能看见她小樱桃似的嘴唇,再不能看见她巧若小鹿的身形。可是惠儿,额娘还没有看够你呢,额娘还没有亲手为你束起发髻,披上嫁衣,额娘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对你放心啊。
“额娘,您为什么不说话呢?难道,您真的不能原谅她么?”弘皎的语气低落下去,接着说道,“我知道,惠惠她真的很过分,她不理解您的苦心。可是我以为额娘是最疼她的,一定知道在皇宫里她过的有多辛苦。您不是说过吗?在宫里要过的幸福,就必须谨小慎微的活着,这样才得以保全。额娘,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惠惠呢?”
“孩子呀,母亲和孩子之间哪里会有长久的怨、长久的恨?更何况,我对你妹妹,从来不曾怨过,更别说恨。额娘只是……”我说到这儿终于哽咽,“只是遗憾。也许额娘这一辈子就再也不能亲眼看看你妹妹了,额娘真的想她。额娘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对她,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无论她是怎么绝情的待我,纵是家宴上她不认我,纵是她坚持只喊我‘十三婶’,纵然我每次看见她都只差一点儿就忍不住的想要冲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像她小时候那样儿。她还是我的惠儿,我亲爱的最最疼爱的女儿,我爱若生命的女儿。”
“额娘——”我愣住了,因为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